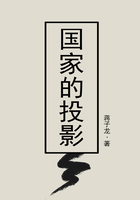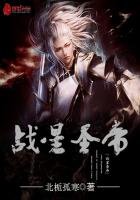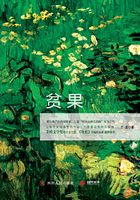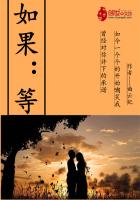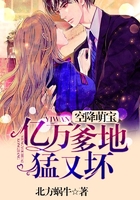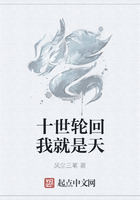在三峡库区庞大的移民系统中,几乎没有一个移民干部不认识他——重庆移民局巡视员陈联德,尽管他已从移民局副局长的位置退居二线,但仍在库区奔波、操劳,可以说,他与水库移民打了一辈子交道。
一位移民干部评价说,陈联德对水电工程、巴蜀移民历史、水库移民政策、水库移民纷争等犹如庖丁解牛。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移民专家,是一部库区移民工作的“活字典”。
这些年来,他为移民争利益,顶撞过上级;站在政府立场,又和移民争吵过。他在万州一个小水库与移民争论,被情绪激烈的移民推进了河里……
陈联德对移民工作的表述常常是妙语连珠。
三峡文物搬迁,要涉及移民资金400亿元的总盘子,在一次讨论如何分配使用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说,我是移民局长,我认为,移民资金主要用于保证在三峡蓄水前把移民搬迁出去。
“文物是死的,移民是活的,现在的移民资金连‘活人’都顾不过来,还要去顾‘死人’!”
“到底是‘死人’重要还是‘活人’重要?”
在“活人”更重要,文物又必须进行抢救的现实矛盾中,国家最后决定在移民包干资金外,另外增加了一大笔文物保护经费,解决了库区文物保护和搬迁之需。
由于陈联德有“活人”与“死人”谁更重要的妙语,不明就里的人以为他对保护文物有很大的偏见,但实际上,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的绝大多数文物搬迁抢救和修复,他都参与了设计和规划,对库区文物的抢救、搬迁和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联德谈起库区抢救保护文物,也是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说: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峡江地区蕴藏着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按照“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目前,已实施地面文物保护项目302项;实施地下发掘项目531项,完成考古勘探面积885.2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数万件。白帝城、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屈原祠、昭君故里等重点文物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002年,在一次讨论如何对水库移民进行后期扶持的会上,很多人都为如何为移民找项目、在移民区做什么项目而苦恼。陈联德一句话语惊四座:我认为,最好的项目就是直接把扶持的钱发给移民个人,而不是我们去为移民找什么项目!
当时谁也不曾料到,他这句“直接发钱给移民”之语,竟与2006年国家出台的扶持水库移民政策有着惊人的一致。
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和他就水电工程和水库移民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
笔者(以下简称笔):陈局长,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水库修成之后,由于生态、战争、移民以及大坝质量、寿命问题而不得不炸掉大坝,这在前些日子还引起纷争,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陈联德(以下简称陈):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美国有大小水坝82700座,如果按平均200年的使用寿命,每年至少也要拆除更新400座水坝。实际上,小型水坝的寿命不可能那么长,一些病险水坝和老龄化水坝都要拆除。水坝总是有寿命的,就像拆除旧房子、建造新住宅一样普通和平常,这算不上什么新闻,也不应有什么纷争吧。
笔:我们国家也常常拆除水坝吗?
陈:当然是,从统计资料上看,我们有很多年份都是小水电总装机容量上升,而电站数目却直线下降。这说明,退役的小水电站有时比新建的还要多得多。如果单从这一点看,我国的拆坝可以说是比美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一份规划表示,今后还要修建55座大型水坝。
笔:你从事移民工作这么多年,除了经验,你认为该从哪些方面总结教训?最主要的体会又是什么?
陈:这些年来,我作为政府公务人员,一方面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但另一方面,我对政府对水库移民大包大揽有一些思考,也有一些疑惑。
笔:你是说对“移民是政府行为”的疑惑?
陈:是的。这种工作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发展中国家建大坝时发挥过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可以减少水库建设的前期投入,集中财力物力干大事。这些年来,三峡库区各级政府把移民作为第一要务,社会总动员,调动千军万马搞移民搬迁安置,实现了三峡百万移民“搬得出”的第一个目标。
笔:我记得你在处长会上讲过,没有这种工作制度,三峡实现百万移民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又会有疑惑呢?
陈:是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应该说“移民是政府行为”这种工作制度,为成功搬迁走百万移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经验和模式也可以载入史册。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另一个方面,我国8万多座水库,共计搬迁安置水库移民有2400多万人。目前约有1/4的水库移民仍然处于贫困状况,其贫苦比例远大于非移民群体,这就使得我们的移民工作的成就大打折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有的移民政策到底有什么不足?在“以人为本”、“制度创新”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对这种模式和工作制度进行重新考虑。
笔:你认为政府大包大揽水库移民的症结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陈:一是补偿偏低,移民短期内难以恢复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
政府行为一般表现为指令性、包办性和强制性。如淹没补偿标准不需要与移民协商,由政府文件下达,并且低于同一地区其他项目的征地标准。《大中型水利水电建设移民条例》规定:水库移民采取“前期补偿、补助和后期扶持”的征地办法,前期补偿一般都取《土地法》的下限。例如,1986年的《土地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取年产值的“三至六倍”,《移民条例》变成了“三至四倍”;安置补助费也由“二至四倍”变成了“二至三倍”。这表明,“后期扶持”是对“前期补偿”标准低于其他行业的一种补救措施。但有的人以“移民是政府行为”为借口,把“后期扶持”说成是对库区的“优惠”。乍一听,这话还令人感动,你想想,你已经搬迁了,住进了新房子,还“扶你上马,送你一程”。
实际上这是忽略了前期补偿偏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笔:按照国际惯例,对于大型工程引起的移民,应由工程项目来负责安置,按此说法,三峡移民应由三峡建设总公司这个业主来负责吗?
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比如地产商修房子,如果由政府全面负责居民的拆迁并修好安置房,地产商肯定省事,成本也低,修房子的速度也快得多。当然,兴建三峡工程不是修一般的“房子”,它是为全国人民谋福祉的一幢“大房子”,是国家的头号工程项目。由国家来充当三峡工程的业主,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
笔:世界银行贷款“4·30”导则政策目标中要求,建设项目“要为移民提供充足的资金和从项目中受益的机会”。对三峡移民“后期扶持”的具体政策是何时制定的?
陈:按理说,工程在动工之前就应把相关政策向拆迁户交代清楚。
三峡的后期扶持政策,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还在探索、完善的过程中。这就是说“政府行为”有被误解的地方。比如,移民人数计算,扶持年限,电站每一度电计提金额等等,是“一口价”说了算,不需计算“前期补偿”到底欠了多少账。因此,就形成了“前期补偿”偏低,“后期扶持”错位。使移民搬迁后缺乏“恢复原有生产生活条件”的物质基础。这是造成水库移民比非搬迁人群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笔:在库区采访,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移民工作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移民工作的“有限责任”变成了“无限责任”,这是不是“政府行为”所致?
陈:是啊,移民工作就像“重庆火锅”,基层政府就是厨师,不论什么菜,都扔进“火锅”里煮。如经济发展、企业破产、居民就业、困难救助、“普九教育”等等,都是政府这个“厨师”要煮的菜。在库区移民搬迁安置前前后后,有些问题的确是由搬迁安置造成的,但有些问题是社会经济运行中自然要产生的,基层政府就“糊里又糊涂”,故意分不清楚。库区的某个社会问题没有资金解决,便归结为移民问题,便伸手向上级政府、业主要钱来解决。移民工作中混杂了许多不是移民造成、不该移民工作解决的问题,使得移民工作界线模糊、职责扩大,其结果是:有限的移民补偿资金分散使用,该办的事没有办,不该办的事又花了大量的移民资金。例如改造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解决无房户住房、城市下岗职工就业、扶贫、教育达标等等,该地方财政办的事,都一古脑儿地全算在移民搬迁的账上,使移民工作留下了更大的资金缺口。这应算是“政府行为”的弊端。
笔:现在库区有一种说法:移民问题不是长的“疮”,也不是长的“癣”,而是长的“癞”(赖),什么事都“依赖”移民工作,区、县、乡镇、村社都有这种心理,美其名曰“打三峡牌”,你对此如何评价?
陈:这就是政府长期包揽移民工作所培育出来的“依赖”心理,“区县村乡,依靠中央”嘛。移民是政府行为,从下到上,不依靠中央还依靠谁?实际上,这种工作制度从一方面看,它忽略了移民单位和移民个人的主体地位,使其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因而产生“依赖”心理;另一方面看,某些基层政府往往在“包办代替”中方法简单,自以为是,把本该交给移民自己办的事也抓在政府的手上。如农民、城镇居民私房建设,按补偿的资金由个人建基本是够的,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形象,规定要由政府统建,结果造成资金缺口。从水库移民的实践看,只要将钱发给单位及个人,他们的“补偿包干,任务包干”一般都能完成。凡是该由政府负责包干的,如农村移民生产安置人数、外迁移民身份审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复建等等,都会出现一定的缺口。
笔:我国大多数大中型水库都是由国家建设,政府负责搞移民,降低“前期补偿”标准,减少水库的前期基建造价,低成本投入,然后政府对因“前期补偿”不足造成的后遗症买单,买单的钱都出自政府财政部门,“肉烂了在锅里”,政府做的事,政府买单,道理上不是也讲得过去吗?
陈:我一开始就说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产物。比如,用于移民的生产安置费,本来应该拨到农业合作社由移民自己安排。库区一些县、乡政府,却要指定移民搞什么“产业”,或由政府办企业安置移民,结果一投产就亏损。很多由“政府包办”的企业都垮掉了,但移民的生产安置费也用完了。基层政府在检讨时常用“好心办坏事”来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一种惩罚。修建电站投资赚钱是业主的市场行为,现在有的大型电站还是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让移民做贡献,业主得利润,政府为移民的后遗症买单,也不符合“谁造成,谁负责”的道德经济学准则。
笔:很多专家包括你都说过,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陈:说实话,我一听见“综合治理”这个词就头痛,“综合治理”这个词的本意是好的,意思是齐心协力,齐抓共管,是大家都拿出吃奶的力气来共同“治理”。可实际上呢,大家是可治理也可不治理。要害是责任不明确,没人负责。
笔:听说你在2005年水库经济专委会年会上的发言,得到大多数移民工作者的响应,能告诉我吗?
陈:我一直在思考,做到投资合理、移民接受、业主放心、实现库区稳定并长治久安,现阶段进行必要的移民管理体制改革,在积累了这么多经验的基础上,是完全可行的。一是水库移民应按一般标准征地拆迁。全国人大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在媒体上公开征求意见时,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是党中央亲民政策和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库移民的补偿标准比其他行业的征地拆迁约低1/3。而10年的后期扶持费是大大少于这1/3的。
这种要求水库移民为企业盈利做贡献的补偿机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法则的。对于以防洪、发电或灌溉为主的公益性水库,也不应该由库区移民做出牺牲,而应该由受益的群体或者全社会出资按市场价给移民补偿。可以对公益性项目优惠的,只能是政府自己的收费项目,如耕地占用税、土地复垦费、植被恢复费等,不能以“公益事业”的名义要求移民个人做出牺牲。
笔:听说三峡移民拆迁的土地,正按新的《土地法》拆迁标准进行补偿,是这样吗?
陈:是的,这是一笔不少的钱,是党和政府关怀三峡移民的一种体现,也表明了政府解决移民区后遗症的决心。
笔:你说“移民是政府行为”在三峡移民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在以后的水库移民中会有所改变吗?
陈:这正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由业主直接负责移民工作,改变“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的做法。从水库移民遗留的问题来看,“安置”是核心,是要害。移民能否安顿、安置好,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是否安稳的大局。实行业主负责制,把移民工作当成工程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解决水库工程和水库移民“两张皮”的问题。
移民由业主单位直接负责或委托社会公司代理。补偿资金由业主按迁建进度直接拨给淹没单位与移民户。据《半月谈》报道,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拆迁办“造假表骗取国家的补偿金,又采取恶劣手段克扣被拆迁群众”。库区丰都县的“黄发祥案”也是造假骗取移民资金,开县在孤岛调查时通过造虚假户口,企图套取国家的移民补偿资金,这不能不说是“政府行为”这种体制中的一大缺憾。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
笔:水库交由工程业主负责,政府是不是就少操心了?
陈:不能这样认识,政府要干的活多得很嘛。
一是按照法律制定征地拆迁的行为规则,如征地补偿标准、房屋拆迁标准,发布封库令,公布征地时间等。制定征地行为的工作程序,规范征地双方的行为。
二是政府要为业主的水电开发活动搞好服务,在安置区鼓励农民向移民有偿流转土地,帮助农村移民在安置区承包土地或自谋职业。在房屋拆迁中根据搬迁人口数量,提前组织开发商或水库业主单位建设足够的房源,平抑房价,供移民户购买,并为移民户提供办理户口、子女入学的方便。
三是监督征地双方正确执行政府的规定,并对超出规定标准漫天要价和得到补偿后拒不搬迁的“钉子户”要依法强制拆迁,维护库区的移民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一句话,政府不能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样很累,大家都累。
笔:我到库区采访,有时有一种感觉,有个别镇乡村在移民工作中,常常自诩为诸葛亮,拿着移民的钱为移民做项目,但效果不是很好,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陈:这是越俎代庖,说严重一点,是剥夺了移民的经营自主权。我认为,移民安置中的生产安置方式、搬迁去向、建房方式、资金投向等,后期扶持中的资金使用等,均应由移民自主决策。国家也多次要求移民资金与移民“利益越直接越好”。是不是一些人想从项目中捞取好处?是不是一些人想树政绩?是不是一些人“心有旁骛”?我看这三者都有。用移民的钱搞个华而不实的项目,一可瞒天过海,二可向上级邀功。据我所知,全国水库库区办了上万个公益项目和经营项目,没有几个项目是能把移民个人出的“本钱”如数赚回来了的。因此,我们移民工作者更应该自觉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想想自己所干的事,是否真正代表了绝大多数移民群众的利益?不要再干那些“自诩为诸葛亮”的蠢事了。在尊重移民的经营自主权方面,在对水库移民的后期扶持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
笔:最后想请你谈谈,你认为解决当前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手段是什么?
陈:这一点要学一学“乌鸦”了。
笔:乌鸦?你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是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
陈:当然是“乌鸦反哺”。水库移民比工厂征地和城市改造的拆迁要难若干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恢复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水平,就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就是对水库移民进行后期扶持。在移民未完全达到当地非搬迁居民的平均发展水平时,应该从水库发电、灌溉等收益中给移民一定的“反哺”,以帮助移民早日安居乐业。
笔:这种“反哺”要多长时间?
陈:一般应为二三十年,大约是项目投产后的一代人。水库从成本中提出一定的资金,“反哺”为水库建设贡献出家园,而又处于贫困状态的移民。国家提出对农业进行反哺,我想这“反哺”二字用于三峡库区移民是再恰当不过了。常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么“水库发端”,就是“始之移民”了。取之于民,当然要用之于民。
笔: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
告别陈联德,“反哺”二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本草纲目·禽·慈乌》曰:“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水库应对三峡移民“反哺”多久?是10年、20年?还是陈联德说的一代人?
一切正确的结论,总是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