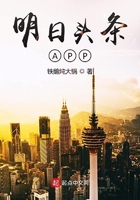费大肚子的日子在有了两三年的好转之后,又重新变得艰难起来。最严重的是他老婆病了。也不知为啥,从领到土地证的那年冬天开始,她的脸渐渐变黄,肚子渐渐变大。借钱去城里看了几回,吃了几十副药,但也没见效力。过了半年,女人就躺倒在床上再也不能下地了。饭吃不下去,那肚子却一天天见高。费大肚子伺候得不耐烦,便与老婆开起了玩笑:“我让人家叫了一辈子大肚子倒没有肚子,原来肚子长在你身上呀?”女人艰难地笑一笑,抬起手拍拍肚皮,那里面便传出了“咣当咣当”的声音。她说:“你听听,这里边都是水呀。是水怎么尿不出来呢?”到了第二年夏天,女人的肚子便像一口倒扣的锅那么大,肚皮薄得呈半透明状态,似乎连里面泡在水里的肝肺肠子都能看得见。女人已经很难说得出几句话,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鼓死我了,鼓死我了。
这天,费大肚子与儿子从地里回来,一进院子便觉得有股腥臭气扑面而来。到屋里一看,只见地上淌满了脏水,床上病人的大肚子却不见了。费大肚子扑过去瞧瞧,发现老婆肚子的一侧张开了一个鸡腚眼那么大的孔儿,一线黄汤还在那里潺潺而出。在她身边的黄汤里泡着的,则是一把剪子。见到这把剪子,费大肚子才明白了早晨老婆向他要剪子不是剪指甲而是要戳破自己。他气急败坏地训斥老婆:“你你你这弄得什么熊事!”老婆闭着眼说:“这回轻松了。这回轻松了。”
可是,这孔儿捅开之后,就再也不能闭合了,那黄汤时流时断,整天引得无数苍蝇来探问究竟。儿子笼头说:“快到城里去看看吧!”女人说:“你还想找媳妇不想?”一句话问得儿子默默退下,而费大肚子这时也蹲在墙边假寐装作听不见。过了几天,苍蝇们便在女人的伤口上生出了后代,那些小东西很活跃地在那里出出进进,费大肚子爷儿俩用小木棍做成筷子轮番夹也夹不尽。
这一天,女人在昏睡了一会儿之后醒过来说:“俺看见银子了。银子说她那里有地瓜干子。”费大肚子听老婆说这样的梦话,不由得潸然泪下。女人停了停又说:“银子她爹,你把咱外甥叫来俺看看行不?”费大肚子答应一声便走出门去。可是过了一会儿,进门的却只有宁可玉的老姐绣绣。绣绣端了大半瓢小米,来后坐在床边说:“姥娘,可玉正在学堂里上学,等放了学再来,俺先来看看你。”绣绣走后,病重的女人却始终没等到外甥进门。他让男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男人这才说了实话:“你就甭再犯傻了。人家可玉是说啥也不来!”女人想起大复查时自己对外甥的绝情,便凄然一笑:“是呀,俺真傻,真傻……”说完这话,女人便又昏睡过去。到了晚上也没再睁眼,却突然将自己的大拇指捅进肚皮上的孔里,浑身上下往紧里一绷,便再也没有声息了。
费大肚子借钱做了口薄棺材,草草将老婆埋掉,接着又为儿子的婚事发愁:笼头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却至今没有找上老婆。这既怪笼头长得丑,更怪家里太穷。前几年也曾托媒人说过,可是等到人家闺女到家里看,一见屋里空空荡荡都是扭身就走。最近一两年再找媒人帮忙,媒人却连连摇头表示爱莫能助。费大肚子想,如今笼头他娘又死了,这个家只剩下光棍爷儿俩,人家怕是更看不上了。
儿子也看透了这种形势,一天天变得颓唐。他家没有牛,去年与另外两个没牛户一道,找有牛的费书理结成了互助组。可是在娘死后,笼头每当干起活来愣愣怔怔慢慢腾腾。一天两天人家还忍着不说,时间长了人家便道:“两个不顶一个用,这工怎么记呀?”费大肚子也觉得不好,对不住别人,便板着脸骂儿子,敦促他动作麻利一些。儿子听了也振作一会儿,但过不了多久又是故态复萌。费大肚子没有法子,想自己多做一些来弥补儿子欠下的,无奈年老力衰,也实在多干不了。这么捱了一年,到第二年正月出了“九”天好耕地了,他像往年那样再主动地去找费书理商量活儿咋干,没想到费书理却说:“你另找搭伙的吧!”
费大肚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弓着一张老腰回家了。他知道再找搭伙的也很难,就决定不找了,耕地没有牛就与儿子拿锨剜。因缺少了其他监督者,儿子越发懒散,不是早晨不起,就是到地里不干。费大肚子训斥他几句,笼头便将大眼一翻:“一个挣了一人吃,出那么多力气干啥?”老子听这话说得可怜,只好到一边摇头叹气。
最难办的还是过年。这个笼头,每到正月初一同龄人拖儿携女串门拜年的时候,便格外地烦躁不安,经常摔盆摔碗。一个年过下来,家中盆碗便所剩无几。缺了盆碗又买不起新的,费大肚子爷儿俩只好就着一口铁锅吃饭。
这年年关又要到了,费大肚子怕儿子把那口铁锅也给摔掉,决定再到王家台找花春子恳求一番。到了那里道:“他表姐,你可怜可怜俺,再给俺操操心吧!”花春子将一对小眼珠子转了几圈,说茬儿倒是有一个,齐家岭的,不过不是姑娘了,是个寡妇。费大肚子连忙说:“管什么寡妇不寡妇,只要是个女人就行!”花春子却又讲了那寡妇改嫁的一个条件:他男人死时欠了一大笔账,谁要娶她就得代她还上。费大肚子低头想了一会,把牙一咬说:“俺给她还!”花春子问:“你有钱还?”费大肚子说:“俺卖地!”
费大肚子从王家台回来,立马在村里发布了要把他家的六亩地卖掉一半的消息。
这是1954年的春节。这个春节封大脚一家过得极不愉快。因为家中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矛盾。
矛盾的起因在宁可玉身上。腊月里他从村办小学毕业了,在拿回一张毕业证书的同时,也将一个要求摊在了一家人面前:他想考中学去。他讲,老师说了,年后凡是想考中学的再回校复习,夏天考试,考上了就在秋天进城。
对他的这一要求,比他大七八岁的外甥、已经做了父亲的封家明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去吧,俺小舅这几年念书一直拔尖,保准能考上!”他妹妹枝子也兴奋地说:“小舅你好好考,上完中学上大学,上完大学去留洋!”
绣绣没吭声,却用眼看看丈夫,再看看儿媳。大脚感觉到了妻子的眼神,也从那眼神里看出妻子是想让可玉再考中学的。但他无法让自己表示出儿子那样的态度。他暗暗想:还想上?这个可玉也真是没个数儿!你爹娘都叫人家砸死了,是我这些年拉扯了你!我不叫你干活,叫你上学,一年年地白吃白穿。早就想你把学上完,好帮帮这个家,可你还想再上!你过了这个年就是十六了,十六就是大人了,可你还想去坐学堂!坐学堂是恣呀,风不刮头雨不打脸,养得小脸嫩白嫩白……最要紧的是,念中学是到城里念,花费就大了,钱从哪里来?不用说还得我供着你。我这几年好容易攒了点钱,那钱是干啥的?能扔到你这个无底洞里去吗?嗯?
这些话他不好说出口来,只是蹲在那里闷头抽烟。就在这时,只听旁边儿媳细粉“啪”地拍了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一掌,厉声骂道:“小杂碎,你还吃不够啦!再叫你吃!”把****从孩子嘴里强行一拔,弄得孩子“哇哇”大哭,然后朝家明胸前一搡:“瞎眼啦,还不抱他出去哄哄!”家明看看细粉的脸色,只好接过孩子去了自己房里。
小两口回房后不久,立即爆发了争吵。只听家明说:“叫俺小舅考学,碍你啥事啦?”细粉大声道:“行呀行呀,你就没想想这是啥事,小的养大的,外甥养他舅,你还想叫这个家过好不?”家明说:“咱小舅以后学出了名堂,人家忘不了咱!”细粉冷笑一声:“谁知道他以后怎么样?就他爹宁学祥那个细作X,还能甩出好种?”
听到这里,绣绣与可玉的脸都变灰了。大脚也觉得不像话,便走到门口喝道:“吵什么?都闭上嘴行不行?”这么一喝,东厢房里就又安静了。
这边,可玉什么话也不说,木然地起身走出门外,去自己睡觉的小西屋里躺下了。
到了晚上,大脚两口子上床后,好久都不说话。后来还是绣绣先开了口:“他爹,我想开了。”
大脚说:“你想开了啥?”
绣绣说:“人心不能太高了。拿他小舅来说,那年能捡一条命就不孬了,还想三想四地干啥?”
男人听了很高兴,把那只大脚在妻子的耳边得意地一晃,说:“就是呀!人不知足不行!”
绣绣说:“我明天劝劝他小舅。”
大脚说:“你是得劝劝他!”
第二天,绣绣敲开小西屋的门,就对那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弟弟劝解开了。哪知宁可玉先是不吭声,后来还是说:“姐,你叫我去吧,我太想念书啦!”
绣绣见自己说了半天没有一点效用,不禁瞅着可玉的脸发愣。过了一会儿她叹口气:“唉,你的心思我也明白,可是这事也难呀。别的不说,就说花钱吧,你知道,咱家的钱都是你姐夫攥着……”
可玉听到这里忙说:“我不花你们的钱!”
绣绣奇怪地问:“你哪来的钱?”
可玉看了姐姐一眼,低头咬了一会儿嘴唇,却又说:“……我,我也没有钱。”
绣绣便道:“算了吧可玉,算了吧。”
可玉把脸扭向门外,两行泪水簌簌而下。半天后说道:“我还是想考学……”
绣绣看着他这样子,也忍不住哭了。
几天后便过年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绣绣与儿媳闺女包完饺子已是深夜。她洗完手,想到小西屋里拿两张纸盖饺子,然而走到那里一看却发现可玉不在床上。绣绣心里便立马找了个激凌:这孩子晚上是从来不出去串门的,眼下到哪里去了?想了想,他便到东厢房里把儿子喊出,让他出去找一找。家明答应一声便出了门。绣绣一颗心悬在那里,没作多想也急跑几步追上了儿子。
找了几户可玉有可能去的人家,但拍门问问,人家都隔墙回答没见。绣绣急了,喘几口粗气道:“你说你小舅到底去哪里啦?”家明想想说:“八分是去了学屋。”绣绣觉得有道理,便与儿子往村后的学屋走。
不料刚走过一条街口,走在前头的家明却突然停住脚步小声说:“娘,你看井台上是谁?”
绣绣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看看,那结了厚厚一大片冰的井台上,正背对着他们蹲了一个人。看那窄窄的肩膀,恰恰是可玉!他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勾下头去瞅那个黑咕隆咚的井窟窿。绣绣立即急得心里冒火:他是要寻死呀?她急忙喊:“可玉!可玉!”边喊边跑了过去。她想伸手抓住他,自己却一下子滑倒了冰上。倒是家明与可玉同时过来扶起了他。
绣绣抓着可玉的肩膀问:“你到这里做啥?你到这里做啥?”
可玉低下头说:“不做啥。”
绣绣恨恨地道:“你想寻死的话,当年我就不该把你藏在地爪窖子里。”
宁可玉不吭声。过了一会儿说:“姐,咱们回家吧。”
路上,绣绣说:“可玉,你可甭再弄这吓人的事了。”
可玉点点头:“嗯,不啦。”
安排可玉睡下,绣绣到堂屋里跟丈夫说了这事,大脚吃了一惊,说:“这还了得?上不成学就要去死?那样的话,庄户人还不都得死净?”
年后的几天里,宁可玉显得很平静,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一家人便把心放了下来。
大脚没有事干,一吃过饭就到村前铁牛那里看热闹去。像往年的正月初一样,这儿的空地上,每天每天都聚集了玩耍的人。下棋的,“打翘”的,啦闲呱的,一堆一堆一伙一伙。就是在这里,大脚得知了费大肚子要卖地的消息。
得知了这消息大脚的心立即激动起来。他存了好几年要置地的心,可惜土改之后卖地的户很少很少,一般找不到。天牛庙全村只是在去年才有过一户卖的,但等到大脚听说后那地已经有了主儿。大脚心想,这一回可不能再落空了,我一定要置上几亩,让儿媳妇看看,她公公不是个孬泥碗子!
想到这里,他就决定赶快回家找绣绣商量。由于走得急促,那悬殊的两脚造成的身体歪斜便加大加快,惹得街上行人都对他投以诧异的目光。
然而,当他回到家把这事和绣绣一说,绣绣却把头直摇:“别买。”
大脚问:“为啥?”
绣绣说:“置地不是好事。”
“怎不是好事?”
“没看见俺娘家?”
大脚很不以为然:“你娘家?你娘家是连抢加夺!咱置地是拿钱公公道道地买,再说费大肚子也急等钱用!”
绣绣说:“反正地多了不好,地多了招灾。”
大脚反驳道:“我知道你又说大复查。大复查是过六十亩的才丢命哩。咱才多少?咱再置上三亩才不到三十亩。”
“我还是劝你别置。”
见妻子一再坚持这种态度,大脚的目光里就有了许多怀疑的成分。他点着头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为啥不答应了。”
绣绣抬头问:“为啥?”
大脚说:“你是想拿家里的钱供你兄弟上学。”
绣绣一下子把眼睛睁大了。她愣愣地瞅了男人片刻,眼角里就有泪水滚了出来。她从腰间摸出钥匙,打开柜子,拿出一个蓝布包扔给男人:“你去买吧。买多少我也不管了。”
大脚接过布包,瞅了妻子一眼,而后就朝门外走去了。
这桩土地买卖是当天在宁学诗家里谈的。宁学诗这个七十三岁的“土蝼蛄”失业多年,听说又有人让他当土地经纪十分兴奋,挣扎着从躺了两个多月的病床上爬起来办理业务。经过半晌午的讨价还价,费大肚子的三亩地以每亩五十三万元成交。大脚的钱只有一百四十万,还差十九万,想了想对费大肚子道:“我再给你一条牛腿行不?”费大肚子算一算,一百四十万够还那个寡妇的债了,而自己正愁没有牛种地艰难,再说大脚家的那头牛也的确值个八十万九十万的,就说:“中。”
接着是写文书,再接着是喝酒。酒钱是买卖两方出,让宁学诗的儿子去割了肉打了酒买了锅饼,几个人就坐到一起又吃又喝。
大脚喝酒喝多了。一则是因为置了地高兴,二则是觉得酒钱他出了一半,如果少喝了就有点吃亏,所以直把脸弄成酱紫色把脑壳弄成一个轻飘飘的葫芦才放下筷子。
费大肚子也喝多了。他眼泪汪汪的,瘪着一张没毛的“嬷嬷嘴”说:“我是个人吗?我不是人呀!天底下找不出我这样的……”
大脚虽有些醉,但这话还是听见了。他打一个酒嗝指着费大肚子的鼻子道:“你懊悔了是不?你懊悔了也无用!文书在咱怀里揣着呢……你不是人?你真不是人!你卖地,那地是能卖的吗?可你卖了!你真不是人!费大肚子你真不是人……”
宁学诗的儿子见他这个样子,便扶起他送他回家。一路上,大脚还是嘟哝不休:“费大肚子不是人!费大肚子不是人……”
到了家中,家明两口子正在院子里逗着小孩玩,绣绣正教枝子做针线,可玉则坐在墙根发呆。大脚从怀里掏出文书向儿子儿媳面前一扔,醉醺醺地说:“看看吧!看看吧!三亩好地呀!都是你们的!都是你们的!你爹不是个孬泥碗子……”
没等儿子儿媳做出反应,他跌跌撞撞去堂屋床上一躺,嘴里还是咕咕哝哝:“你爹不是孬泥碗子!不是孬泥碗子……”咕哝几声,便打着呼噜睡了过去,妻子儿子走过来说了些什么他一概听不见了。
他被闺女急促推醒时屋里已经黑朦朦的了。闺女喊:“爹你快起来,俺小舅跳井了!”大脚乍以为是做梦,等看清枝子的焦急模样后便一跃而起,一歪一顿地向外面跑去了。
跑到井台上,那里已经围了许多人。在往人堆里挤时,他听人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不是跳井,是他自己踏着井边下去的!”
“下去干啥?不是找死?”
“快把他弄出来吧!”
“弄他干啥?一个熊地主羔子,淹死就淹死!”
……
待大脚终于挤进去,发现妻子正趴在井台上。绣绣带着哭腔喊往井里:“可玉,你好好抓住石头,家明去拿抬筐去了,这就来捞你!”
大脚弯腰勾头向下一看,深深的井筒子里是一片黑。看了一阵子,才隐隐约约看见在那井水里,一个脑袋正露在那里,旁边井壁的石头上则有着一双手。他起身把棉袄和鞋一脱,再往下一蹲,人就下到了井里。
天牛庙村总共三口井,位于村中央的这口井最深。因为打水时有时出现铁筲掉到里面的情况,大脚曾下过这井几次。此刻,他分开两腿,用脚尖踩着井壁的石缝,一点一点下去了。他知道,此时井里的水有一人多深,可玉如果不抓住井壁上的石头,肯定会被淹死的。所以他一边往下走一边大声说:“他小舅你千万别松手!千万别松手!”
井筒子越往下越粗,靠近水面,大脚的两腿为了还能够上井壁,已经张开到最大限度。他低头向下瞅瞅,黑暗中,只看得见小舅子那一双发亮的眼睛。奇怪的是,小舅子的眼睛里一点也没有惊慌的神色,就那么仰起来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大脚再抬起头瞅瞅上面,只看得见小而圆的一块光明。他高声喊道:“家明来了吗?快点呀!”
绣绣带着哭腔的声音传了下来:“快啦快啦!——噢,来啦!”
井口上一阵嘈杂,接着就垂下了一个大荆条筐。当这筐降到水面,大脚说:“他小舅,快爬上去!”宁可玉便抓住筐沿往里爬,但爬了几次也没成功,人却差点沉下水去。大脚再向下移动几步,弯腰抓住小舅子的衣裳帮他。这样,像个落水鸡一样的宁可玉终于坐到了筐里,让上面的人吊了上去。随后,大脚也往井口上爬,踩着石缝,一点一点,终于爬了出去。当那双脚踩在井台边的冰溜子上面时,一步一个血印子。
把可玉抬回家,绣绣急忙剥光他的衣裳,把他捂在了被窝里。当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打了半天哆嗦终于平静下来后,绣绣问起他来:“可玉,你是想寻死?”
宁可玉却摇摇头。
“那你下井干啥?”
“不干啥。”
以后再问,便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大脚心里很生气,把绣绣拉到院里说:“不管他,爱咋着咋着!”
正月十八,封铁头再婚所生的儿子出世了。
封铁头和费百岁的寡妻陈桂花是三年前结合的。本来他没打算再要孩子,他想自己有一个儿子在部队上,陈桂花又带来了一儿一女,有这么三个就够了。所以他与陈桂花同房归同房,但定了一个原则:光耕地不撒种儿。因此三年过去,陈桂花这块土地上草蒿没长出一棵。不料去年的二月里,让铁头当年用门板抬去当兵的那个宁大巴写来信,说铁头的儿子封家运在朝鲜牺牲了。紧接着,上级民政部门也来送烈属证,使这一消息得到了彻底证实。
铁头为失去唯一的儿子悲痛不已,一连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只管吃烟。这天夜里,他又坐在被窝里发呆,陈桂花偎到他的怀里说:“你甭难受了,我再给你生一个。”铁头没理她,照旧吃烟。可是以后的日子里女人常说这话,说得铁头终于动了心,从此有意识地改变了房事习惯。过了没几个月,陈桂花果然怀了胎。现在,孩子已经在陈桂花怀里踢腿蹬脚大哭大叫了。
四十七岁的人了又生出儿子,封铁头自然高兴万分。孩子出生的第三天,他特意置了一桌酒菜,把村支部成员宁兰兰、郭小说以及他领导的互助组的几个男性成员都请来吃了一顿。吃酒期间,郭小说与土改女果实生出的六岁儿子自卫一次次来找他爹,每次都必须由吃酒的人在他嘴里塞上一块肉才暂时离开,郭小说挤着疤眼骂:“这个馋痨壳子,我回家揍扁他!”宁兰兰笑道:“你甭揍他,揍你自己吧。你要不是先跟他说这里有好吃的,他能来吗?”郭小说听妇女主任这么戳穿他,窘得满脸通红。
喝足了吃饱了,封铁头便让大家给孩子起名。小说对铁头说:“给侄子起个响亮的名,从小叫到大!别像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铁头呀小说的,有大号也没人叫。”他这么一说,众人都笑。
郭小说搔搔头皮,开始动起了脑子。片刻后他把脖子一拍:“有啦!抗美援朝正紧,就叫援朝吧!”他的话音还没落,铁头脸上立即变得灰了。宁兰兰赶紧道:“这名字不好!咱们这几年不是正办互助组吗?就让侄子叫‘互助’吧!”铁头连忙点头赞许:“好好好,就叫互助!”郭小说明白了刚才自己的失误,这时也打圆场:“互助好!铁头哥跟嫂子就是互助,互助出了互助!”说得大伙哈哈大笑。
众人正在说笑着,只听院门一响,进来了一个披蓝棉布大氅的中年人。铁头看一眼急忙迎了出去:“哟,米乡长来啦?快来喝酒!”不由分说,把他拉到屋里就敬酒。
米乡长是一年前上任的,原来在四区干小学教师。这人有文化,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他喝过一盅,一张长方脸变得严肃起来。说道:“铁头同志,不是我批评你,你可不能光沉醉于个人的喜事,忘了村里的大事。”
铁头一惊,急忙问:“米乡长,村里有啥事呀?”
米乡长说:“你们村里自发倾向很严重,你知道不知道?”
“自发倾向?”封铁头不太明白这个词。虽然他在乡里开会时这个词好像往耳朵里钻过,但其具体含意他不清楚。
见他尚在迷糊,米乡长就直接了当讲了:“你们村又有买卖土地的了,这你该知道吧?”
说到卖地,铁头几个人都明白了。铁头点点头:“是有一户卖的。”
“谁卖的?谁买的?”
铁头几个人就把这桩土地买卖向乡长做了汇报。乡长听后问:“你们觉得这事怎么样?”
铁头说:“费大肚子要娶儿媳妇,确实缺钱,他不卖地还有什么办法?”
米乡长这时拿指头点着铁头的额头说:“你这思想认识水平也太差啦!你就没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共产党分给贫雇农的土改果实又重新丢掉了,中农买去土地,在暗暗地上升,这叫什么?这叫两极分化!这种现象能继续发展吗?”
这些话把天牛庙的三名党支部成员说得都瞪大了眼睛。铁头想一想,心里说:是呀,费大肚子的地真是土改分的呀!他卖掉了以后咋办?还剩下的三亩地,能够一家人吃的吗?要是叫钱逼急了,他说不定还要把地卖个净光!而大脚这个人呢,我可知道他的心思,他是一辈子净想着把家业闹大的。他今年置上三亩,来年置上四亩,时间长了不就成了富农了吗?照这样下去,土地改革不是白搞了吗?
想到这里,这个共产党员头上的汗涔涔而出。他急切地问:“乡长,你说咋办?”
米乡长胸有成竹地说:“甭怕,中央已经有办法了。”
郭小说问:“啥办法?”
米乡长说:“办合作社。”说着,他拿出了一份文件。“中央讲得很深刻,根据总路线,咱们国家不但要求工业经济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也要高涨。可是个体经济,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暴露出很大的矛盾。所以中央要求,下步党在农村的根本任务,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
对于办合作社,铁头早就有所了解。十里街的刘纪顺去年办起了一个,有二十多户参加。这个社办得并不咋样,社里整天闹矛盾,庄稼也没多收,秋后有一些户就退了社。铁头想,几十口子在一起呼呼隆隆的怎么干活,不窝工吗?分粮按地四劳六,地多的能愿意吗?说实在的,他是比较喜欢办互助组的,就那么几家,有牛的跟没牛的,有劳力的跟没劳力的,都出于自愿,就那么一凑合,生产就搞起来了。秋后,谁家地里的归谁,一点也不麻烦。因而,他以前对合作社这种生产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今天经米乡长这么一说,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上去了:哦呀,千万别小看了合作社,它能防止自发倾向,防止两极分化呢!
搞呀!赶紧搞呀!铁头觉得自己必须像当年闹农会那样,立马在天牛庙干出一番新名堂了。
他向米乡长表了态,要以村支部成员为主,开犁之前就在天牛庙办起一个合作社来,争取组织起三十到五十户来!
米乡长听了铁牛的表态十分满意。他说,县上过几天就要办学习班,教给乡村干部办社方法,一村去一个学习的。他今天就是先来吹吹风,通通气,让铁头有个思想准备。说完,他又到王家台村去了。
乡长走后之后,铁头几个免不了又议论了一番。说着说着,刚满三天的儿子在里屋哭起来了。宁兰兰走过去看了看,出来说:“我寻思,侄子别叫互助啦,马上就要办合作社了,就叫他合作吧!”
铁头把脑壳一拍,兴高采烈地道:“好,就叫合作!”
三天后,上级果然发下通知,让铁头去县里学习。铁头背着铺盖卷儿去学了五天,对合作社怎么个搞法有了七八分明白。回来之后,他顾不上照顾还在月子里的老婆,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办社上。
铁头设想的方案是,先把村里原有的五个互助组合并在一起。有了这二十多户,合作社基本上撑起了架子。不料他只说通了三个互助组,另外的两个坚决不干,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意合作社地四劳六的分配方法。几个村干部无奈,便转而在村里动员那些单干的户。封铁头、郭小说带头动员自不待说,连宁兰兰也抱着只有六个月的孩子走东家串西户。
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入社的终于到了三十四户。然而列出名单一看,穷户、缺劳力户占得多,富裕户很少,有牲口的户更少。驴总共九头,牛是七头外加三条牛腿。这样合作社必然出现许多困难,一是劳力不足;二是生产投资难筹;三是牲口不够用的。铁头说:“不行,还要拉一些好样的户。如果再拉进二十户中农就好了。”于是他们又排出了二十户中农,接着再分头动员。
这二十个目标中有封大脚。这是郭小说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封大脚有牛,而他家那头牛的一条牛腿被费大肚子拥有。现在费大肚子已经入社,如果把大脚也拉进来,那么这头牛的四条腿便全是社里的了。而且大脚家有劳力,也能投资,能把他发展过来对合作社是很有利的。另外,大脚刚买了土地,自发倾向十分严重,如果把他弄到社里,大伙镖在一起,就能掐掉他那个自发倾向的芽芽。但铁头了解他的邻居,说:“够呛,他怕是不会入的。”郭小说自告奋勇道:“我去动员!”
郭小说是在第二天早晨找到大脚的。当时他正在接收费大肚子送来的牛草。费大肚子拥有一条牛腿,按说是应该隔一段时间将牛牵回家喂几天的,但他没有牛棚,再说他正忙着为儿子娶回那个寡妇,实在无力建设牛棚。加上大脚也不放心一辈子没养过牲口的费大肚子将牛牵回家去,于是两家协商,让费大肚子送四分之一的草料来,牛还是由大脚一家喂养。这天早晨,费大肚子果然挑来了两篮花生秧。大脚对这份牛草很挑剔,见里边有一些发了霉生了白毛,就一一挑出,一边拣一边说:“表叔,牛是给咱挣饭吃的哑巴儿呀,给儿吃的东西,咱能糊弄?”费大肚子脸上便现出羞容,点着头道:“是,是,下回我好好剔剔!”
就在这个时候,郭小说来了。郭小说向大脚表达了让他入社的意思,当即遭到了拒绝。大脚说:“俺不入。自古以来种地都是一家一户地干,非要伙在一块干啥?”
郭小说又向他讲道理,说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脚说:“俺不信。我三天就能把我的地锄一遍,你社里也能三天把所有的地锄一遍?”
郭小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直接说出了合作社所设想的结果:“还是入社吧!入了社,土地就能增产!”
大脚笑笑:“增不增的,等秋后看吧!”
郭小说问:“你真不入?”
“真不入。”
郭小说看看旁边站着的费大肚子,说:“那么,大肚子叔入了你不入,这牛怎么使?”
大脚道:“按老例子呗,我使三天,他使一天。”
话说到这里,郭小说只好走了。
他沮丧地回到村部,打算向铁头汇报这一结果,想不到党支书的眉头锁成了疙瘩,正蹲在那里边抽烟边骂:“****娘的,怎么净出这样的事?”
郭小说问正在一边给孩子喂奶的宁兰兰出了啥事,宁兰兰道:“又有卖地的啦!”
“谁?”
“腻味。”
郭小说不禁吃了一惊:“他?”
腻味确实将他在当年所领导的“粗风暴雨”式的土改斗争中得到的土地卖掉了三亩,卖得干脆利索。
腻味一共有五亩地,其中包括原来被宁学祥准去土改中夺回的三亩,分到女果实金柳后又多分的两亩。他现在卖掉的,恰是他家祖传的三亩。
大复查结束后,腻味又成了一个什么职务也不再有的普通村民。但不管上级怎么说大复查有错误,也不管他大权旁落之后村里有多少人在恨他在耻笑他,他心里始终荡漾着一种自豪感:老子就是不简单!老子那时是天牛庙村掌龙头的!全村贫雇农的地都是老子给夺来的!你们谁行?谁也办不了咱这样的大事!咳咳!
那些日子里,腻味常做噩梦,经常是一合眼就见那些被他杀死的人带着满脸血污站在他的面前,吓得他猛丁醒来大汗淋漓。更严重的是,在他与土改女果实金柳****时,一旦进入恍恍惚惚的境地,那些死人竟也会闪现在他的眼前,使得他迅速萎掉再也弄不成事。金柳问:“你怎么啦?怎么啦?”腻味不好回答,只能从她身上滚下来躺到一边去喘粗气。后来经过多次这样的事,也经过金柳多次问询,腻味便说了实话。金柳道:“你看你咋不早说?俺有办法。”腻味问啥办法,金柳便告诉他,把那把杀人的铡刀取来放在枕头底下,那些死鬼就不会来了。她还说,这是她那死爹用过的法子,那年她爹打死过一个烧火丫头,事后常做噩梦,她爹把打死那丫头的棍子放在枕头下就没事了。腻味听后立马照办,将那把还能嗅出腥味的铡刀放在枕下,果然见效。从此以后,腻味就从从容容地跟金柳交欢,从从容容地入睡。白天,便用他当年在东南乡扎觅汉练就的做农活的本领,一本正经地侍弄自己的土地。七年下去,他与金柳养出了三个闺女,家中也有几十万元的积蓄了。
然而,他现在却把地卖了。
他萌生卖地的念头,只是年后半个多月的事。费大肚子卖地,米乡长到铁头家里提出批评,同时又传达上级关于办社的指示,这事经在场的几个普通庄户汉子的传播,很快让全村都知道了。紧接着,铁头从县上培训回来,热火朝天地办社,这一切都引起了腻味的注意和思考。他想呵,想呵,这一天终于悟出:啊呀,共产党这是又要办大事啦!不是整天叫喊着学苏联么?咱听说过,苏联人种地就是办集体农庄合大伙的,那么中国还不也走这一步?
这样,土改分的地当然要合在一块儿。共产党能分给你,也就能从你手里再拿回来。唉呀,这样的话,咱还不赶紧卖点钱花花!
想到这里,腻味有了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但他不愿将他的思考成果告诉别人。他要独享这一成果。他想让人们继续闷在鼓里。看到他的大脚堂兄新添了地意气风发的样子,他捂着嘴偷笑不止。与此同时,他也在村里开始寻觅像堂兄那样的傻帽。
悄悄问了几家,他的地便有了买主。那是住在后街的中农费文财,他父子三个都正壮实,正怨有力气没地种,听说腻味要卖地,而且一亩只要四十万,当即就揽下了。
写地契还是去找宁学诗。这个“土蝼蛄”此时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七八天不进汤水了。可是一听说让他写地契,一双眍娄下去的小眼睛立马又放出光来,嘶哑着声音让家里人研墨。而后,他听完买卖双方讲清地的亩数、位置和价格,便趴在枕头上写了起来。写几个字喘上一会,写几个字再喘上一会,好半天才将那张文书写毕。待他写上自己的名字,脑袋却像叩头似地突然一垂,就抵在文书上不动了。在场的人看他这样,急忙把他翻过身来,但那口鼻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人们方注意到,宁学诗的脸上沾满了黑黑的字迹。那些字都是反着的,且都模模糊糊,看了一阵,才看出了两个字:一个是“最”;一个是“后”。
二月初一,天牛庙开天辟地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大会是在村前铁牛旁边的空场上召开的,除了三十八户社员,封铁头让其他村民也参加大会,目的是受受教育,激发大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然而社外群众来得不多,也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样子。他让郭小说去村里催了几遍,也没见出多少效果。
会场上有一人显得十分活跃。他就是腻味。腻味卖了地之后也找到封铁头表示要入合作社。铁头生气地说:“你把地卖了又要入社,这不是占便宜么?”腻味说:“那地我想卖吗?我老婆有妇女病,整天吃药,我不卖地咋办?你不叫我入,我剩下的二亩也可能保不住。”铁头一听情况严重,心想,还是让他入吧,不然他又成了穷光蛋啦。便批准了他的入社要求。在今天的会场上,腻味走来走去吆吆喝喝:“入社好哇!毛主席叫干的事没有错!没入的赶紧入呀!”
亲临大会祝贺的米乡长注意到了腻味。他问铁头那是谁,铁头如实以告。社乡长说:“看来搞合作化还是贫雇农积极性高,你们要把这样的积极分子用起来!”
成立大会的议程是宣布合作社成立;敲锣打鼓放鞭炮;米乡长讲话;社长封铁头讲话;社员代表讲话;通过合作社章程;最后是社员们牵着所有的牲口下地开始春耕。
大脚的牛也被牵到了会场。因为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天要显示一下声威,社里就让费大肚子去牵牛。大脚起初不肯,说我家才耕了一天的地你就要使牛呀?别忘了你才有一条牛腿!费大肚子道:“社里不是想今天好看吗?你就让给俺一天吧!”大脚这才委委屈屈地让他牵走了。
村前的会议大脚是接了通知的,但他没打算去,同时也没让儿子去。然而当牛被费大肚子牵走,他却忍不住跟到了会场。会上都讲了些啥他一概不关心,只是蹲在那里看着牲口群里那头被他叫做“黑大汉”的犍牛。这个“黑大汉”,这头他喂养了六年的牛,今天却要去耕不属于他的地了。他不能容忍这一点,所以一边看着一边心疼。
当会议结束,那头牛让人赶着去了南岭时,他觉得自己的魂也让人牵走了,只留了一具肉身子木木地蹲在那里。
整整一天,大脚都是失魂落魄,连午饭也没能吃下。从南岭那里传来的牛鞭响声,声声让他觉得是打在自己身上,声声让他心悸。
好容易盼到天黑,费大肚子把牛送了回来。他接过缰绳,便手抚牛身仔细审视起来。看到牛屁股上有几道白白的鞭痕,便拧着脖子大声嚷:“你们把它往死里打呀?”费大肚子道:“没怎么打呀,你看也没出血。”大脚说:“还得出血?出血就毁啦!”费大肚子说:“大侄,我知道你心疼牛,可是这牛也有我一条牛腿,我就不能用啦?”大脚想了想说:“不行,我得把你这条牛腿抽回来!”费大肚子听大脚这样说,便道:“你愿抽就抽,可是你得给我钱!”大脚说:“当然要给你,我去借,三天以内给你!”
话这么说了,大脚决定立马借钱抽回这条牛腿。他心里说:我可不叫我的牛腿插到合作社里。牲口到了社里,谁使都行,谁还爱惜不是自己的牲口?今天这牛身上没见血,但是保不准明天就能不见。还有,他们使起牛来,中间歇不歇?要歇的话,时间长短?能等到它开口倒磨再用?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的!
想到这里,大脚抽回牛腿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但他已经将积蓄花光,这笔钱只能去借。找谁呢?他想到了费左氏。她家只有婆媳二人,钱是肯定有的。他便向绣绣说了这个打算,让她出面找苏苏去。绣绣起初不同意丈夫的做法,说咱家手头正紧,那牛也余着力气,让人家用几天也没有啥。可是大脚坚持要抽,绣绣只好去了妹妹那里。
到了妹妹家,那门却久叩不开。她喊了几声妹妹,费左氏才迟迟疑疑打开了门。到堂屋里坐下,绣绣把事情一说,费左氏很痛快地就把四十万票子拿给了她。绣绣道了谢,想起有好长时间没见妹妹了,便要去东厢房看她。费左氏莫名其妙地红了红脸说:“你去吧。”
苏苏正倚坐在床头发呆,见姐姐进来她也是满面含羞。绣绣觉得蹊跷,便拿眼打量妹妹。这一打量便打量出一个让她吃惊的事实:妹妹的肚子大了。她急忙问:“苏苏你这是……”苏苏羞笑道:“有男人的时候没有孩子,没有男人的时候倒有了孩子,姐你奇怪了吧?告诉你吧,已经六个月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家里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