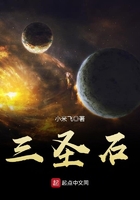墓地是什么样子的?
孤寂?悲凉?伤感?还是生死两隔的落寞?
简单的小土包里埋着曾经活过的人,上面正正方方的岩石雕刻着简单的几个字。
仅仅过了几日,尚且血肉丰满的亡者可能还在留恋着世间不肯离去,拿贪婪悲切的目光注视着陌生亦或熟悉的地方,回忆着曾经的过往。
过上几月,几年,几十年。不过空余一具白骨,一把黄土,一块磨灭了字迹的石碑。可能保持着坟墓的形状,也算得上一种幸运。
死去,还能留下什么?
又有几人能在经年的岁月中留下曾活过的痕迹?
若是亡者故去,还有生者铭记,就当死而无憾。
鸠酒堂的杀手,在第一次动身进行暗杀之前都会被他们的师父领到这里聆听简短的几句话:
这是你们前辈埋葬的地方。
你们的尸骨如果可以被找到就会被埋在这里。
记住这里,你们死后就不会因为陌生而感到恐惧了。
像是蛊惑,却又直白到极致。
看着眼前的新坟,不知为何,青衣公子心中凭空出现了一个词:归家。
鸩酒堂是他们的“家”。能埋在鸩酒堂的墓地中,他们至少在死后回到了家。他们的身边躺着与他们度过了极为相似的人生的先来者,或是后来者,又或是……死前并肩而立的同伴。
在这里,似乎连风都是悲凉的。
杀手生于死亡,活在死亡之中,又结束于死亡……
青衣公子勾唇一笑:“你怎么看?”
影子立在他身后一步远的位置,闻言反问道:“主子是问什么?”
“血月……还有流沙。”青衣公子眯目看着刻有“血月”两个字的墓碑,若有所思。
影子稍稍沉默:“我觉得主子处理得很好。”
青衣公子看了他一眼,又转回视线:“那样就可以吗?这次是因为血月已经死了,浅痕又受了重伤,加上流沙本来就不能杀才如此了事……再有下回可就麻烦了。”
影子淡淡道:“下回直接杀就好。”
青衣公子低声笑了笑:“说的在理。”又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的伤怎么样了?”
影子道:“已经没有大碍了。”
青衣公子抬手摸了摸身前的石碑,轻笑道:“凉的。”
影子道:“石头自然是凉的。”
青衣公子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是啊,石头的确是凉的。”
影子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没有明白青衣公子的意思,所以没有答话。
青衣公子手指在石碑上轻敲着,唇边仍旧留有一丝笑意:“丐帮的人活下来几个?”
影子道:“除了副帮主蒋随和在傀儡宫后山山下等待的那些文启华的心腹,剩下的人已经尽数死亡了。”
青衣公子问道:“你能确定?”
影子点点头:“属下传信给钟离婴,让她带人分两路前去,一路去傀儡宫暗宫救急,一路至傀儡宫后山等待丐帮残众下山。钟离婴截下了所有下山的丐帮残余,只了蒋随一个人。依照风琼的回禀,她是在亲眼看着莫哭打开了后山机关中枢之后才离开的。”
青衣公子满意的道:“做的不错。”在青衣公子需要万无一失的时候给出最全面的回答,在青衣公子只需要结果的时候将事情迅速完成好再视情况汇报——这就是青衣公子对影子的要求。
影子神情平淡,继续问道:“主子准备如何处置蒋随?”
青衣公子转身面对着他,沉思道:“原本的打算是让浅痕易容为重伤的蒋随与文启华一起回丐帮。但浅痕现在伤成这样,显然不可能让他去了。只能让轩辕阴替他了吧?但是……这么一来冥谷少了浅痕,又少了轩辕阴,单凭宫诡一个人,想约束住整个冥谷就更吃力了啊。傀儡宫擅长易容的人倒是不少,但现在还没有可以信任的人选,也只能作罢了。”
影子道:“属下有一人推荐。”
青衣公子一怔,问道:“谁?”
影子道:“流鸢。”
“流鸢?”青衣公子思索片刻,“他会易容?”
影子道:“他是魔晕的亲传弟子,鸩酒堂里除了魔晕应该就属他的易容术最为高超了。流字堂本身就是辅佐其余分堂的存在,虽然流鸢是堂主,但有流沙这个副堂主在,流字堂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青衣公子问道:“他和浅痕相比,谁的易容术高?”
影子道:“可能浅痕要稍胜一筹,但流鸢的易容术肯定要强于轩辕阴。”
青衣公子唇角的弧线调的更高了几分:“可以,那你就去安排吧,到时候一定是一场好戏。”
影子微微躬身:“请主子放心,这次绝不会出现任何差池。”
青衣公子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又转回了身:“我想再待一会儿,你先去吧。”
影子低声道:“是,属下告退。”退后两步,转身离开。
————————————————————————
“流鸢!你怎么可以同意?”流沙推门冲入,含怒出声。
流鸢的目光从掌心捧着的玉盒上挪到流沙的脸上,淡淡反问:“同意什么?”
流沙道:“易容成那个丐帮副帮主啊!先不说你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就说你要伪装成蒋随就要把自己弄的遍体鳞伤啊!”
流鸢笑了:“你为什么要咒我失败?”
流沙深吸一口气,仍旧满面愤怒:“你为什么要同意?将功折罪也应该是我受罪,凭什么要你来替我受罚?”
流鸢道:“你会错意了,我不是替你受罚,这不是惩罚。而且就算是惩罚,我也该受罚,和你没关系,不要把事往自己身上揽。”
流沙问道:“怎么就和我没关系?你是陪我去的啊,要罚他应该罚我!”
流鸢低低笑了几声,眼中带着嘲笑:“你会易容?”
流沙不禁一怔,呆呆的看着他,没有说话。
流鸢轻叹口气,悠悠道:“流沙,你莫忘了,咱们是鸩酒堂的杀手啊。不要因为咱们待在流字堂负责这些档案和任务分配用不上武功,就忘了自己的本事。更不要忘了,杀手,首先是服从主子的命令,其次才是顾忌自己的想法。”
流沙哑声道:“我……”
流鸢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话中不无惋惜之意:“再这样下去,血月会失望的,堂主更会失望的。公子会如此简单的放过你,是因为堂主冒死求情,更是因为你是宫诡和浅痕的师弟。但再多的理由,也抵不过一句‘你还有用’。如果你真的这么颓靡下去,忘了自己是谁、该做什么,那你就真的废了——你应该知道鸩酒堂里废人的下场。就算不为你自己,你也要想想,流字堂的副堂主因此被处理掉,整个流字堂将会面对什么?我这个分堂主将会面对什么?你的师父,咱们的堂主将会面对什么?”
见流沙扔在呆愣,流鸢顿了一下,继续说了下去,声音极轻:“堂主养育了你近二十年,如今鸩酒堂正是危急关头,你就准备这么弃鸩酒堂于不顾?你就忍心看着堂主最在乎的鸩酒堂满目疮痍而犹自神伤?我愿意陪你一起请求公子让你再见血月一眼,因为我知道你在乎她。但如果你在答应公子之后还是如此模样,那我,会恨你。”不再说话,退开一步,然后转身离开。
你是宫诡和浅痕的师弟。
堂主养育了你近二十年。
满目疮痍。
那我,会恨你。
字字诛心。
十八年前,流沙八岁。
师父生性冷漠,不苟言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苍白到极致的脸色,眼中无情无欲,犹如死人。
而流沙的两个师兄,一个灰衣,一个白衣,与他年纪仿佛。
大师兄很爱笑,笑容中时常带着几分捉弄。但他并不爱捉弄人,反而经常掏掏鸟蛋,下水摸鱼,或者去抓野兔野鸡,全都裹上泥拿火烤。烤完了把东西分成三份,然后一起吃。包括师叔们那些弟子在内的人中,他是唯一敢笑出声的,还敢偷偷跑出去胡闹玩耍,在大白天四处走的。奇怪的是,没人会阻止流沙,更不会骂他。
二师兄也会笑,但并不常笑。他在笑着的时候,眼中的神情会显得格外落寞和悲伤,却又显得很温柔。他一直跟在大师兄的身后,在树下仰望着掏鸟蛋的身影,在河边等待着摸鱼的人,在火堆边撑着脸看着对过于肥大的兔子无从下手的师兄……
二师兄一直跟着大师兄,而大师兄也愿意带上流沙。在习武之外的时间里,流沙非常喜欢黏在师兄们身边,因为师兄们比冷冰冰的师父要好多了。
流沙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师兄作为一名杀手是什么样子——或说,流沙足足等了五年,才知道。
十三岁的少年咱在满地尸身之中,被鲜血染红了大半的脸颊使唇边的笑容和眼中的笑意被并不明亮的火光映照的分外明显。那笑容是带着几分作弄却分外令人心安的笑容,眼中的笑意是伸手帮自己擦去嘴边油腻时有几分宠溺的笑容。
而他身后不远处的另一名少年则蹲下身,唇边噙着温柔的笑意,侧耳倾听着脚边那将死之人喉咙里艰难吐出的隆隆声,然后用分外温柔的声音吐出一句:“多谢了。”将手中的钩子钉入脆弱的喉咙。
钩子拔出,血将白衣打湿了不少,少年不满的嘟囔。而灰衣少年回头看向他,笑着说了什么。
树丛后的流沙早已无心去注意流沙的师兄说了什么,只顾狂奔着离开,在陌生的树下拼命的呕吐,然后彻夜难眠。第二日天色发白,流沙蜷缩在棉被中不肯起床,更没有如往常一样开心的去找流沙的两位师兄共享早餐。
流沙不去,但流沙的师兄却自己过来了。同样的笑容,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目光……自己在师兄们的眼中,和那些死去的人,有什么区别?
师兄的身上有很轻微的腥气,血的腥气。
问到味道的流沙用力推开师兄,用棉被捂住头。但师兄的声音还是传到了流沙的耳中:“看,兔子血弄到身上的味道又让师弟讨厌了吧?”
大师兄的声音勾起了流沙记忆中的战栗。
漆黑的夜,白衣的少年看着身上的血迹不满的嘟囔:“这下又留下味道了。”
灰衣的少年回首一笑:“怕什么?和他说杀兔子溅到身上的血就行了。”
记起来了……昨夜震惊中没有注意到的话……
流沙丢开被子,疯了似的赤足跑了出去,用尽全力的奔跑,只想逃离。
他没有回头,但他也知道,看着自己跑远的师兄,已经知道了原因。
他们,会对自己失望吧?
流沙以为他的师兄会追上来。
但是没有。
从那一日开始,流沙开始明白什么才叫杀手。
流沙也开始知道,师兄不让他接触杀戮,不代表他就可以一直像个孩子一样只知道黏着师兄爬树摸鱼。
作为一个杀手,却因为见到了鲜血和死人而反胃呕吐,多么好笑?
同样的年纪,他有什么资格让师兄来迁就自己?
真正残忍的是欺骗,而不是告知现实。
“别忘了,你的师兄还在后面躺着,生死未卜。而你却在为一个已经死掉的女人失魂落魄。”
“堂主养育了你近二十年,如今鸩酒堂正是危急关头,你就准备这么弃鸩酒堂于不顾?你就忍心看着堂主最在乎的鸩酒堂满目疮痍而犹自神伤?”
“那我,会恨你。”
……
流沙猛然惊醒过来,环视着周围,额头上惊出了冷汗。
作为杀手,却在为情所困。
自称有“情”,却弃师父师兄的努力和付出于不顾。
作为副堂主,却不顾堂中数十人的生死存亡。
这算什么?
自私,自欺。
流沙忍不住坐到在地,肩膀微微颤抖,脸色因为巨大的惊愕而变得雪白,大滴的冷汗不住的渗出。
直到此时,流沙才真的醒了。
一步错,犹可改,步步错,无可改。
好在他醒了,就不会再继续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