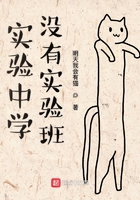喜子一进门,二话不说,“扑通”跪下了,我吓了一跳。这喜子可是我的爷,是给我交租金的大爷,什么事把他给难住了?堂堂一个一米八六的男子汉,怎么说跪就跪下了。我连忙过去搀扶他,嘴里吐出几个字:“喜子,你有啥说啥,别这样,快起来。”
“王经理,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不会起来。”喜子发狠地说完,头也不抬。
“出了什么事?老弟,非要跪着才行?”我看着眼前的喜子,心里猜想可能出大事了。
喜子原来是对面电视台的副台长,大名张贵喜,在镇里几乎家喻户晓,年轻时扛着个摄像机在镇里录像,晚上当地新闻的那几个画面基本都是他拍的。上了年纪后,机子扛不动了,活动活动当了个小编辑,加上能说会道,把个领导哄得挺舒服,最后不知啥时候别人都叫他张台长了。而我一直叫他喜子,虽然他职位有变,但这小子脸上一直有股喜气未变,无论见谁,他都露着牙笑嘻嘻,即使没高兴的事,也会把你给逗乐了。
临近退休了,喜子无事可做,不知何时与大头鱼较上了劲,在几个哥儿们的簇拥下吃了几次还行,脑子一热投资了一个鱼庄,他说这大头鱼特别好吃,一定有市场。这不租的房子正好是我公司的铺头,要不然我怎么会说他是我的大爷,这年头顾客是上帝,上帝不就是大爷吗?
前一阵我听说鱼庄开业了,生意兴隆,按规矩我代表公司还送了一个红包助兴,怎么还没过几天,喜子就跑来给我下跪了,难道是鱼庄出了问题?这对付吵架骂街我这几年学了两手,可对付下跪的人,我还真没辙,我只有照猫画虎地学着凶起来。
“喜子,你他妈别跟老子装蒜,有事说事,有屁就放,你再这样耍死狗,我可只有走了。”
“你别走,千万别走,王经理,我说,我说。”说来也怪,这人真欠骂,让我这么一咋呼,喜子站了起来。
喜子一站起,屋子里的气氛温暖了许多,我亲自给他斟满茶,听他开始倒苦水。喜子不愧是东北黑土地人,话匣子一打开,苦水就像松花江的波涛,哗哗地滚滚而来。
原来喜子鱼庄开业不久,大伙儿正在为生意兴隆开心,不料遇到难事一桩,从水库拉来的大头鱼莫名地连续死亡。这一条五、六斤的鲢鱼,成本很高,喜子找了多名高手会诊都无济于事。急得喜子满嘴生疮,几天下来,他的脸变得真跟喜字差不多了,全是褶子,十分疲惫。喜子几经折腾,最后求教到本地的一位垂钓者,一个有着丰富养鱼经验的老人,他告诉喜子这是水土不服,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让鱼喝上地下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鱼的小命。
这说者容易听者可难了,到哪找地下水去?喜子也算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可要得到一处地下水,还要永续使用,这真让他犯难了。眼看着池子里面的大头鱼翻着白眼纷纷死去,喜子急得真想也跟它们去了。这才引出了前面的一幕,一大早他跑进我的办公室,一句话没有,“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喜子讲完了,我也明白了,看样子这下跪的目地很明显,他是讹上我了,想让我在小区里帮他找地下水,说白了,就是帮他打口井。这会儿可轮上我犯堵了,喝光了茶杯里的茶水,也说不出一句话。这不答应他,有点张不开口,答应他,可是狗撵耗子多管闲事,这是哪和哪啊?岂有此理,今天他开鱼庄,我打井,赶明儿再碰一个租客是做羊肉汤的,我还得给他圈一块地,让他种草遛羊?
话虽这样讲,但也不能见死不救,我拿出了自己敷衍的真本事,我告诉他:“喜子,这弄地下水就得打井,而打井的事可不是小事,不但需要花钱花人力,关键是政府要批准,你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如果仅仅是死了几条鱼就要打几十米深的井,恐怕报批的理由显得太牵强。喜子,你也算是半个政府的人,你觉得这行得通吗?”
“王经理,你是我大爷,千万不能等政府批,我太了解那些老爷了,等他们婆婆妈妈扯来扯去,我的鱼早死完了,我的鱼庄也倒闭了,最关键的是你的租金也泡汤了。王经理,我们只有今晚偷偷地、快快地在小区找个隐蔽的地方打个井,把水引到我的鱼庄,一切就有救了。”喜子两眼放光,一口气陈述了他的方案,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方案,估计他跪之前就想好了。
看我一时没有了主意,喜子的声音更大了。“打井的人我去找,一切费用我来负责,您只要答应就行了。”说完他递上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明眼人知道,那是答应费。“王经理,这是我的心意,等事成之后,一定另当感谢,另当感谢。”我认识喜子多年,他的这种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谁说男人有泪不轻弹,这男人有钱也不轻弹啊。
当天夜里,一群人在小区荔枝园里忙碌了一个通宵,一口深达三十米的水井在凌晨终于打成了,因为安排的隐蔽,小区里竟然无人知道这回事。当看到地下水流到鱼庄的时候,喜子比鱼还活蹦乱跳,脸上仿佛出现了双喜的字样,很明显,一个喜是为自己,另一个喜当然是为了他的大头鱼了。
我本想着这井打好后,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没想到一个月后鱼庄又出事了。这回是喜子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一个鱼庄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王经理,请坐,这里条件不太好,说完事咱们出去喝茶。”
“有什么事这么急?还不能一边喝茶一边说嘛?”
“外面不太方便,来,给你看一样东西。”说完,喜子拿出了一封信递给我。
信封的落款是市技术监督局的字样,我从皱皱巴巴的信封里抽出信,看完顿时傻眼了。我一连再扫了两遍,望着喜子,战战兢兢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好不容易想出一句安慰的话,刚欲张口,喜子打着手势坚决地制止了我。
“你刚进来时,看到门口的那个胖女人,就是准备接手鱼庄的新老板,再过几天我会找你做转让手续,你放心,租金不会欠你半分钱。”喜子语气沉重但很客气。
“鱼真的全完蛋了,这水真的不能养鱼?”我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算你会算,我的王经理,这里今后真要改羊庄了,是海南东山羊,但他们那些人不像我,以后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对我的问话,喜子没有正面回答,反而是安慰我,不要为租金担心。
“喜子,这事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太大了。”
“王经理,今天叫你来,是请您帮我最后一个忙,这地下水的事你要烂在肚子里,和亲娘老子也别说,否则我不但丢了党票,可能连退休金也没有了,而你也会因此遇到麻烦。”
“你放心,喜子,我从来不知道打井的事,不,我根本就没听说有人打过井。”我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听得别扭。
从喜子那儿回来,我一直不踏实,说不出什么理由,总觉得这事很蹊跷,难道这打井的事被人捅上去了?可怜的喜子,你好好的为什么要和大头鱼较上劲?
第二年的春天,我曾几次从打井的地方路过,奇怪的是井口的周围,渐渐长出了叫不出名的野山花,它们的样子很奇特,外观颇似大头鱼。开始一点点,后来一大片,都是红色的花瓣,极为茂盛,也极为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