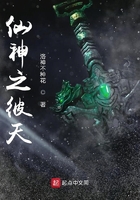第二天阿黄娘跑到公社门口的邮电局去拍电报。这一回阿黄的病,把她吓破了胆。不管怎么说也得让她爹回来看看。但万没有想到,相隔千里之遥的父女俩竟然患上了同一种病,几乎是同时做的手术。接到电报,齐德贵硬是从病床上爬了起来。他回来后,阿黄已经出院了,睡在自家的炕头上一脸憔悴,看上去十分羸弱。齐德贵叹口气,想给他的独养女儿找个伴,她太孤单了。阿黄娘说也好,一来她有个做伴的,二来是家里以后没个劳力也不行。所以,她家里就来了个玉哥哥。玉哥哥是老牛岭往东再上二十里山路,一个叫做老鸦圪嘴的小山庄上一户人家的孩子。因家口太大养不起,才把这么大的孩子送了人。玉哥哥来的那一年阿黄8岁,他9岁。可是这个玉哥哥却偏偏不争气,每晚都尿炕。渐渐地,母亲厌恶极了他,阿黄也厌恶极了他。母亲脾气一不好的时候就开始打他,越打他,他就越尿炕,越尿炕,母亲就更加倍地打他,如此反复成了恶性循环,屋里整天臭气熏天。阿黄不再和他一起玩耍了,玉哥哥整天胆颤心惊,如鸟窝里摔下来的一只受伤的小雏鸟,很是恓惶。三扁那时候和三狗子同岁,正好上了三年级。她好像天生喜欢恶作剧,用从学校偷回来的粉笔,在玉哥哥的背后,那件蓝色的粗布小褂子上,横七竖八划了几根粉笔线,非常醒目。三扁很是得意她的杰作,在院里跳着喊:
“噢——快来看玉生穿上花衣裳喽!快来看喽……”
阿黄娘看到这情景非常生气,她不敢招惹西屋这一家,就冲上去劈头盖脸打了玉哥哥一顿,骂他越长越草包,顶不了门立不了事,要你做甚?滚吧,滚回山上去!没多久,母亲便捎了口信,玉哥哥真的被他亲父母领回去了。谁知他回去后不久,竟然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一下,牛岭村里流言四起,说人家活蹦乱跳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说死就死了呢?肯定是被阿黄她娘打坏了……
一时间,阿黄娘成了牛岭村最恶毒的女人。
16.恶语伤人六月寒
阿黄娘要带着阿黄走了。这个消息对于三狗子好比是当头一棒。他闷头生了半天气,之后,就躲在一棵桑树上哭。他这一哭,被正巧路过的赵大锤碰上了。赵大锤说:哎哟,赵大年的三公子,怎么爬在桑树上哭呢,想吃桑葚了?没桑葚就回去吃你娘的奶。反正赵大年也不吃,闲得都快生锈了。”赵大锤哼着小曲儿在一旁讪笑。他话里有话,不过料定这小屁孩也听不明白。可是三狗子是谁呀?跟个人精儿似的,他可不是好惹的。
只见三狗子从树上“哧溜”一声滑下来。抓了把土就扬了过去,嘴里骂道:叫你老狗再龇牙!”
赵大锤被土迷了眼,边揉边骂:小狗日的,敢扬老子一脸灰,我看赵大年野地里下的种还真是没出息!”
三狗子更不示弱:你娘养你有出息,也别跑到玉茭地里让人摁住屁股呀!”三狗子小时候赖的很,一出口就知道捅他的痛处。
赵大锤这下更恼了,心说这小狗日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竟然也敢揭老子的短,看老子不收拾你!他撸胳膊卷袖子的架式活像个恶狗要扑食,三狗子一看他要动真的,撒开丫子就跑,一边跑一边扭头喊道:老杂种,等过十年小爷爷再跟你斗!”
三狗子呼哧呼哧跑回了家,把院里的小板凳和鸡食槽子踢得满地转。他娘一见拿个笤帚疙瘩就冲了过来:你撞见鬼了啊?发什么邪火,闹得家里七神不坐,六神不安的!”“七神不坐,六神不安也是被你搅的!”三狗子瓮声瓮气恶狠狠地冲着他娘大吼。
三狗子他娘近来喜欢骂人,是受了西屋娘娘的煽惑。西屋娘娘对她说:怕赵大年打你,明的不行就来暗的,你就不会比鸡骂狗?这天底下只有拾银钱的,哪有拾胡疙嗒的(胡疙嗒,指骂人的话)。只要你不指名道姓,她阿黄娘,还不是哑巴吃黄连?”
三狗子他娘对西屋娘娘的话是言听计从。西屋娘娘也像个搅屎棍一样从中添油加醋。说赵大年每次去堂屋,她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常言说,篱笆扎的紧,野狗钻不进。”常言又说了“母鸡不嗒声,公鸡不跳墙!”
听了西屋娘娘的一顿挑唆,三狗子他娘更是对阿黄母女恨之入骨。自打那以后,阿黄母女的耳根就再没有清净过,只要是赵大年不在的时候,三狗子他娘是比着鸡也骂、比着狗也骂,最后一鼓劲儿跳着脚骂,直骂得阿黄娘见了她就躲。可偏偏是针往哪里钻,线就往哪里穿。三狗子他娘有几次撵到堂屋门口,说我告诉你养汉的,这风不吹,树不摇,虱子不咬人不挠。我骂你也不屈你,都是你自找的。阿黄娘觉得自己就跟那过街的老鼠一样,总是难逃西屋娘娘和三狗子他娘的羞辱。好几次她都想把心里受的委屈告诉赵大年,可要是依着赵大年的脾气,三狗子他娘免不了又得挨一顿毒打。这样一来,和三狗子娘的仇不是越结越深了吗?终于有一天,阿黄放学回到家娘跟她说,咱们走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17.飞机飞机落落
阿黄娘领着阿黄走了。
这几天三狗子他娘进进出出嘴里总是哼着一句上党梆子的唱词,那是县剧团来村里演出《三关排宴》时她学会的唯一一句:你好似糖葫芦撒上胡椒面,辣不辣来甜不甜。”虽然她唱得走腔走调,虽然不久前她刚刚被三狗子他爹痛打了一顿。可她还是在心里说:这顿打挨得值!值啊!要不然不光是老的看不住,就连小的迟早也得跟着学坏!”在她看来,她13岁的儿子和只有11岁的阿黄之间,就像两只小猫或者是两只小狗藏猫猫一样,你说一对乳臭未干的小孩儿,他们究竟能懂得什么呢?
那的确是一个眼里没有杂质、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年龄。那些最童贞、最纯洁、最质朴的语言,不掺杂半点世俗的污垢。两颗幼小的心灵好像游离于这尘世之外,是那么的超然,却又是那么的万般不舍。
那一天临分别的时候,三狗子不死心,总是追着阿黄问:狗妹,你还会回来吗?你一定要回来。我给你上树摘核桃,我给你上山去摘马梨蛋蛋,我给你用柳叶桃的花朵染指甲,我给你下河去逮螃蟹,我给你……”三狗子急切地想把那种无穷无尽的不舍表达出来,就像山中顽强的一颗小树,伸展出的一枝一叶都含着愿望的果实,是那样饱满而执着。半晌,没有等来他期待的回应,头顶上的几只麻雀啾啾啁啁的就把这一刻的心绪啼乱了。这时候,他猛然发现站在他面前的阿黄嘤嘤地说不出话,在那里扑扑簌簌往下掉眼泪。这让三狗子顿时感到呼吸有些不畅,并且越来越不畅,胸里憋涨得如同一只被爆吹的琉璃瓶,嘭嘭”一呼一吸就裂了,给他小小的心上留下了第一道伤口。
这个冬季,阿黄戴着那对美丽的蝴蝶结离开了他。他撵到村口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喊了一句:狗妹——明年马梨开花的时候你就回来……”
没有阿黄的日子,变得好无聊好无聊。夜,如此漫长、寒冷。每天晚上,三狗子躺在和阿黄一起睡着过的大碾盘上数着天上的星星: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钉上银钉数不清……”数着数着他就烦了,开始“嘛——咕——嘛——咕”的装鬼叫。
五豆子时常被他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回去告诉三扁说:“姐呀,大磨道的碾盘上睡了个鬼。”三扁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四扁和五豆子一起来到磨盘跟前,抓住脖领就想往起提三狗子,三扁说你黑天半夜装甚鬼呢?三狗子一把将她推开说:关你屁事?”
气得三扁说你除了会放屁,还会干甚?三狗子还是不理她。到了第二天照样睡在大碾盘上,遇见天上有飞机飞过的时候,就喊:“飞机飞机落落,下来让我坐坐。”逗得三扁直发笑。说:活该,狗妹走了,没人跟你耍,真活该!”
三狗子说:关你屁事?”
三扁又问:你老护着她作甚?你娘给你们定下娃娃亲啦?”
“关你屁事!”
三扁一听他又是这一句,就愤愤地骂道:你就是个放屁虫!”
18.住窑洞的是“老临”
其实在阿黄第一次踏上异乡的土地时,让她感到满目荒凉的,不是大西北那广袤无垠的沙漠,而是心与心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
大字不识的母亲,是怀揣着一个信封带着她来的。离开兰州站坐上了一路颠簸的客车,窗外掠过的一切,都让她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这里没有故乡的苍松翠柏,没有清澈的河流。只有扬起的沙尘,像是代表着大西北在欢迎着每一位匆匆而来的旅人。透过车窗,阿黄发现道路两旁大片大片的土地上都铺满了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阿黄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母亲。母女俩惊讶地隔着玻璃往外看去,除了铺满石头的土地,一闪一闪从窗外掠过的还有围着花格子方巾的红脸蛋女人。这都使刚走进大西北的阿黄产生了好多疑惑,而这些疑惑,在以后的日子里阿黄才明白,原来在土地上铺鹅卵石是为了提高土壤的温度,增加昼夜温差,尤其是瓜地,还可以提高瓜的甜度。另外,沙石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水性,对于治理含盐碱性较大的土壤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甘肃的女人为什么都是红脸蛋,那是由于西部地区太阳光线强烈、日照时间长、空气干燥、接受紫外线多等因素造成的。
阿黄爹住的地方,是被两座山头夹着的一个山沟沟,沟两边全是窑洞。阿黄对这个新家极为不满,撅着小嘴说:放着咱家的大堂屋不住,偏要跑来这里住窑洞!”阿黄打心眼里不满意这一次的西北之行。
爹并不理会她的心情,乐呵呵地说:住窑洞好啊,住窑洞冬暖夏凉,你看这一沟子两边住着好多人呢。”
这里的窑洞,虽说比她们家的大堂房差远了,不过学校还算漂亮,是在一座三层楼房里,阿黄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楼房。上学的第一天她就惊奇地发现,她们班主任老师也是个红脸蛋,当她走近的时候,能清楚地看见她脸蛋上的毛细血管,觉得她的脸皮薄极了,那些细小的血管随时都可能穿透皮肤渗出血来。她说一口半普通半夹杂着甘肃方言的话,让阿黄听起来很吃力。放学的时候,老师对她同桌的女学生说:方萍,齐萧雨是新来的,放学后,你跟着去看看她们家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每天帮助她按时完成作业。”
在回窑洞的路上,经过了大约三四排的红砖瓦房,方萍向她示意说她们家就住在这里,这里是单位的家属房。言外之意是,单职工和全家不吃供应粮的都住不上。
第二天,方萍和同学们说:她家住窑洞,是老临(临时户)。”就是这句话,让她觉得格外刺耳,一下子比所有的同学都矮了一头。整整一节课,她都没有认真听讲,她一直在想她的牛岭村,想她去上学的第一天,三哥挺着胸膛站起来的样子……等所有的往事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之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从四面八方向她包抄过来。课间,她一个人蜷缩在角落,看同学们玩,看他们跑过学校对面的自由市场,买五分钱的葵花籽在那里嗑得津津有味。她就突然想起了她口袋里装着的花生米。她们老家盛产花生,花生一度是她们山里人赠送亲朋好友最拿得出手的礼物。于是,她掏出来“咯嘣咯嘣”地在嘴里嚼,咂巴出满嘴的香味儿。
“你吃的是什么?”不知什么时候,她身旁竟围了许多同学。
“花生。”她漫不经心地答道。
“花生是什么树上结的呢?”
“啊?”阿黄瞪大了双眼,惊奇地打量着身旁的同学,不过很快她就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说:花生树上结的呗。”
“那树长得高吗?你会上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