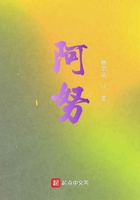一
海子自杀时,留下一句话: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人们想不通年轻的海子为什么要自杀,热爱海子的人想不通那么有才华的海子因何要卧轨自杀。
只有我能体会海子自杀的原因,只有我能理解海子生存的迷茫与漫漫度日的孤寂,只有我,我能听到海子卧轨的哭泣,只有我能体会海子生存的痛楚与无奈的自尊。
海子死时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康拉德小说选》、《孤筏重洋》。这是海子唯一的随葬品,比他来到人世时多了两样东西,那就是文学与孤独。
上帝一定是一位残忍的君主,因为他把一种纯粹的艺术赐给一个人的灵魂,却不给他生存的双翼,这样的糟践一个人的命运,让生命与艺术经历尴尬与血淋淋的撕碎,上帝是有罪的。
海子死时只有25岁,25岁的海子眼里只有诗歌,单纯深沉得就像大海一样: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蔬菜和粮食。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如果我与海子是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两个人,面对前面的艺术殿堂,海子是穿越赤道最直接的路径去冲击(海子朋友语)。我却不能,我是绕着弯儿身带背包准备采摘鲜花却身陷生存的深渊一路向着那神圣殿堂艰难行走的人海子想喝酒,却没有钱买酒,即使那瓶酒只有几元钱,而年轻的海子却没有。海子说:我给你们朗诵诗,你给我酒喝。
酒馆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不要听你朗诵。
在海子的眼里,诗歌与感情同样是价值,海子想公平交换需求,海子不是乞食者。可海子需要酒,酒馆老板不需要诗歌。
艺术在某种程度一文不值,甚至身为艺术者的海子也为自己的交换条件而脸红。因为他站在酒店门外,声音是怯怯的。艺术有时候是无形的,拿不到手里当钱使。不是每个生命个体都需要为艺术生存,艺术只是精神贵族的通行证,正如钻石永远戴在贵夫人的手指上,而一粒钻石在鸡的眼里远远不如一粒小石子有用。诗歌对于酒馆老板来说一文不值。
海子啊,你为什么要喝酒?你是禁不得酒的诱惑吗?你觉得它比尊严重要吗?你是需要靠酒精麻醉自己的感知吗?
酒馆老板的慈悲表现在愿意给海子酒喝,但酒馆老板是一个残忍的悲悯者,因为他拒绝了诗歌,拒绝了海子的心,让海子直裸裸的成了乞食者。
我不知道那一夜海子有没有喝酒,我只能体会到诗人海子的心被切割成几段。血从海子年轻的胸腔迅速酿造成一张精神黑网,罩住海子的眼泪。海子需要喝酒。酒可以麻醉舌头,润滑喉咙,点燃胸腔,滚烫肚腹,然后迷离整个精神与灵魂。海子需要麻醉、需要燃烧、需要滚烫、需要迷离,唯独把自尊丢舍到一旁,挂在众目睽睽之下。海子一遍一遍的快速用迷离的心抚过自己的尊严,眼睛却装作看不见。血从海子的身体深处顺大腿流下,流过脚趾头,染红整个脚心。
海子想喝酒,却没有钱买,哪怕只有几块钱,而海子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于是海子哭了,用生存的所有呻吟。这眼泪谁都看不到,只有海子的灵魂扛着。故乡的黄土和大海听到的只是海子的纯洁与善良。
上帝干嘛要和人类开这么邪恶的玩笑,他让一个人的灵魂丰满到溢出才华,却给他生存的行囊上不缝制那怕很小的一个拿取硬币的口袋。于是,艺术、生存与尊严、穷困,在同一个人的肉体与精神上该如何纠缠、抵制、平衡、和谐,海子的死能见证一斑。
要么,就疯掉吧。而海子选择了结束。
难道艺术与贫穷永远是两个互不厌弃而又互相厮杀的恋人吗?
二
我认识的杨老师在小城书画界小有名气,他创作的树皮画早已经独树一帜,虽然作为装饰品不适合家居,但它是艺术。书画的艺术、树皮的艺术、手工的艺术,是一些已故的细胞重新组合成生命的艺术,它们应该被挂在艺术的殿堂,令世人瞻仰、评说与欣赏,让人感受那斑驳的粗糙穿越生命蛹道的细腻与再生。
我亲眼目睹过杨老师的成功作品一百多幅,每一幅作品都离不开胶水、清漆、刷子、硬板,最后装框,而这一切都不是杨老师能从地里可以带回家的,杨老师需要资金。除了可以自由潇洒地从田间地头独自兴高采烈的采集回一大包一大包的柿树皮外,杨老师在面对其它投资时,他的心就像他的手,就像他的柿树皮一样皱巴巴的满是沧桑。
可我亲耳闻听过杨老师爽朗的笑声与对柿树画未来的展望,那是透过心酸的一种质感的笑声,那是穷困的艺术家才惯有的一种略带自嘲的笑声。与艺术挂钩的人多半清贫,清贫到只有一门心思钻研自己的成果。在杨老师的眼里,那些斑驳的柿树皮就是他的孩子,一个孩子的诞生是需要爱心从头至尾孕育与呵护的,要不就是流产,或者畸形。杨老师无暇顾及来自家人的不解甚至咒骂,他把所有的冷落与嘲笑都从头发稍上抖落出去,每天都穿着永远大他一号的衣服在创造与爱护着自己的孩子。
破落的艺术家这个词安装在杨老师的外形上,是那样的贴切与吻合,可他的眼睛在面对能听懂他语言的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时,光芒,是从他的眼睛里长出来的可以感染与激活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灵魂的。
想知道杨老师的形象很简单,先去看看田里的柿树,老柿树,这样见到杨老师时便不会惊讶。可他的画却充满灵性与厚重。也许他的眼里手里心里都是柿树,所以渐渐地把自己的外形也感染成了柿树皮。他没有钱,工资够不够生活,我看多半都用在创作上,他对艺术的执着就靠一个要好的兄弟在接济,而不是赞助,他的兄弟是个做生意的款哥,经常接济杨老师的创作。
我曾经在一次杨老师侃侃而谈他的柿树画到眉飞色舞时,正好与他兄弟的不屑调侃打个正面:“穷的只剩下树皮了,还吹!”而杨老师没有听见,继续着他的高谈阔论,我眼瞅着老师兴高采烈的手舞足蹈,深深的为一位艺术工作者的痴情梦话而心酸。杨老师谈到兴致处转过身认认真真的对他的兄弟说:兄弟,我把我珍藏的一幅“龙门”送给你,你给我的画出资装框。兄弟说:我可以给你钱装框,但我不要画。杨老师讪讪的笑了,说那画是抗战以前唯一保存的古老龙门,很有收藏价值的。
我把头扭到一边,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我看见海子站在酒馆门口说:我给你们朗诵诗,你给我酒喝……
杨老师每笑一下,都要看他的兄弟一眼,我的心就被切割成两半,一半为艺术工作者渗出心酸的泪,一半为财大气粗者生出愤怒的鄙夷。而杨老师还得感谢他,毕竟大千世界,愿意帮助他的就只有他的这个兄弟。杨老师也算幸运的了。
而海子没这么幸运,所以海子走了,海子走时只有25岁,海子是卧轨自杀的。
当火车的警鸣逐渐地撕裂人心,当火车的车头山一样地压下来,我看见海子的眼泪,滴在杨老师干枯的头发上,落在我的嘴角,辛酸而苦涩……
三
而我,我终于在某天清晨醒来后,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面对着满屋子我永远收拾不完的琐碎的东西,面对着我永远也无法打理好的生意,面对着窗外灰蒙蒙的闷热的天气,我再一次理解了自杀者的从容与义无反顾。真的,我不想活了,虽然我并不愿意死去。
活着有什么意思?睁开眼睛就开始奔波,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张一张的钞票努力地从别人的口袋里挣过来,然后又轻而易举的送给另外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学会计算成本,像一个奸诈的商人一样斤斤计较。我要学着说热情的话,让别人感到我很亲切,我人性中本来的真诚被商业歪曲成一只摇着尾巴的哈巴狗。我厌倦自己。
我厌倦自己日复一日的奔波。我厌倦自己像个头顶稻草的女人,我厌倦自己在田间地头无休无止的劳作,我厌倦看见自己整天忙忙碌碌的样子,却从来没看见过我收获的稻谷,却是把庄稼地里屋内院落到处都落满稻草渣子,我厌倦自己不厌其烦的负债播种,日日年年头顶稻草,奔波在稻草与野草的纠缠中,劳作着无谓的孤独的劳作。于是我终于在这个特定的灰色的日子里,羞于自己酿造的苦果而痛哭流涕。
有人说生存本来就是男人的事,你不用那么辛苦。然而我能“不用”吗?当我依赖的肩膀承载不了我追求的生存,我必须靠自己去打拼,不然我会被那个男人的啰嗦、埋怨逼成疯子,这样一想,我又觉得自己面对的工作压力比面对他时就显得轻松多了,我总之不能让自己沦为怨妇吧,我宁愿埋怨自己的工作能力。
我突然发现自己俗不可耐。
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也应该算是他了。我不得不感谢他,就像杨老师必须感谢他的兄弟,而海子就没有我们这般幸运。毕竟只有他能体谅我的痛苦与悲伤,也只有他能怜悯我的辛苦和我的思想,也只有他是我唯一能靠近的彼岸。但他也是造成我此生走向痛苦深渊的唯一缘由,他像一颗恶果,这世界只有一颗,不幸被我吞噬。而我现在唯一的救世主也只有他,只有他的包容能让我受伤的心得到心安理得的救治。虽然他每天都会给我念紧箍咒,虽然我的眼泪不会感动他,但他会给我伸过来他的竹竿,让我行走在钢丝上的人体,能找到平衡的支点。
我下意识的从六楼朝楼下吐了一口唾沫,看着它摇摇摆摆飘洒而下,我有一种结束的快感,如果我能像我的唾沫一样毫不顾身飞溅而下,我会不会感到更快乐?我非常渴望轻松与结束。
我该不该把我爱过的亲人和朋友都集中在我的死亡档案里?我还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就决定放弃。
一个人面对死亡,孤独其实是一种清高的美。就像海子,生为孤者又何必苛求有谁来送行。当我身披鲜花时,我的身边站着许多关心我的人,当我在荆棘路上艰难劈径时,我常常体验到孤独是一种怎样无望的凄美。
但我最终没有海子的勇气与纯粹,我只能仰慕他的义无反顾,一如我仰慕他的才华。对于艺术,海子是穿越赤道最直接的路径去冲击,包括死亡。而我不能。而我不能是因为我以为驾着爱情的船可以划向理想的彼岸,我以为婚姻可能是飞船。不幸的是我的爱情是一颗带毒的苦果,婚姻更是一副无形的枷锁紧紧地缚住我的喉咙,在挣扎与喘息中我不得不靠自己开辟事业来拯救我的灵魂与自由,却不料又一头陷进生存的夹缝里苦捱岁月。
于是,生存与尊严,艺术与穷困,对于我来说,让我又一次陷入一片混沌之中,我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走出这片泥泞,我没有任何办法。生存对于我的压力就像山一样深重。当我身无分文站在街头,我一次次看见海子的眼泪流在我的心里,翻滚,纠缠,就像我身处生活炼狱里的挣扎。我显得很疲惫,是疲惫不堪。而我能放弃吗?痛定思痛,如果坚持我那不断更换内容的“俱乐部”,意味着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投资。而放弃就等于从身上剁下一块肉来然后扔掉。而继续坚持就等于它将成为我身体某个部位的癌症,不断地要拿钱来填补这块永远也合不拢的伤口,这伤口分明是一张魔鬼的嘴巴,吞噬着我的金钱与精力,然后把负债、把苦涩、把郁闷、把狂躁、甚至把仇恨留给我。
我的生命还有多少耐力去经受?
也许我真的没认清自己,就像一件物品放错了位置,这样的错误既是对其位置的不恭,也是对其物品品质的伤害与价值的亵渎。我一时混沌,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我与我现在的生活关系。
于是,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在艺术与生存之间,我就这样生活在夹缝里,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里一下外一下,像一个乒乓球一样被这两个终极颠来打去,颠来打去。于是我在乖戾与叛逆之间极端行走,在懒惰与激情之间来回丈量,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自己的头破血流,我再一次渴望从高空坠落的快感。
可是。可是我一定要阻止自己向海子那样去自杀,因为我非常想要: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