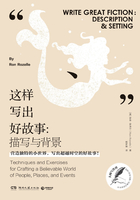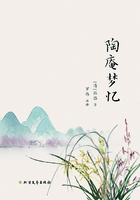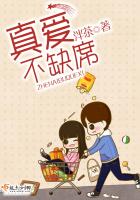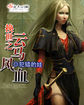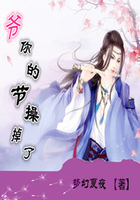今天是大年十五,元宵节。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多的辛酸,为什么提起元宵节,也是有想流泪的感觉,许是因了在别处受的委屈,还是因了岁月的流失,总之我是处在这样的亦悲亦戚的情绪中。难道是我的年龄正是这样的阶段?要不然本来喜庆异常的节日,我怎会有风华已逝的酸楚,难道这样的节日和节日的快乐就只能属于我们的孩子们了?
这样的想法突然让我很生自己的气,哽在心头的悲戚已荡然无存,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衰败的女人,即使风霜曾经相逼,我也是以傲然挺立的姿态面对,我悲戚的只是过往不再的岁月,那是压在心底的悠然幸福的金色童年,还有我纯真青涩善良含羞的少女时代啊。
两汪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流下来,就像那一江春水东流不再归,笔记本上滚落的泪珠瞬间鼓起纸的皱纹,一屡一屡的像我饱满的不平衡的心事,我再也无法把这些热泪收回到我的眼睛、我的身体,它只能像我身后的岁月,会风干一部分记忆,会留下一些痕迹,镌刻在心灵深处,一如笔记本上的泪珠,风只能干了它的湿度,而曾经皱起的波纹,永远的也无法从那洁白的纸上抚平消失,即使经历太多的岁月也不可能。
“巧姑姑”是母亲蒸给女儿的元宵之馍,是父母对女儿一生幸福的期盼,女儿吃了“巧姑姑”,人便会变得心灵手巧,女儿家若能巧手灵心,一生便不会受苦,便会受人尊敬。丰衣足食,是和心灵手巧联系在一起的,每当元宵月上之夜,母亲总会把“巧姑姑”放在一个茶盘中间,“巧姑姑”背上插着三柱香,放在窗台上,对着清冷喜庆的月光,我跪在炕上,母亲站在炕边,一句一句的教我念:巧姑姑,巧姑姑,正月十五拜姑姑,姑姑,姑姑你听着,从此以后你蹩着,我巧着,我捏花馍你看着……
接下来便是父亲呵呵的憨笑声,是我扑到母亲怀里的撒娇声,是我爬上父亲肩头边给他挠头皮痒痒边听他调侃我又苯又蹩的笑声。
父亲和哥哥的馍都是“布袋”,家里的男人都是布袋,意思是男人是粮,是一年的收成,吃多了布袋,挣回来的粮食自然就多了。
我唯一记不清母亲是什么馍,好像我们家什么好事都没母亲的份,母亲就是个围着灶锅吃苦耐劳的角色,最后终于想起母亲的馍是银子罐,银子罐是所有家庭主妇的专利吧,常言说外面有个好耙耙,屋里有个好盒盒。好盒盒说的就是母亲,就是家里能聚住钱财的人,要不然,男人纵能挣上万两黄金,家里若没有一个勤俭聚财的女人,恐怕那万两黄金,也不会落下一个,所以银子罐自然是母亲的专利,因为是专利,所以我就没注意,也是小孩子对那些银子之类的不关乎切身利益的不感兴趣,也因为银子罐上只是盖子上有一颗枣,自然对它不甚感冒。
麦子堆与浑身眼是全家人吃的,我因为麦子堆能马上钩起我对麦场的欣然向往而对那个浑身是刺的、上面只有一个枣的馍也感兴趣,那是个大大圆圆的馍,全身有剪刀自下而上剪的刺,从馍的顶部开始转圈一直剪到馍底的花纹,外形就是麦场上堆的大麦堆。而我对浑身眼的兴趣不只是它全身的枣,还有托着枣儿的花瓣,那是母亲的手逐个地先在大馍馍身上竖着压一条纹,再用大拇子与食子分别在竖纹两侧压下去然后拇指与食指会合,再轻轻用力往外一拉,于是一个漂亮的半圆的瓣就形成了,再把剪成条的枣往瓣后一塞,就成了一只美丽的眼睛,紧接着一个个的眼睛紧挨着布满大馍馍的大肚皮,从四面八方看都是眼睛,所以叫“浑身眼”,意思是谁吃了“浑身眼”谁就能多长个心眼。心眼多的人聪明,伶俐,所以我们家的浑身眼理所当然的留给我,都说我太笨了,心眼太少了,每年都应该多吃浑身眼,以便长大后能变得乖巧伶俐。每每这时,我都会幸福的望着浑身眼笑,我除了想让自己变得聪明乖巧外,我更眼谗那满身的眼睛,抠一个“眼睛”送到嘴里,那可是一份甜甜、粘粘、绵绵的幸福啊。
而我们小时候的馍馍都是外面包着一层雪白的白面,里面裹着的可全是红面,所谓红面就是麦子的糟糠部分,除了颜色是褐色的外,吃到嘴里也是粗糟的难以下咽,而外面那层雪白而细腻的馍馍皮,是麦子的精华部分,每次磨完面妈妈都要特意把白面留在过节、走亲戚或是家里来了客人时才能吃到。那层白面馍馍吃起来香甜可口,想要在嘴里多嚼上一会儿,可那喉咙就像长了只手,硬拽着口水与甜香滑到肚子里去,咂巴咂巴嘴,唇齿之间香味依然,再看看那红褐色的馍,然后极不情愿地送到嘴里,赶紧嚼上两下,喉咙却像有道拒绝的阀门,非得用力强行下咽。我们那时候吃元宵馍有好多种吃法,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吃法,也就从不同的吃法看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
有的人一下子就把白馍皮剥下来吃完,享受完后,望着里面黑黑的馍发愁,为了填饱肚皮,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吃黑面馍馍,回头再看别人在细细咀嚼白面皮,就像咀嚼一份幸福,只能羡慕懊悔地直抠自己的头皮,这种人属于无头脑的享受型,只管前半截不管后半截。有的人先把黑面馍馍先吃完,再一点一点吃白面馍馍,好幸福的滋味呀,好吃,这种人属于先苦后甜者,是能吃苦耐劳的实干家。有的人先吃一点白面馍馍,再吃黑面馍馍,最后再吃白面馍馍,这样开始是好吃的,中间是难吃的,最后又是好吃的,这种人属于懂得生活的人,他会安排好自己的一生,属于有理想与奋斗目标的人。有的人吃一口白的再吃一口黑的,这样交叉着吃,甜一点苦一点甜一点苦一点,这种人属于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大的起落,一生会平平安安,幸福苦难参半。有的人白的黑的不分,一口咬下去,黑白相参,苦甜同嚼,这种人不拘小节敢作敢为,不言苦甜,大大咧咧,一生见福则福见贫则贫,与世无争。
而我们今天的元宵节,好多家庭早就不蒸元宵馍馍了,也就是在农村,只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做了母亲的还记的蒸馍馍,所有家庭的馍馍里再也看不见那红褐色的面了,再也听不到“白面馍馍真好吃”的欢声笑语了,再也没有聚在一起讨论谁谁谁先吃白面谁谁谁又先吃黑面的调侃说笑声了。
而元宵馍馍在我们的口腔里,再也吃不出当年的甜香味了。而那香甜味道的失去,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嘴吃腻了白面?还是我们的味蕾麻木了?而当年元宵节的繁荣与欢喜与多彩与街头巷尾的人情味仅仅是因为当时家家没有电视机吗?
我有好多年没有闻到过“滴滴晶”的味道了,尽管我家里也有个十二岁的少年,他正是应该抓着一把五颜六色的滴滴晶去找小伙伴,嚷着自己的又多又好看的年龄,也正是搭帮结伙东家进西家出串街走巷看花灯猜谜语的年龄,我们不奢求他们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在潮湿的墙面上刮销自制滴滴晶,但我希望我能看到我的孩子知道元宵节的来历,知道在这个节日里呼朋唤友去玩、去看灯盏,去到处走走、看看、闻闻飘荡在夜空中的美丽香甜的花炮味与浓浓的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