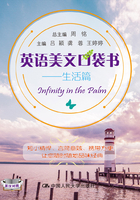“您不是很爱她吗,”内莉答道,没有向我抬起眼睛,“既然您爱她,那人一走,您就娶她。”
“不,内莉,她爱我并不像我爱她那样,再说我……不,这是不可能的,内莉。”
“这样我就可以做你俩的佣人,伺候你俩了,你们就可以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了。”内莉不看着我,几乎用很低的声音说道。
“她是怎么啦,她倒是怎么啦!”我想,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内莉闭上了嘴,从此整个晚上没说过一句话。后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她就哭了,哭了整整一晚上,后来就眼泪汪汪地睡着了。甚至半夜,在睡梦中,她还哭,夜里还说胡话。
但是从这天起,她变得更忧郁,更沉默寡言了,而且变得根本不同我说话了。诚然,我也注意到她曾偷偷地瞥了我两三眼,而且在这目光中包含有多少温柔啊!但是这很快就与唤起这种突然的柔情的那一瞬间一并逝去,而且仿佛要反戈一击这一突然的冲动似的,内莉几乎随着每一小时变得更忧郁了,甚至跟大夫也这样,大夫对她性格的这一变化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她却已经几乎完全康复了,于是大夫允许她可以到户外去散散步,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当时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正当基督受难周,这一年它来得特别晚[2];我一早就出去了;我一定要到娜塔莎那里去一趟,但是我决定早点回来,好带内莉出去,跟她一起散散步;因此把她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家里。
但是我简直无法表达在家等着我的竟是怎样的打击。我急忙赶回家。回来后一看,房门外插着一把钥匙。进门一看:没有一个人。我傻了。再一看: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粗大的、歪歪扭扭的字:
我走了,离开您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到您身边来了。但是我很爱您。
您的忠实的内莉
我吓得一声惊呼,拔脚跑出了屋子。
第四节
我还没来得及跑上大街,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现在怎么办,蓦地看见在我们那座公寓的大门旁停下来一辆轻便马车,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拉着内莉的手正从车上下来。她把她抓得紧紧的,好像生怕她再次逃跑似的。我急忙向她们奔去。
“内莉,你怎么啦!”我叫道,“你上哪啦,干吗呀?”
“等等,您别急嘛;快到您屋里去,到那里以后就全知道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叽叽喳喳地说道,“我要告诉您的事可悬乎啦,伊万·彼得罗维奇,”她在半道上匆匆说道,“非让您大吃一惊不可……快走,您马上就知道了。”
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她有非常重要的新闻相告。
“快点,内莉,快去躺一会儿,”我们进屋后,她说道,“你不是累了吗;跑了这么多路,可不是闹着玩的;病刚好,看把你累的;快躺下,宝贝儿,快躺下。咱俩先离开这里一会儿,别打搅她,让她先睡一觉。”她说罢向我挤了挤眼,让我跟她一起到厨房去。
但是内莉并没有躺下,她坐到沙发上,伸出两手捂住了脸。
我们出去了,于是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便急匆匆地告诉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又打听到了更多的细节。这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内莉在我回家前约莫两小时给我留了张条子,离开了我,她先跑去找老大夫。他的住址她早打听到了。大夫告诉我,他一见到内莉上他家去,简直吓呆了,当她待在他家的时候,他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完后又加了一句,“而且永远也不会相信竟会有这种事。”然而,内莉的确上他家去过。他当时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坐在圈身椅上,穿着睡衣,在喝咖啡,这时她跑了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就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她哭着,拥抱他,吻他,吻他的两只手,并且恳切地,虽然是前言不对后语地,请他收留她,让她跟他住在一起;她说,她不愿意,也不能够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因此才离开了我;她说她受不了;又说她以后再也不取笑他了,再也不提新衣服的事了,她以后一定规规矩矩,好好学习,一定要学会“给他洗烫胸衣”(她可能路上就想好了她要说的所有的话,也许更早就想好了也说不定),最后,她又说她以后一定听话,哪怕每天吃药都成,随便吃什么药。至于她过去说她要嫁给他,那是说着玩的,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事。这德国老人惊愕得一直张着嘴坐在那儿,举起了手,手里拿着雪茄,把雪茄都忘了,雪茄灭了,他也不知道。
“小姐[3],”他好歹恢复了说话能力,终于说道,“小姐,据我了解,您的意思是想请我让您在我家找点事做。但这是不可能的!您瞧,我的日子过得很紧,收入也不多……再说,连想都不想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这太可怕了!最后,依我看,您是从自己家里逃出来的。这不足称道,也是办不到的……再就是,我只允许您出来稍微散散步,在大晴天,但必须在您的恩人的监护下,可是您却撇下自己的恩人,跑来找我,而这时候,您本来应当保重自己的身体……而且……而且……要吃药。而且,最后……最后,我什么也不明白……”
内莉没让他把话说完。她又开始哭,又开始求他,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越来越感到惊讶,越来越什么也弄不明白。最后内莉只好撇下他,叫道:“啊呀,我的上帝!”——边说边跑出了房间。“那天我病了一整天,”大夫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又加了一句,“临睡前还服了一剂汤药。”
而内莉直奔马斯洛博耶夫家。她身边留下了他们的住址,终于找到了他们,虽然也没少费劲。马斯洛博耶夫正好在家,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一听到内莉请求他们收留她,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惊讶得举起两手一拍。她问内莉:为什么她要这样,住在我那里,她是不是觉得难受?——内莉什么也没回答。而是扑到椅子上嚎啕大哭。“她哭得死去活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告诉我说,“我想,这样哭下去,她会哭死的。”内莉苦苦哀求,哪怕让她当女佣人,哪怕让她做厨娘都成,她说她会扫地,而且一定会学会洗衣服(她把自己的希望特别寄托在这个洗衣服上,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这是让人家收留她的一个最富吸引力的理由)。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的意见是先把她留在他们家,等事情搞清楚后再说,同时通知我内莉在他们家。但是菲利普·菲利佩奇坚决反对这样做,并且命令把这个逃兵立刻送回去,交给我。半道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又是拥抱她,又是吻她,这倒使内莉哭得更厉害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看着她也哭开了。就这样,两人哭哭啼啼的哭了一路。
“内莉,你为什么不愿意住在他那里,为什么呢;难道他欺负你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眼泪汪汪地问。
“没有,没有欺负我。”
“嗯,那么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反正我不愿意住在他那里……我不能……我对他总是那么凶……可他却那么好……可是在你们家,我一定不凶了,我要干活。”她说,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凶呢,内莉?”
“不为什么……”
“我问了她半天就问出了这个‘不为什么’,”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擦着眼泪结束道,“这孩子多苦命呀?该不是得了急惊风吧?伊万·彼得罗维奇,您看呢?”
我们走进屋去看内莉;她躺着,把头埋在枕头里,在哭。我跪在她床前,拿起她的两只手开始亲吻。她把她的手使劲抽了回去,又嚎啕大哭,而且哭得更厉害了。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才好。就在这当口,伊赫梅涅夫老人走了进来。
“伊万,我找你有事,你好!”他说,他打量了一下我们大家,惊奇地看到我跪在地上。最近以来,他老人家一直在生病。他瘦了,而且脸色煞白,但是他好像对什么人不服输似的,不顾自己疾病缠身,也不听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一再规劝,硬是不肯躺下,而是继续为自己的事四处奔走。
“我先告辞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定睛看了看老人后说道,“菲利普·菲利佩奇让我尽可能早点回去。我们还有事。到晚上,天快擦黑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们,坐一两个小时。”
“她是什么人?”老人悄声问我,他分明想到别处去了。我作了解释。
“哦,伊万,我找你有事。……”
我知道他此来所为何事,而且一直在等他来访。他是来找我和内莉商量,想把她从我这里要过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好说歹说终于同意了收养这孤女。这是因为我跟她进行了几次秘密的谈话,她才同意的:我说服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告诉她,这孤儿的母亲也受到她父亲的诅咒,看到这孤儿,也许会使他老人家改弦易辙,回心转意的。我十分生动地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计划,现在反过来是她自己缠着丈夫要收养这孤女了。老头非常乐意地开始操办这事:他想,第一,借此可以讨好一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第二,他另有打算……但是这一切我以后会详细讲的……
我已经说过,从老人第一次来访时起,内莉就不喜欢他。后来我又发现,每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伊赫梅涅夫的名字的时候,她脸上就流露出憎恨。老人立刻开始谈正事,并不转弯抹角。他一直走到内莉身边(内莉仍旧把脸埋在枕头里躺着),拿起她的一只手,问道:她肯不肯搬到他家去住,做他的女儿?
“我有过一个女儿,我曾经爱她胜过爱我自己,”老人最后道,“但是现在她不跟我在一起了。她死了。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家……而且在我心里取代她的位置呢?”
他那双漠然以及因发高烧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噙满了眼泪。
“不,我不愿意。”内莉回答,没有抬起头。
“为什么呢,我的孩子?你没一个亲人。伊万总不能永远让你待在他身边吧,而你到我家去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不愿意,因为您坏。对,您坏您坏。”她抬起头来又加了一句,面对他老人家,坐到床上。“我也很坏,比谁都坏,但是您比我还坏!……”内莉说这话时脸色发白,两眼闪出了光;甚至她那发抖的嘴唇也变得煞白,而且由于某个强烈的感觉猛地袭来而变得口角歪斜。老人惶惑地看着她。
“对,比我还坏,因为您不肯宽恕您的女儿;您想把她完全忘了,因此您才想收养另一个孩子,难道自己的亲生孩子能忘掉吗?难道您会爱我吗?您一看到我就会想到我不是您的亲生孩子,您有自己的女儿,可是您自己把她忘了,因为您这人心狠。我不愿意住在狠心的人家,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内莉呜咽起来,匆匆瞥了我一眼。
“后天基督就复活了[4],大家都会互相亲吻,互相拥抱,大家都会言归于好,所有的过错都会得到原谅……我早知道了……就您一个人,就您……哼!狠心的人!给我走开!”
她说罢泪流满面。这一段话她好像早想好了,而且早背熟了,就准备老人再一次请她住到他家去的时候说出来。老人闻言吃了一惊,脸色变得煞白。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痛定思痛的表情。
“干吗大家都这么替我担心?何苦呢?干吗呢?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内莉蓦地在一片迷狂状态中叫道,“我要去讨饭!”
“内莉,你怎么啦?内莉,我的朋友!”我不由得叫道,但是我的喊叫只是火上加油。
“是啊,我还不如去沿街乞讨好,我决不留这儿。”她一面痛哭,一面叫道。“我母亲也乞讨过,她临死的时候亲口对我说过:宁可穷,宁可乞讨,也不要……向人乞讨并不可耻:我不是向一个人乞讨,而大家并不是一个人:向一个人乞讨——可耻,可是向大家乞讨,并不可耻;一个女乞丐这么跟我说过;因为我小,我没地方挣钱。因此我要去向大家乞讨。可待在这儿,我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我就是坏;我比所有的人都坏;瞧,我多坏!”
说罢,内莉蓦地、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从小桌上抄起一只茶杯,猛一下摔到地上。
“瞧,现在摔破了。”她以一种挑衅般的洋洋得意的神情看着我,加了一句。“一共有两只茶杯,”她又加了一句,“我要把另一只也摔碎……看您用什么喝茶?”
她像发狂一般,仿佛在这疯狂中感到一种快感,她自己也好像意识到这样做是可耻的,这样做不好,与此同时,又仿佛在给自己火上加油,继续胡闹。
“这孩子有病,万尼亚,我看这样吧,”老人说,“要不就……我真弄不懂这孩子到底怎么啦,再见!”
他拿起帽子,跟我握了握手。他似乎非常伤心;内莉可怕地侮辱了他;我心里乱糟糟的,不知是什么滋味:
“你也不可怜可怜他,内莉!”就留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叫道,“你也不觉得,不觉得害臊!不,你不是个好人,你的心的确很坏!”我没戴帽子就跑出去追老人。我想把他送到大门口,哪怕说两句话安慰安慰他也好。我跑下楼梯时,眼前好像还看见内莉那张由于我的责备而变得煞白的脸。
我很快就追上了我的那位老人家。
“这可怜的孩子受了很大委屈,她也有自己的伤心事,请相信我,伊万;是我大吹大擂地向她说起我的痛苦,”他苦笑着说道,“是我刺痛了她的伤口。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我看呀,万尼亚,还得加上一句:饿汉也不总了解饿汉,好了,再见!”
我本来想顾左右而言他,对他说件不相干的事,可是老人只是挥了挥手。
“别安慰我啦;你还是留神,别让你那小姑娘又跑了;她那模样好像有这意思。”他愤愤然加了一句,说罢便迈开大步,匆匆离去,一路上挥着手杖,敲击着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