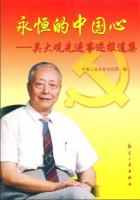古人煮酒论英雄,而今日英雄之论早已沉沦为世俗之物。论者过多,则未免乏味无趣。酒陪了英雄数千年,今日我打算让它当一回主角。
在今日来看,饮酒不过是应酬时自找麻烦,孤独时借以消愁之物,未免少了几分雅兴。古人则不然,若不是“三元”之中已被“天、地、水”占满,酒定会被道家列为“三元之一”以尊天地。
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唬拍光”,可见古人对酒器之重不亚于酒本身。汾酒清如水薄如雪冰如玉,自是要在玉杯之中饮之方见其润泽凝练的一面。若哪日有了闲情,掬一瓢汾水所造之酒,人羊脂白玉杯里品其味观其色再听其与玉杯交流的绢绢丝雨,不更会有几分惬意。
中原酒色以清为上品,关外白酒以烈为最佳。酒出自粮,粮已是烈风之下的“烈士”,那酒自也不会是“懦夫”。只是品来必是少了一分芳冽之气,何不用犀角杯饮上一秋甘烈再增其一层香气?“劝君更进一杯酒,必是用了这增香的犀角杯,才不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苦闷。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美酒艳红妖冶,于须眉男子饮之必是方刚不足。于是古男子将其注人夜光杯中,其色血样无异。“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实是快哉。
上古大禹治水实是有功,可另一功绩也不可灭之,造酒便是其一。最古的高粱酒便是出自大禹之手。天下谁人不为王?而当年项王豪气干云,若饮上佳米酒自应用大斗。斗胆而饮之,自又一番气概在其中。
百果百草曾经也用于造酒,以百年古藤造杯储之方得其清芬之气;绍兴状元红则必用古瓷杯。南宋瓷破败,元瓷鄙俗,只有北宋瓷方可用之。白乐天诗云:“红袖织续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梨花酒月翡翠杯,则梨花如有绿叶相衬分外精神。再者玉露如有珠泡在其中,只有琉璃杯透明不失华丽,才可看其佳处。
金搏银盏是帝王家之做派,又何尝不是故作姿态?只不过帝王自有帝王之美酒可饮,宫廷女儿红即是其中之一。想来宫中的女儿最苦倦,则女儿红也必是酿得最为久长,银盏品之方有思苦的心怀,金尊饮之则又有除望的梦幻。
酒,是一种文化的陈酿。当我们将自己浸在苦涩的啤酒之中,将生命摆在陈列了轩尼诗、人头马的做作之中时,何曾想起过古朴的酒是怎样的千古绝唱?
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