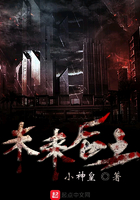在许多年之前,我无所畏惧,因为我一无所有。一切我珍爱之物都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钢铁大幕中,每一个曾经我为之而战的理由,如今都被证明是谎言与幻想,不过是那时年少之人在向苍穹与魔鬼的低声耳语。我不再感到愤怒,也不会再悲伤,位于大脑皮层的那段边缘系统里面所珍藏的,我已经决定丢弃,向命运妥协,向友人伸出刀剑,向帝国的铁血与钢铁的意志承认失败。
但是梦魇却未放过我。
当我放松下来并强迫自己入睡时便遇到它们以及他们。
——————
这是一座古老的塔。塔很高,塔也很旧。
天空是凄迷的苦雨,人类在雨中缓缓地前行,又缓缓地入睡。是的,是入睡。雨水像是无边无际,要向世间的众人展示它的震怒,展现它淹没世界的决心。而地上东倒西歪地,到处都是身体冰凉的没有一丝温度的人。
这些人的身上绝对没有一丝伤口,他们的特制的全身覆盖的板甲,采用了最严密的瓦格纳的工艺,纵使眼睛都被金属覆盖,为了这样的防护能力,它甚至牺牲了绝大多数板甲所具有的机动灵活性。
无数的神圣的烙印在这些瓦格纳的板甲之中流淌,人造的小源以太核心仍然在运转着与大源泾渭分明的力量——
他们却好像死了,不,应该说睡着了。
沉眠于一个不可见的深沉的梦境,在敌人还未临面的前一刻,他们就睡着了——
也许再也不会醒来了。
刚毅面孔的黑发男人就在这个铺满了沉睡的士兵的道路上缓缓地走着,他在祈祷,却不是向诸神或者上帝,西瓦尔的血统让他强壮,杀戮中的本能教会他不信神明,他在向一个很少有人还记得、或者说记得的人不会提及的人名祈祷。
他在缓缓地行走,行走在枯萎的大地之上,浩荡的风暴之下,通天的高塔如同传说屠龙白银龙枪一般直指天穹,似乎就要把这天也撕碎。
从远方的天际,黑潮一样的军团正在列队冲杀。
万马奔腾,大地战栗。
他的目光却似乎不在眼前任意一处,而是在更加遥远的更加遥远的地方,跨越山川大地,突破以太星空,直指不可测的平行时光线索。
“是你么?”
似有无声呢喃。
——————
突然释放的肾上腺素将章子厚从浅睡眠中惊醒,他双手由于神经刺激而颤抖,身上满是汗水。幻觉中那个男人似有似无地一抹目光依然跟随着他,似乎此时耳边还可以听见苍穹破碎、大地震怒,命运与根源发出尖锐而疯狂的嘶鸣。甚至可以感到这些声音流淌在血管与骨髓中,在他的基因链上留下痕记。
坐起身来,他等待着那些幻觉消失在耳膜隐隐回荡的噪音之间,然后才注意到一个人影已经来到他的身旁。
“小雪,你还在这里干什么,不是说好了让你好好在基因舱里面完成注射的么?怎么还在外面乱跑?”话刚刚出口,他的语气已经不觉之间就变缓和了。
尤其是想到那个久远的梦境幻觉。
他看向女儿章映雪的目光在下一秒就又柔和了三分。
少女一身居家便装,却是微微低着头,似乎有些犹犹豫豫的。她的身体肤色,无论是裸露在外的肢体还是那一张线条精致柔和的面容都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白,某种程度上与基因病状的白化病很是相似。
章子厚很疼爱这个女儿,从各种意义上,她都是他唯一的珍贵之物。她的妻子,那个漂亮而骄傲的罗那人女人,因为那些陈旧如噩梦的东西而死亡之后,这个出生便在暴露的高辐射环境中染下基因病症的女儿就是他无法放下的东西。
她安静了许久才开口问道:“父亲,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哼,”女孩翘起嘴角,又似乎有些着急,严肃认真地说道,“我知道这种基因补全的药剂,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因为一次实习中被基因感染了,几乎为了一笔手术费,耗光了家产——爸爸你是不是干了些不好的事情……”
章子厚有些好笑道:“不好的事情?”
少女一跺脚,似乎对于父亲的嬉笑的态度很不满意,“就是打黑拳,干脏活,做走私买卖之类的,那种不清不楚的快钱啊!”
“小孩子,胡思乱想些什么呢?”章子厚毫无破绽地表现出一副微笑轻松的模样。半真半假地解释道,“瑞雪祭要调整气象计划,所以最近局子里天天加班加点地赶工,身为领导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必须以身作则,这几天都没有合眼累了点。”
“那这些基因药剂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委托当年旧友带来的。”章子厚无奈地回答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实是实话,但是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猫眼公司】的完美级别高纯度基因蓝图补全注射药。
区区的账面上只是数字的钱,也能买到?
做梦吧。
“哦。”章映雪并没有生疑,只是把手中的一杯咖啡端了上来,然后扫了一眼书桌上面散落的书籍,便说道:“这些东西我来整理一下吧,应该都是很重要的吧,我都放到那边的书架,行么?累了就多休息一会儿吧。”
话音刚落,章子厚的女儿就已经像只穿花蝴蝶似的,收拾桌案,
他缓缓地依靠着天鹅绒的椅子靠背上面,阴云高悬于天,落雪纷纷坠落,他望着像是凝固的铁水浇筑的天空,心中却似乎空荡荡的。
冰凉的空气与手中的暖暖的咖啡形成鲜明的冷热对比。舌尖的味蕾似乎有些干涩,温柔的水流穿过咽喉,灌入胃袋,发出满足的生物信号流淌在大脑皮层亿万神经元之间。
他环顾四周,洁净的天花板,去年置办的新家具,白色漆面的墙壁在壁灯光量子迁跃的光束的照射下,平整而温馨。
他大口大口地呼吸,肺泡产生无规则的抽搐的感受,像是有异物阻塞在那里,他缓缓的闭合双目,像是明悟了什么似的,不再做什么多余的动作。
走马观花一般地,一生的经历就那么平平淡淡地在他的面前展开:
那年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就像是这个国家无数的无名小卒一般无二,通货膨胀影响到了【玄昊公国】,民间动荡,帝国铁血镇压,一场民变之中,家破人亡,他为了生存投身了革命军。然后革命军败亡,他又机缘巧合成了一个帝国开拓军的成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养马人。
那是最好的日子。
那里是【帝国军部】认可的开拓军团【阿瓦隆】。
他忽然间地战栗起来,迅速起身,几乎是一步就从座椅上跨出了七八丈之远,衣袂翻飞之间,身形已经化为一道黑影激射到整理书籍、杂物的少女的身后。
面无表情,神色肃穆。
——真是精湛的技艺啊。该说是长久的安逸让我最基本的东西都忘记了么?
首先,确认第一件事情,这是“梦境”,对么?一个梦中之梦的思维“陷阱”——他从第一个战场的噩梦里醒来,却还是受困在第二个梦境,而潜意识里面的却在这个家里的书房中放松了警惕么。
在这个国度里面无处不在的大小天网固然恐怖莫测,但是更加令人恐惧的是那些悖逆人类常识向着极限与边境行走的人,比如说思维大师,基因掌控者,前者颠倒现实与梦幻,后者篡改身体与灵魂,几乎把人类认知一切砸碎。
他右手三指曲起,食指与中指并拢,抬手虚空之处遥遥地一压,一束烈焰从以太虚无之间升腾,呼啸而出,卷起扭曲的空气与炽烈的热风,而后传出血肉绽裂的声音。
章映雪,他的珍爱之女,像是一张纸,瞬间洞穿,绽放出殷红。
他落入了一个思维大师的“陷阱”之中。
然后是,确认第二件事,寻找“情境”——更加专业的解释是思维自发式诱因组合记忆的思维构建基础。
他刚刚在干什么?
出门前往百眼之城,为女儿购买基因补全药剂,以求抑制那近乎是诅咒一般纠缠在章映雪身上的基因病症。
所以,是那个年轻的司机做的手脚么?
下一刻,章子厚的身上丝丝缕缕的锋锐的气机爆发牵引,剧烈的以太震荡便直接被激发,身体皮肤之下,无数的鲜血瞬间逆流迸发,体表开裂、血管破碎,剧烈的痛苦与瞬间的失血令他的手脚发凉,面色苍白。
【逆血冲击术式】。
然后,一切表象散落、剥离。
他又重新回到了那一辆梭车之上。
他从思维世界挣脱开来——
思维与现实,巨大的时间差在这仓促的惊醒过程中带来的首先便是如针刺一般的剧痛,从天灵盖一直传到脚底,伴随着一时间混沌的思维。
他睁开眼睛,便发觉到了自己手臂上面缠绕的皮管,那是一根抽血的发条机械泵,半个巴掌大小的微型机械发出工作的发条运转的蜂鸣之声。
白色的皮管将血液通过六支细针从心肺、脊柱以及四肢经脉以一种稳定的速率抽离着血液,失血的眩晕在头颅里面盘旋,伴随而来的还有源源不断的神经里面的麻痹感。
“审判庭的【离心抽血锁脉法】,还有【青花神经麻痹药剂】,”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得意,反而是声音里面充满了大限将至的悲凉与无奈。
“没想到你还是醒了。”作为梭车司机的黑发黑瞳的少年平静的声音里面似乎充斥着一种冰冷的嘲讽,“章子厚先生,很不幸的是,你醒过来的时间有点迟了,该拿到手的东西,我已经从你的头脑里面拿到手了。”
“你是谁?”
章子厚本能地感到一阵刺痛从透露里面炸开。他明明不可能认识这个年轻的大男孩,但是不知为何从他的身上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熟悉与印象。
少年想了想,然后很简洁地回答道:“十五年前的【阿瓦隆】。我亲爱的阿瓦隆幸存者与背叛者先生。”
章子厚瞳孔紧缩,一瞬间的恐惧甚至超过了肉体之上濒死的极限所带来的恐惧。
“哈、哈、哈……”
他张大嘴,向着空气使劲地把肺泡里面的空气挤出,又充满,眼睛里面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解脱了的笑容。
——原来是你的儿子么?
他终于认出了那面孔上面熟悉的棱角与轮廓,心脏却更加冰冷而痛苦。
西瓦尔之血。
银之血。
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