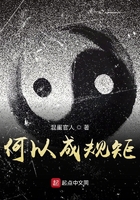去年初秋,接来新夏先生电话,说三晋出版社有意刊印一套读书随笔集。
稿约规定,不收已入集的篇什,这自然是应该的。但因为自己本来写得不多,前些时候又编了两本集子,所剩也就无几了,正像孔乙己小碟里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明知不多,还是翻箱倒柜,找出八篇来,远不够字数,另外还存着一点近年写的序跋,但人家未必想读你自以为不错的“悉心文字”,只好也选出八篇,仍不够字数,那就只好赶写了。自元旦开笔,历时四个月,断断续续写得十二篇,总算将字数凑足。我就照此分成三辑,因为本来就是小书,不必再拟辑名,也省了书中的隔页,在目录上间空一行,以示分别。
读书随笔大概没有规定的写法,也不必向“正宗”书话看齐,我在《看书琐记》的后记里说了一点想法,这或许会让看惯“正宗”书话的读者失望。其实,我的不再“正宗”,正是由曾经“正宗”而来的。许多年前,我也写过“正宗”书话,数量还不算少,大都一书一议,不痛不痒说几句,甚至起承转合也都规矩绳墨,“厌气”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回过头来,对自己过去的写,真有点像看一张光腚赤脚的孩儿照,虽然幼稚,却还有一点童趣的可爱,但如果再像老莱子那样,穿了斑斓衣裳,扮婴儿啼戏于父母之前,其他人是不会喜欢的。我心里清楚,有的事情不到这个年岁,大概也明白不了。
承来新夏先生的厚爱,屡屡敦促,心中实在感激得很,还有张继红先生的宽容,让我能在最后的时间交稿,这都是隆情高谊,应该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