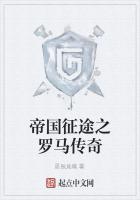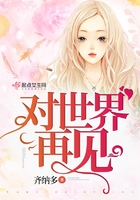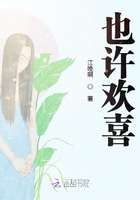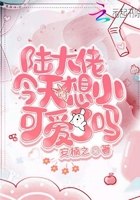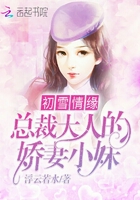曹搡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杰出的诗人。他开创了建安诗风,是建安诗坛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现存二十余首,《蓠里》是其有名的篇章。
《蓠里》也叫“蒿里行”,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原是齐国东部的民谣。古人说,人死后灵魂归于蓠里,所以“蓠里行”是送葬时唱的挽歌。作者借此乐府古題抒写时亊。内容与题目无关。
钟惺{古诗归》称蒈搡的诗为“汉末实录”和“诗史”。(蓠里》正是这样一首诗作。它以简短篇帳,凝炼地概括了公元190—198年之间的史实,反映了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推写了战乱中人民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抒发了诗人悯时伤世的情感,是当时历史的艺术再现。
其思想意义主要在于:
对军阀混战的强烈憎恶。全诗分两大层次。第一层为前十句,即从关东有义士”到“刻玺于北方”。作者严肃冷竣而又饱含情感的笔墨,如实地记录了汉末各地豪强起兵讨伐董卓及他们各怀野心互相争夺的史实。一至四句,概括了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的事件。称聚集诸侯为“义士”,称董卓之类为“群凶”,说明在作者心目中,讨伐烧杀掳掠、挟持献帝、野心勃勃、祸国殃民的董卓的军事行动是正义行动。作品以武王伐纣会师孟津和刘邦项羽攻秦咸阳两个典故表明,起初各方将士都是一心一意除奸诛恶、忠于国是、匡扶汉室的,表现出作者的兴奋赞美之情。五至八句,有力地批判了袁绍之流野心家各怀鬼胎,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图谋私利互相残杀的罪恶。用“踌躇”的“雁行”作比,形象地说明貌合神离,军心不齐的状况;又指出“使人争”的真正原因是“势力”。诸侯们各怀野心,置盟军主旨于不顾,拼命扩张自己的实力,竟至“自相戕”,使军队四分五裂,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九至十句,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军阀们分裂军力、自相残杀的实质是想当皇帝。袁术在“淮南”称帝、袁绍在“北方”“刻玺”,铁的事实面前,军阀们的野心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些揭露和批判,表现了作者对军阀混战的深恶痛绝。
最后六句为第二层。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以悲切沉痛的心情,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连年军阀混战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战争接连不断,战士们衣甲不解,虮虱遍生,老百姓深受其害,大量死亡。富饶的山河,变得满目疮痍,白骨遍野,人烟稀少,千里之内听不到鸡叫声。一幅悲惨至极的图景展现了出来,诗人不禁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这种感慨既表现了诗人对军阀混战的无比憎恶,又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心,大悲大痛之情溢于言表。
对汉王朝衰败的哀伤。作品处处流露出诗人对汉王朝衰败的哀伤悼惜之情。开头四句肯定盟军讨董义举,赞美“初期”的团结一心;中间六句揭露批判军阀分裂,自相残杀及其称帝野心;最后六句同情百姓、感慨残局。从这些内容中,读者感到了作者为使汉室重新振作而激荡跃动的脉博、听到了作者感叹汉室的衰敗而哀伤痛惜的心声。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表现,基本反映了诗人全部诗作的主要特色。
质朴简练的语言。全诗找不出一个诘屈聱牙的词句;除+“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之外,再无典故;遗词造句不讲式究辞藻的华美。作品只就事件如实道来,明白如话,读者似乎在聆听一位亲自经历或目击者的娓娓诉说。语言风格极为质朴。这种质朴并非粗糙和松散,而是高度锤炼以后的语言精华,容量很大,十分简练,显得浑厚凝重。
慷慨悲凉的情调。在曹诗中这种情调随处可见,《蒿里》更为突出。作品中的豪情壮志和强烈责任感就是其惊慨表现,如前四句的内容。如果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与此联系起来,就更能深刻体会出这种情调。
作品中对社会动荡和人民遭受苦难现状的悲愤沉痛心情就是其悲凉表现,如最后六句所展现的图景。这一点在本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动形象地高度概括了东汉末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充分表达了诗人同情人民疾苦的悲凉心情,因而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在乐府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新的创造。“蒿里”原为乐府杂言体,基本是四字一句形式,而此诗则改成了整齐的五言句式;内容上它原来是挽歌,此诗则叙写了当时的时亊,这是对这一乐府旧题的发展。作品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和质朴的民歌语言,又是对乐府精华的继承。
曹诗沉雄豪放的气势,在此诗中虽然不及《观沧海》等诗突出,但也有一定的表现。例如结构上起承转合,相当完整。段落之间环环紧扣、层层剥笋。内容上对军阀势力敢于斗争、奄不妥协。都表现了诗人的超群笔力和英雄气概,是沉雄豪放气势的表现。
附:
蓠里行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蹐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