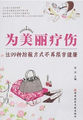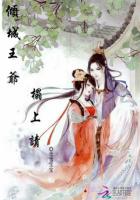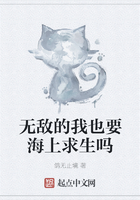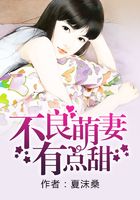我1863年生在塔甘罗格市。
大约从六岁起我开始记事。那时,我们住在修道院街和集市街拐角上一所两层楼房里,那房子是莫伊谢耶夫家的。父亲在楼下开一个不大的食品杂货商店,我们一大家人,父亲、母亲、六个孩子,大部分人住在楼上,有几个人住在楼下。
我有五个兄弟。亚历山大比我大八岁,尼古拉大六岁,安东大三岁半,伊万大一岁,弟弟米哈伊尔比我小两岁。我们的父亲做的是小买卖,养活这样一家人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些孩子得干许多活儿。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要比别人干更多的家务,帮助母亲。哥哥们一般是在铺子里帮父亲做事,安托沙也如此。
按照当时老派家庭严格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父亲对孩子们要求苛刻而严厉。哥哥们做错了事,往往难免遭到皮鞭的惩罚。有时安托沙也挨父亲打。安东·巴甫洛维奇长大成人后,虽然性格非常温柔体贴,却也批评过父亲教育孩子的方法。父亲极力要孩子们接受宗教教育,他们必须到教堂去祈祷,参加唱诗班唱诗,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练唱。此外,作为父亲的帮手,哥哥们还要看守他的店铺,那是个枯燥无味的差事,正因为这些,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曾说,“在我的童年没有童年”。当然,人们不要忘记我们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祖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是一个地主家的农奴,受过农奴生活的严酷训练,我们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年轻时也是个农奴,后来才得以赎身。因此,我们家那种严格与冷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父亲童年时经历过的那种严酷和不自由生活的反映。然而我后来却感到奇怪,父亲那种演员式的性格,他对音乐、歌唱的热爱,他那些明晰的道德原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他本人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但是他却想方设法送孩子们进中学读书。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当时商人家庭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反动观点,就能明白我们的父亲比他同阶层的人要高明多少。
所以,认为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待子女纯粹是一个“残忍的暴君”是不对的。他是一个严厉的人,然而他杰出、有才能。
那些论述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专横性格的文学研究家,通常援引我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书信和回忆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大哥虽然很有才华和能力,不过他有病,醉酒病,发病时,想入非非地编造了许多东西。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大哥,可是他看到,疾病给大哥带来严重的后果。1888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拿大哥有什么办法呢?没别的,光是叫人难受。他不饮酒的时候聪明、虚心、诚实、温和,可是一喝醉酒,就简直叫人受不了。他两三杯酒下肚,就会十分兴奋,开始胡扯。他写信就是要满足他那种要说、要写或者要编造某个无害而动人的假话的强烈愿望。他还没到产生幻觉的地步,因为他喝酒还算少。我根据他的信就能知道,他写信的时候是清醒的,还是喝醉了酒:有的信写得非常规矩、真挚,有的信却从头到尾都是胡说。他患有醉酒病,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1905至1912年间发表的回忆录的某些章节会引起读者误解了。
此外,从父亲写给儿子们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大哥亚历山大年轻时代的生活有时多么让他生气,父亲对大儿子的性格、秉性又有多么细致入微的了解,他又怎样谨慎而委婉地努力教育他。在我的珍藏室里,保存着父亲写的一些信的原件。例如,1875年4月8日父亲给亚历山大写过一封信,当时亚历山大住在男子古典中学校长家里,做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下面是这封信的摘录:
萨沙,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们,我们放纵了你,你岁数这么小,就能自己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就是说,我们的话你是不会听的。……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随你的便,你没有我们也能行,也能活。只可惜,你这么早就忘了父母,可是我们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为了把你养育成人,我们不惜花钱,不顾劳累……今后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改改自己的脾气,对我们和对你自己都要厚道些;你又漂亮又聪明,可是你有些忘乎所以,你身上有一种自高自大的派头。萨沙,你可给我们添了很大的罪孽呀……
我们的母亲叶甫盖尼雅·亚科夫列芙娜跟父亲不一样,她是一个很温柔、安静的女人。她的性格平和可爱。我记得,我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听她讲故事,那些不平常的、神话般的故事都充满诗情。与父亲严厉的外貌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对孩子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我们深有体会,而且铭记在心。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地说道:“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而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
安东·巴甫洛维奇早在17岁的时候,就给堂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契诃夫写信说:
父亲和母亲对我来说是举世无双的人,为了他们,我永远也不会吝惜什么。如果我将来有所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功劳,他们是极好的人,单是他们对孩子的一片爱,就值得赞扬不已,只这一点就可以忽略他们身上的一切缺点,而那些缺点,由于生活贫困,或难避免……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而透彻地评价了我们父母的性格和生活状况,评价了他们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他一生对他们都怀着深切的热爱。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不得不干许多活儿,不得不遵守父亲的清规戒律,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而快活。我们家里总是充满玩乐、取笑、顽皮和欢笑。在想出各种逗笑的即兴表演也好,搞天真无邪的儿童恶作剧也好,安托沙总是起主要作用,由他带头。例如,我一直记得,安托沙组织我们小孩演戏。有一次我参加演一个戏。当时我还完全是个小姑娘。我演的角色是塔季雅娜·切普鲁尼哈,我记得,根据剧情的发展,安托沙在“舞台”上当着大家的面拥抱我,我简直窘极了。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对果戈理的著作,对他作品里的人物都非常入迷,并且经常扮演这些角色,把整场的戏演出来。两个哥哥,安东和伊万都打扮起来,穿上乌克兰民族服装。哥哥尼古拉演过果戈理的《圣诞节前夜》中的一个场面,他扮演醉汉丘勃,在暴风雪中寻找自己的茅舍,演得逗极了。
在我们家,《钦差大臣》享有很大的声望。我们小时候在家里经常演这个戏。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演市长。他穿上他漂亮的中学生制服,纽扣闪闪发光,为了显得有气派,他在制服里垫些小枕头,该垫高的地方都垫高了。他的制服外面,没有佩剑,只挂一把平常的马刀,胸前戴着自己做的勋章。他化装很仔细,而且应该说非常精致。在所有“演员”当中,无可争论,他最有才能。如果用戏剧语言来说的话,他实际上既是导演,又是布景设计师。
哥哥伊万通常演赫列斯塔科夫,我演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市长的女儿(在缺少合适的“女演员”的时候,我也演市长的妻子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时演仆人奥西普,有时演法官利亚普金-加普金。我现在想起这个戏的某些情节还忍不住要笑。例如,有一幕,赫列斯塔科夫(哥哥伊万扮演)向我走来,要拥抱我,我应该躲开他一点。可是我躲开他远远的,因为当着观众的面让人拥抱,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观众通常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戚、熟人和邻居。最后,我一个劲儿往后躲,一直退到房间的墙上,所有的对白都念完了,赫列斯塔科夫原该吻我一下,可是始终也没吻着。
哥哥安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异常敏锐的观察力。例如,他在城里、学校里或者熟人家里看到的事情,他能绘声绘色地描摹和表现出来。每当他模仿我们熟人身上可笑的特点,都要招得所有在场的人,从小孩到大人,笑得东倒西歪。安托沙甚至还开兄弟们的玩笑。他常给他们取外号,那些外号幽默极了,不过有时也挺气人。比方说,他管哥哥尼古拉叫“独眼龙”,因为尼古拉讲话时养成习惯,总眯起一只眼睛。他给尼古拉还取过一个外号,叫“站在大船上的细面条”,因为他两条腿又细又长,穿着非常瘦的裤子,脚上却穿着肥大的皮套鞋,样子确实滑稽。他那条裤子还是安托沙亲手做的,那时候他在一个技工学校学裁缝。我的几个哥哥在上中学的同时,都到那儿学习过。当初,安托沙给尼古拉做那条裤子的时候,尼古拉非要他把裤子做得尽量瘦不可(那时穿瘦腿裤时髦)。于是安托沙就极力照办了。
我也没逃脱可笑的外号。安托沙给我取了整整三个外号:“哈巴狗”、“小扁豆”和“光环”。最后一个外号惹得我特别生气,我为这个外号哭过。我小时候头发又短又直。为了让头发别乱,我用一个半圆形的梳子把头发卡住,可是头发仍旧不贴顺,梳子周围的头发竖起来,像光环似的。哥哥给我取的外号就是由这儿来的,可是我心里觉得十分委屈。
每逢节日,教堂举行祈祷时,我们的父亲一概要热心去参加,而且硬逼着全家人都得参加。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有时候这很不轻松:早早就得起床,还要在教堂里站很久。可是哥哥们即使在这种场合也还要开玩笑。比如,有这样一件事。
清晨。大家还睡得正香,根本不想起床。可是母亲催着大家起来,不然会耽误晨祷,父亲就要生气。父亲自己早在大家前面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准备好,只有安托沙一个人用被子蒙着头躺在床上,不理睬母亲的催促。
“安托沙,快起来……该去晨祷了。去晚了父亲会生气的,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
哥哥蹬蹬腿,不愿意听。
我们没有等他就到教堂去了。尼古拉也没有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早已经走了。他有一种天生的乐感,很喜欢在钟楼上打钟,当他把所有的钟都打响的时候,那钟声特别响亮悦耳,和谐动听。
我们往教堂去刚走了多一半路,出乎意外地瞧见安托沙在前面。原来,他还在被子里就穿好了衣服,我们走后,他很快起来,洗了脸,穿过几条小巷,绕到我们前面去了。
我们快要走到教堂了,可是突然……钟楼上所有的钟全敲响了。这么庄严的全部钟鸣,完全不是时候,大家都感到奇怪。原来,尼古拉在钟楼上看见母亲来了,就决定鸣钟迎接。全部钟鸣只有在教士临近教堂的时候才能用。不用说,哥哥由于干了这件事,遭到了父亲的处罚。
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常常回忆起尼古拉用钟声迎接母亲的事,每次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我的兄弟们逐渐有了男孩子自己所特有的爱好,他们不让我加入他们的活动。虽然我还是跟他们一块玩棒球,玩羊拐子,可是毕竟跟兄弟们一起玩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加上对母亲的依恋,也使我这一时期不能和他们接近。夏天,兄弟们经常结伴到海上去捕鱼,到草原上克尼亚扎亚村我们的爷爷那里去,而我留在母亲身边。
那时候,大哥亚历山大在中学高年级读书,不大与我们来往。他觉得,他已经不适于跟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块儿生活和游戏。后来,他上中学最后一年,就干脆从我们家搬出去,到中学校长埃·鲁·赖特林格尔家去住,为他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得些报酬。
1875年8月,我们家里的人口减少了:大哥和二哥到莫斯科去上学。大哥亚历山大中学毕业后,考进莫斯科大学,二哥尼古拉在绘画方面显露出很大才能,也跟大哥一块儿走了,希望考进绘画雕塑建筑学校。
这个时期,我们父亲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他在给莫斯科的两个儿子的信中,开始流露出忐忑不安的情绪。例如,他在1875年8月18日的信里写道:“我的买卖一天不如一天。我已经有点灰心丧气,妈妈看到我这样,也不知如何是好。唉,钱,钱!要不去托人情,清清白白地弄到钱可真难……”
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显出做生意的才干,虽然他有一个“三等商人”的称号,可是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地地道道的商人。最后他的生意陷于困境,欠下大堆债务,特别是他又筹划盖了自己的房子,导致他的铺子不得不停业。1876年4月,父亲彻底破产。4月23日,他为了躲债,几乎是从塔甘罗格逃到莫斯科去的。这一事件使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生活状况急转直下。
父亲在莫斯科住在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那里。他们俩过着清苦的大学生生活,父亲来到,他们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在塔甘罗格盖好的房子被夺走抵了债。
1876年7月,我们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米哈伊尔也到莫斯科来投奔父亲。安托沙和哥哥伊万留在塔甘罗格,继续在中学读书。可是伊万不久也搬到我们这里,只有安托沙一个人留在塔甘罗格。
在故乡那种无忧无虑的幼年时代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莫斯科的艰难贫困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