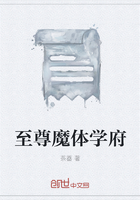何氏爱着她的丈夫,她像所有女人一样,渴望被关心和宠爱,只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唯一的梦想。
在许多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夜晚,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那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孤单与痛苦,她找不到可以让自己解脱的方法,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消磨着她那原有的美好,她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当看到丈夫对另一个女人极尽体贴之能事时,她的绝望和怨恨,却从未有人理会过。
林徽因只看到了母亲丑陋的一面,却没能像对待其他朋友那样,给她多一些的体谅,甚至不理解母亲的难处和苦楚,母亲曾经踮起脚跟,想要拥抱幸福,却被狠狠地摔倒在地,没见到半点幸福的影子。
有多少人同林徽因一样,将善解人意统统给了朋友,却将蛮横无理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自己的疏忽,注定会成为一个遗憾。
有矛盾,要及时说出来,及时化解,不要憋在心里。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杀伤力巨大,你怎知它不会隐藏在心中的某个小角落,偷偷地生长,直至有朝一日成为悲剧的导火索呢?
将好坏看开
死亡是生命的最后一幕,曾经的悲欢离合也将在这里终止,所有的恩怨情仇也将一笔勾销。
生老病死,人间常态,或早或晚,人人都须面对,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把好与坏、生与死都看淡、看开。
抗日战争胜利了,林徽因终于可以从偏僻荒凉的小村镇回到心心念念的北平了,崭新的黎明和曙光却并没有给她带来生的奇迹,她在一日一日地走向死亡。
梁从诫回忆道:
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著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按:林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学生助手程应铨的未婚妻,走入他们的世界的",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致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著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四七年前后她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外界就有她病逝的传闻,李健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咀华记余·无题》感叹:"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
好在她福大命大,病逝只是无中生有的误传而已。
1947年,她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严重感染的肾脏随时都会夺去她的生命,终止她的呼吸。
同年10月,病情恶化的林徽因住进中央医院,病床上她托人带话给张幼仪,询问能否见上一面。虽不明缘由,张幼仪还是带着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来到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打量着这对母子,似乎在确认些什么事情,最终还是没能说出一言半语。
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想见一见张幼仪母子,她没有说,我们也就无从知晓,张幼仪也没有问,这是两个女人无声的交流。
这一次住院做手术,林徽因自知凶多吉少,提前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算是最后的道别。没有悲怆,只有淡淡的不舍与留恋。
然而,她是幸运的,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以主人翁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续熬夜,一再坚持,似乎一下子恢复了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实际上,她的身体健康已近枯竭。亲近的朋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有必要带上一个懂事的人,知道话说到什么时候需要刹车,管住舌头,及时告辞,避免过度耗费她的精力。
50年代,林徽因收获了许多荣耀,而每一份荣耀背后,都隐藏着十二分的辛勤和愈发枯竭的生命力。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偶遇萧乾。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叫了她一声"林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她也希望自己不要变老,不要生病,她还有许许多多未能如愿的心事,还有许许多多刚有眉目的计划,她积攒了一辈子的知识学问、经验技术,都要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钱美华在《缅怀恩师》中记录了这么一件小事,在同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健康,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
生命还在继续,她没有理由放弃生活,不仅不能放弃,还要愈加珍惜所拥有的分秒与朝夕。
幸运之神没有一直眷顾这个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女人。
1954年的秋天,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必须暂停一切工作,安心静养。
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记叙:"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1954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移居到北京城内。几乎同时,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也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又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到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处在精神昏迷的状态。
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尽一切努力进行抢救,肺部大面积感染的事实已经预示了她生命的终结时刻即将到来。
3月31日深夜,弥留之际的林徽因用尽力气,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好心地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可是,她没能再等到明天。
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她51年的生命旅程。
想要说的最后几句话,终是没能说出来。
梁再冰的《我的妈妈林徽因》里写道:"当父亲被扶到病房时,从来不流泪的他哭得不能自已,坐在妈妈的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听着真令人肝肠寸断。"
又是一场生离死别,而这一次,是她带着遗憾离开。
再仔细端详一下她的面容吧,下一世,她将以其他面貌出现,此生是无缘再见了。
也许上天待她并不友善,一生的苦难多过安稳,她却都平静地接受了。
远在1945年的时候,医生就已经对她宣判了仅剩5年的寿命,还是在静心休养的前提之下,而她不顾警告将最后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她从死神那里争来的,能坚持到1955年,已是不易。
就像1947年秋她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看到这段文字,仿若能看到她俏皮的微笑,得意于自己的顽强。
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时刻面对死亡,也时刻迎接死亡。
不愿就这么草草离开,却不得不默默地准备离开。
生命是生与死的循环和轮回。
在挚友徐志摩去世4周年的时候,她挥泪写下《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其中有一段令人记忆尤深:
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她不明死的奥秘,却不忌惮它。从最初的最初,她就决定用自己赌未来,将好与坏都置之度外。死亡注定浸满他人的泪水,弥漫着悲情的色彩,却是人一生之中不可逾越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
除非临近死亡,否则永远不能感知它是什么滋味。与其将最后的时光用来恐惧害怕,倒不如留着力气和亲爱的家人朋友说声感谢,说声再见。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直到死去的那一刻,都没能参透人生的真谛,都没能勇敢一回,将释怀无畏的笑容留在世间。
不留遗憾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生的每一天里,尽量将一切看淡、看开,已知活着的不易,又何须再去纠结于既定的事实,上天可以左右你的命运,却不能左右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