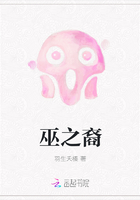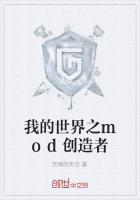梁思成此时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本书翻译成与当今建筑学可以融会贯通的参考书籍。他对这本书的喜欢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状态,遂为第二个孩子起名为梁从诫,希望儿子能和李诫一样,成为中国有影响力的建筑学家。
生下女儿梁再冰之后没过多久,林徽因回到北京香山养病。她的身体在生产后极其虚弱,初为人母的喜悦抚平了身体上的创伤,女儿带给她生命的美好、宁静和温情。
她静静享受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听到她哇哇大哭会心疼,看到她开心的笑容会喜悦,女儿操纵着她的喜怒哀乐,仿佛一下子填满了她的心灵,人生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忍着裂骨的剧痛,拼尽全力,将自己的骨肉带到人间,赋予他独立的生命。这只是母爱的开端,从此,她承担起一位母亲的职责,无私地奉献着她的全部。
每一位母亲,都曾是一名花季的少女,拥有令人羡慕的青春年华,她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只是生活就是生活,它不是由梦幻装点,而是布满琐碎和平凡。
时间教会她忍耐平淡,付出时间和精力,她开始快速地成长,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母亲,她用最大的心力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正如同她的母亲曾经那样守护她。
每个孩子,都是母爱的传承之作,凝聚了一个女人毕生的心血,是她此生最骄傲的杰作。
她看着你一天天茁壮成长,也在感受着自己一天天衰老,而这却使她由衷地感到喜悦,因为她的孩子,快要长大了。
当然,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母亲不仅是最强大的守护者,还是精神的引导者。林徽因是一位很有思想见地的女人,作为母亲,她也时刻鞭策着孩子们成长。
林徽因的性格独立自主、潇洒不羁,不受婆婆的喜爱也有一定的道理,她不喜欢做家务,总认为这无聊的事情消磨了她的大好时光,然而,她虽嘴上不情愿,行动上却做得比谁都出色。
她依旧无愧于一位优秀的家庭主妇,一位温柔的母亲。
30年代,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家位于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租来的四合院。方砖铺地,干净整洁,一个美丽的垂花门装饰着小院,屋里摆放着几件从旧货店里精心淘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时无意捡到的残破石雕,以及罗列整齐的书籍。
她用自己的生活趣味和艺术品位,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生活氛围。每逢假日,总有亲朋好友聚在这个小院落里高谈阔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潜移默化中熏陶着两个孩子。
林徽因素来对书爱不释手,自然懂得薄薄的书页,对于个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怎样重大的影响,因此,她也用书陶冶孩子的心灵。
卢沟桥事变后,战争愈演愈烈,为了避难,他们一家开始了长达9年的颠沛流离。
梁从诫小学二年级时,一家人刚从长沙辗转来到昆明,困顿无助的生活里,林徽因始终不忘对孩子的教育。她十分擅长朗诵,一篇《唐雎不辱使命》,在她绘声绘色的朗读中,两个孩子深切感受到了唐雎的英雄胆色。
3年后,颠簸的生活在继续,一家人又离开昆明来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连日来的奔波,使得林徽因旧病复发,卧床不起。
行动不便的她只好待在床上,庆幸的是有书籍的陪伴。她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使她受益匪浅,于是要求儿子梁从诫认真去读,并在读过之后一起细细体味作者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另一本《米开朗琪罗传》是英文版本,两个孩子根本读不懂,她便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声情并茂地描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
闲来无事时,林徽因会招呼两个孩子坐在她的床前,用感情充沛的声音为他们朗读她写的诗文。
许多年后,儿子梁从诫带着深沉的怀念,在回忆中写道:"她的诗本来讲求韵律,由她自己读出,那声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无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
女人本身就是水做的,柔媚动人,而成为母亲之后,更是激活了她所有的温柔。
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她的柔情和细腻,影响着孩子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去感受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处世之道,也会从这点滴中积累、变化,形成自己独到的眼光。
林徽因自身从未放弃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她的身上有着中国妇女缺乏的洒脱与无畏,她要求平等,她也以平等的身份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在她与丈夫外出考察的时候,思念成了最大的心魔,她需要工作,却也时刻惦念着家中的小不点儿。而她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她把一个8岁的孩子当成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大人,她在旅途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甚至考察所获得的成果,事无巨细地写进信中,邮寄给孩子们。
如她这般的态度对待孩子,放眼现在,也是少见的。她试着去和孩子交流沟通,彼此打开心房,互相倾听。
忆起那段担惊受怕又缺衣少粮的日子,梁从诫有些怀念:"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精神上很富足。"
精神上的供养是一个母亲的闪光点,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撑。
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总是与叛逆脱不开关系,而叛逆并不等同于坏,只不过是家长并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尽管每个人都有过童年,也都曾一步一步走过青春的隧道,有过彷徨和忧伤,却不一定就能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
试着去了解一下孩子的想法,以前辈的身份去引导和开解,帮助他/她平稳地度过青春期,学会成长,学会做人。这正是为人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宝贵的财富。
梁从诫曾自嘲说,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说,自己如果说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母爱是毫无保留的付出,是完全彻底的爱护。
她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子女身上,不计较得失,不问回报,用生命为孩子们的前程护航。每位母亲都是平凡普通的妇女,她有着自身的局限和狭隘,可这样的缺点并不会影响她对子女的爱。
做一位好母亲的同时,如果有机会,也做一位好女儿吧。
身为人母,也一定更能体会母亲的艰辛与不易,好好孝敬她老人家,用行动告诉她,她的孩子终于强大到可以像她曾经保护自己一样,去保护她。
女人的重任是护她安好,保她喜乐。
这个"她",有自己的孩子,也有自己的母亲。
怀着平常心去阅历磨难
改变不了的现实,与其终日苦苦挣扎,在绝望中沉沦,不如放宽心,悦纳周遭的不完美。
世间没有哪一份苦难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老天爷从没有打算要陷害谁,刁难谁,算计谁,人生最初始的设计就是需要遍尝百味,才不枉此生。
请老天爷赐予人们"可以怀着平常心去阅历磨难"这项技能。
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她在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描述了水深火热中的重庆:"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
浓烟滚滚,烟气弥漫,恶劣的环境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林徽因所处的李庄距离重庆几百公里,情形大致相同,刺鼻的硫黄气味漫天盖地,直接导致她肺结核的病发,战争对人类的摧残,是对其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破坏。
老金赶到李庄看望林徽因一家人,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困苦的生活,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林徽因,她的病情已经极其严重,让他不忍心直视。
老金在平常的书信来往中早已获悉她旧疾复发的大体情况,谁知相见时,才确切地知晓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为了给林徽因改善伙食,补充营养,老金从他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钱,跑到镇上,一口气买了十几只鸡回家饲养,盼着能早日生蛋。他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京总布胡同时,就养过几只大斗鸡,并且还有同桌就餐的趣闻和请医生"助产"的笑话。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说:"在昆明,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呀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在老金的精心饲养之下,千里迢迢买回来的这十几只鸡,长势很好,不仅健康,而且没让大家等太久便开始下蛋了。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老金用哲学家的处世之道对林徽因和梁思成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
不要总揪着得不到的东西不放,珍惜已经拥有的,用平常心面对得与失、功与过。
在当时的环境下,医疗条件更是简陋,没有正式的医生,没有任何药品,生病的村民只得硬扛下去。
病情日渐加重的林徽因,发烧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可家中唯一一支体温计也被儿子不小心摔碎了,没有了计量体温的工具,她只能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猜测体温度数。
灰蒙蒙的天,总瞧不见太阳,整个人就愈发觉得阴沉。
躺在床上不停咳嗽的林徽因,深陷的眼窝没了神采,苍白的面色让她看起来更加虚弱,病魔将她本来拥有的美丽夺走了。
许久没有照过镜子了,聪慧如她,也知道自己大概是个什么模样,可她没有力气去计较这些,因为能活着就已经很不易了。
在她给沈从文的信中,不难看出她的痛苦和无奈:"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
她想将无望的生活看透,上天的旨意又是如何安排她的人生,是走是停,是去是留,她只需要一个痛快的答案,她有平静接受的心理准备,可上天不回答,只是沉默着。
关于这段生活,梁再冰在许多年后曾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回忆: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帕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四肢无力的林徽因,坚持与美国好友费慰梅保持通信,歪歪扭扭的字迹寄托着她的情感。
费慰梅说:"从来信中看,那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泛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蓝色信纸。但共同的特征是,每一小块空间都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途。那用过了的信封,上面贴的邮票一望即知,当时即使是国内邮件,邮资也令人咋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信封里装了好几封信,这样一次寄出去,可以在邮资上避免一次挥霍。"
关于那段提心吊胆,并被疾病与贫困纠缠的日子,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详细地讲到了李庄的生活:
使我烦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
…………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处于战争岁月的知识分子,除了一连串的苦难,也有片刻的欢乐时光。每到下午四点钟,梁思成与助手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弄一个大茶壶,与老金等人喝起下午茶来,以消解苦难与身心的疲倦。
此时严酷的暑热已经退去,病中的林徽因也请人把行军床搬到院内,与大家一道喝茶聊天,寻回一点生活的温馨:
那些伺候了我们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烂衣服必须拿出来修补了。思成要到重庆去,他的东西必须先补。去年冬天他在重庆把它们磨损得这么厉害,它们就像大战后的军舰,必须拉到干船坞去大修,有些被鱼雷或炸弹毁坏得这么厉害,要修理还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在苦难中煎熬着的人,心绪多是复杂慌乱的,谁也不愿意与疾病、贫穷扯上关系,若不能大富大贵,至少衣食无忧,平平淡淡也好。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谁也躲不开,既然遇上了,就不如以平常心视之、待之,那些或大或小的不顺心,也是欺软怕硬的,越是胆小软弱的人,就越是受欺负,越是坚强不屈的人,就越是容易将不顺心打跑。
自救是最好的办法,那些能够说服别人的大道理,人尽皆知,可到了自己这里,却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
那就不要去管什么人生哲理,再大的道理也是人总结出来的,目的就是劝解人心,既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如从别的地方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