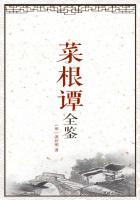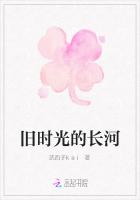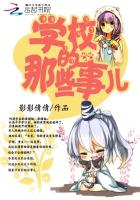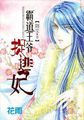人所共知,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大家章炳麟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章阁下虽然以偏概全,但的确说中了一点:日本幕府统治末年的英雄豪杰所以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与漂洋过海到日本的阳明心学中所包含的自尊无畏、立志改革的狂狷胸襟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一节)日本:心学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心学在日本生根发芽,光芒四射,先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叫了俺桂梧的和尚,一个就是阳明学日本分部的创建者中江藤树。
当王阳明在杭州思索圣人之学的1503年,了俺桂梧以日本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潜心研习中国儒学(其实就是朱子学)。没有资料证明他和王阳明是何时相识,不过两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就在10年后的1513年了俺桂梧回国时,王阳明特意为他做了篇动人的送行文章,搞得了俺这位道行高深的和尚甚为感动,一致流下泪水。1513年,距王阳明创建心学已6年,了俺和尚对这门几乎近于神迹的学说必然有所了解,当他回到日本后,在给政府提供朱子学的同时,也就把心学顺带记录下来。从此,心学在日本开始生根,但发芽,却很艰难。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思想欲破茧而出,化蛹成蝶,必须有独立性。但15、16世纪的日本,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要依附于佛教和神社,中国儒学虽然早就传入日本,却只是被统治阶层当成教养的工具,儒学被统治阶层垄断,下层人无缘见到儒学的神秘面目。
转机来自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1542--1616),这位明智之士发现中国朱子学的纲常名教很利于培养忠实的奴仆和恪尽职守的官僚,所以大力提倡朱子学,并以政府的名义在全国大力推行。如你所知,一种思想一旦被官方确定为意识心态,那这种思想理想很快就会僵化,失去活力,成为人人都想扳倒的不倒翁。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王阳明创建心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跟已成为僵尸的朱熹学说对抗。在幕府统治日本的二百多年里,朱子学作为显学,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不过,朱子学给日本贡献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附带品:武士道。在中国,朱子学连这点附带品都没有贡献。
武士道精神的提倡者正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中江藤树(1608--1648),和王阳明一样,中江藤树从小接受的就是朱子学教育,他天赋异禀,自学《四书大全》,20多岁时在日本就已跻身朱子学顶级专家行列。
有一天,中江藤树在翻看中国儒家学说时忽然发现,中国的“儒道”其实就是日本的“武士道”。中国的“儒道”讲究“臣为君死,毫不保留”。也就是“忠”、“勇”精神。那么,日本的“武士道”又是什么呢?
日本“武士”阶层起源于646年中大兄领导的大化革新。
--注意这个人,就是他后来在位的663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白江口海战,中国彻底打残了日本,使的日本马上掉头来学习唐朝的一切。
所谓大化革新,就是仿照当时中国政制模式,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既然是中央集权,那百姓的土地就必须收归国有,但多年后,日本中央权力式微,各地的贵族地主通过各种手段聚集了大量土地,建立起了“庄园”。“庄园”需要维护和保护,防止被贫民抢劫。所以,贵族们就请了很多保镖,这些保镖就是武士。随着武士的不断增多,武士家族开始出现,并力量茁壮。1192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了镰仓幕府,这是日本第一个武家执政的政权,武士阶层开始正式登上日本的历史舞台。
由于武士出现的原始目的就是保护主人的财产,所以主人必须要他死心塌地的为自己卖命。这就形成了一种武士之道。所谓“武士道”指的是武士在日常生活以及在执行任务时所需要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包括忠、孝、勇、礼、诚、知耻、名誉、勤俭等等。
【2】
不过,武士道发展到中江藤树时代时,虽然已几百年,可那些行为准则没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的“道”就不能称为“道”,它只能是一种外在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中江藤树有一天突然发现,中国的儒道恰好可以为武士道提供理论源泉。也就是说,他把儒家的理论(其实就是朱子学)嵌进武士道精神中,使之相和。这是一次对武士道精神高度的理论贡献,在他的整合下,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的精神。
所以,中江藤树忽然旱地拔葱,成了日本的大圣人。
如你所知,中国儒家系统中的“圣人”是活宝,千百年来,可怜兮兮的不超过十个人。中国人口比日本要多出几十倍,才出了十个不到。而稀少人口的日本忽然间就出了一个,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不过,日本士兵后来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武士道精神,比如珍珠港事件中的自杀式攻击,战败后的剖腹和为了尊严不惜一切代价的抗争,的确让我们刮目相看,所以对武士道精神理论贡献人中江藤树的圣人头衔可以默许。
如果你对中国儒家稍有了解,就完全可以肯定,中江藤树创建的武士道精神理论,并非全来自中国儒家。如你所知,中国儒家门徒虽然慷慨激昂的提倡杀身成仁,但真正做到的没几个。儒家门徒大都讲究明哲保身,讲究的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其实就是贪生怕死。中国儒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损毁。更有大儒大言不惭的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武士道精神却是不怕死,为了效忠主子和自己的尊严,视死亡如儿戏。两种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无法搞明白,中江藤树为什么会把儒家口头上的表演当成事实。可能只有一种可能,他没有来过中国,没有见识过儒家贪生怕死的烂污精神。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世界上发挥了令人震撼的爆破力,原因只有一个:武士们从小就接受没有人性的思想教育。比如日本最出色的武士世家山本常朝家族就规定,家族成员5岁时就要斩杀狗,15岁时就要斩杀死罪者。前提是,必须“义勇奉公”,只有为了公义,人命才无关紧要。如何保证武士不滥杀,当然需要平常训练保驾护航,克己、理性的勇武、知道羞耻是武士的三门必修课。
【3】
王阳明说,人唯有能克己,才能成己。只有理性的勇武才是真正的勇武,否则只能是屠夫。只有知道羞耻,才又奋发向上的动力,才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不过,就在中江藤树用朱子学为武士道提供理论后,忽然转向朱子学的死对头阳明学。这缘于他三十七岁那年忽然读了《王阳明全书》,彻悟之下发现,只有王阳明才真正继承了儒家大亨孔子的精髓,朱熹只是形似而已。
其实任何努力钻研朱熹学说的人只要拿起王阳明的心学,都会有豁然开朗,重见天日的感觉。因为王阳明的学说飘逸轻灵,与朱熹那一本正经、沉重的学说相比,使人耳目一新。而且,王阳明心学的一大特点是,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入门特别容易。中江藤树不过一年的时间,就切中王阳明心学的动脉。他说,阳明心学告诉我们,道德秩序的最高范畴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明德”、“慎独”、“格物”,每个人都能成为圣贤。而真正的学问(圣人之学)就是“以心读心”的“心学”。
“炼心”一时成为日本阳明学的最高指示,中江藤树之后,日本阳明学派最光辉灿烂的一派就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中江藤树的弟子渊冈山滴水不漏的继承了中江藤树的“炼心”思想。而另一派虽然承认中江藤树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但却走上了王阳明心学最重要的一条路,这就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着名人物有熊泽蕃山、大盐平八郎和后来的维新豪杰们。
不过,在当时的日本,虽然有这些精英苦心孤诣的传播阳明学,可在朱子学当家做主的时代,阳明学没有大显光辉的机会。
中江藤树和他最得意的弟子熊泽蕃山死后(公元1691年),阳明学进入死寂般的墓道期。至于另外以事功为主要思想的知行合一派,更是因没有平台,而销声匿迹。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就是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后期,阳明学派突然如火山爆发一样,震动天地。
第一个把王阳明心学用到实践上的就是大盐平八郎。
(第二节)揭竿而起的心学门徒大盐平八郎
【1】
王阳明心学力量在日本首先被大盐平八郎展示,大盐平八郎是日本史上出类拔萃的起义者之一。他用心学武装自己,从而发动了武装革命,证明了心学无孔不入的渗透力。
大盐平八郎出生于1793年,正好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江户时代后期。大盐平八郎的少年时代的颜色并不鲜艳,反而暗沉。7岁时老爹呜呼,8岁时老娘离世,他跟着爷爷一起生活。14岁时,他人生拐点出现,继承了爷爷的大阪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职务,而当上了“见习与力”(实习警察局局长)。这是一个有分量的职位,地位仅次于奉行(地方行政兼军事执行官)。
14岁,不过是初中生毕业的年纪。忽然平步青云到他从未想过的高位,自然神魂飘荡,忘乎所以。他可能在那个显赫位置上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一名武士向他言辞挑战:你这样的人不配领导别人。
大盐平八郎又羞又恼,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武士是最让人崇敬的一个职业,遗憾的是,他不是武士。当他在自己的家谱上看到先祖曾经是一名武士时,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念想,他开始以青年人震惊的热情学习文武之道,精读朱子学,学习骑射和枪炮技术。经过五年时间的刻苦修行,他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武士。
这一时期,他的梦想和几百年前的王阳明一样,都想成为“圣人”。所谓“圣人”无非是建立下震动天地奇功的人。然而,也和王阳明一样,他在左冲右突的现实学习和践履中,总是碰壁,没有平台给他施展抱负,况且,他的抱负只是好胜心驱使下的冲动的产物。同时他也深刻的感觉到,自己那点学问修养简直不值一提。人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时候,王阳明有过,大盐平八郎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命不凡是人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关卡,能过关的人,会继续激情向前,止步不前的人会活在由自己编织的梦幻里,成为一事无成的人。
大盐平八郎很幸运,他过了关。他认为,建立震动天地的功业是可遇不可求的。他感到人生的迷茫,于是,毫不犹豫的辞职,一头扎进朱子学中,埋头苦读,然而几年后,他发现朱子学并不能让他心灵得到多少益处。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学术界的风气是训诂,只在字里行间打转。大盐平八郎苦不堪言,就在他心灵前景黯淡时,王阳明心学照亮了他眼前的黑暗。
【2】
大盐平八郎是从中国明朝人吕坤的着作《呻吟语》上发现的阳明心学,吕坤是王阳明心学忠实的门徒,专心致志的传播和实践王阳明心学,他的着作《呻吟语》中的人生哲理虽然取材广泛,但都以王阳明“良知”作为主导思想。大盐平八郎粗读王阳明心学后,恍然大悟,如脱胎换骨。他后来就有了对心学的感悟:人之初,本有一颗明辨善恶的正直的心,不必向任何人请教。但是,这正直的心却被私欲给遮蔽了。所以,人应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克服私心,以保持住一颗有良知的正直的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就能够团结广大民众,实行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政治。
这就是王阳明说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一个人如果能恢复被私欲遮蔽的良知,那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样的人因为本身具备人类最高尚的道德情操“良知”,就是一块磁石,能吸引广大民众来到自己身边,为美好的政治贡献心力。
不过,大盐平八郎只是把王阳明的“心即理”当作心学入门的一把钥匙,他在这座海洋般的宝库中找到了无价之宝--知行合一。其实所谓“知行合一”,无非是,你心中的想法必须要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开始身体力行,说到做到,无时无刻不在反省自己的行动是否带有私欲?努力做到和那些淳朴善良的民众一致。当他再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时,一个秉公执法的清廉“与力”(警察局长)出炉了。他的声望如日中天,在日本岛上直冲霄汉。
1830年,大盐平八郎见幕府的腐败统治和百姓所受的苦难,所以决定拯救众人的心灵,于是彻底辞职,开办“洗心洞”学堂,传播王阳明心学。“洗心洞”学院的传授课程排除了空洞理论,严格实行王阳明的心学宗旨--务实(知行合一)。
大盐平八郎的“知行合一”除了说到做到外,最重要的就是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身体力行。和王阳明不同的是,他的大多数弟子都是农民。大盐平八郎对农民有着炙热如火的感情。因为在官场多年,他看透了那些知行不一的狡狯人士,朴实的农民才是有良知,能知行合一的人。
心学的“知行合一”被大盐平八郎演绎成了另外一种意思:对百姓的无限深情的怜悯和对那些特权阶级的深入骨髓的痛恨。在他的心学学习笔记中,“一切人都应受到宽宏大度的待遇”、“贫农也是自天而降生的人”石破天惊的思想和王阳明的“人人都是圣人”何其相似,简直就是大盐平八郎在依葫芦画瓢。他在让贫民肯定自己自尊的同时,还对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不恨身死恨心死。心若不死,乃与天地作无穷之斗。这是心学中顽强不屈的进取精神,王阳明就曾对他的弟子说,你那颗心要时刻跳动,不然,它就是一块死肉。只要心不死,去真心实意的追寻良知,那就是心学意义上真正的人。大盐平八郎的“与天地作无穷之斗”的进取思想,注定了他站在弱者的立场说话做事。王阳明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终于,在1836年,大盐平八郎用实际行动验证了他是个真正“知行合一”的汉子。
1836年这年,日本岛国气候怪诞,稻子收成不如往年的一半,所以米价翻了两三番,贫苦之人无钱购买,遍地饿殍。日本幕府对百姓的尸体无动于衷,大盐平八郎坐不住了。他向政府多次请命,要求政府拯救灾民,但政府已经冷血,投进的请命书如同投进了坟墓。
大盐平八郎气冲斗牛,因为他知道,政府的粮仓里有米,但这些米却被一些和官员有关系的商人拿出来高价出卖。大盐平八郎深知,如果你没有正当渠道讨取自己的权益,那只能自己开辟渠道。他开始和弟子们秘密的赶制火药、筹集枪炮,准备干掉政府官员和奸商,开仓放粮,拯救灾民。
【3】
第二年(1837)2月19日,大盐平八郎率领100多人拿着自制的火药和枪炮,冲上大街,直奔政府粮仓。这次起义的过程没有任何可以渲染的地方,100多人拿着山寨武器,很快就被政府军镇压。大盐平八郎逃到一个村庄躲避一个月后被发现,政府军包围他的住所后,他自杀身亡。有一种说法,大盐平八郎自焚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