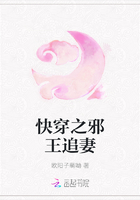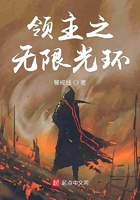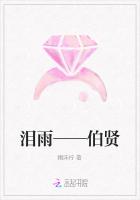大量的诗歌断裂、扬弃传统,抛弃了千年的语言积累和现代汉语新传统,尤其抛弃真正的民间和当下。诗歌导致语言消亡。如果说朦胧诗冲破简明、定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构造话语形象的现代方式,成为日常和文学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可以断定新近的诗歌却试验失败。
李湟水:雨虹、贝贝和我分别出生于上个世纪70、80和60年代,恰恰经历了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我的经验和阅读是80年代文学的热烈和朦胧诗争议登场,雨虹恰恰经历了朦胧诗后各种诗群崛起的90年代,而贝贝遭遇的是世纪交替,“80年后”青年的青春色彩及其诗歌的各种展现。
王贝贝:我所经历的正是一个诗歌创作五花八门的时代。在我大学的四年中,山大还是形成了一部分稳定的诗歌创作群体,我记得当时我就读的中文系里出过几个校园诗人,我的下铺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历史系、管理学院、哲学系甚至环境工程系各有一些人常常有诗作见诸校内报刊,我认为这批人正是当时校园诗歌创作的主力军。这也与当时校园文学创作氛围浓厚不无关系,中文系曾坚持组织过一段时间的诗歌沙龙,一些教授也很支持,并参与进来,校内的文学协会也组织过类似的交流,并且还有自创诗歌的朗诵比赛,我记得还诞生过一本纯创作的诗刊。总体来说,当时的校园诗歌创作相对繁盛,质量也比较高,有些作者会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出现。但是在复旦,我还未发现这样稳定的诗歌创作群,大家对诗歌的热情并不高,只是偶尔会在校园BBS的文艺版上发现一些诗歌的影子,这可能与地域有关吧,在这个处处重经济利益的年代,大家对诗歌的热情早就磨灭殆尽。
焦雨虹:因为我一直在追踪阅读着当代诗歌,我可以简单地谈谈我对当代诗歌的具体阅读。《0档案》被认为是杰出的后现代诗歌文本之一,于坚在此进行了卓越的语言记录和试验。全诗大量堆砌官方鉴定材料,罗列了诸多“中心词”,在词语的层面上记录和清理了都市生活的核心领域,但是,除了记录,它的意义何在?它没有提供真正的诗意,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李湟水:诗人郑敏说,诗人扮演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即站在最尖端的地方看人类。我们走过文学现场,来聊当代诗歌,以此是否能审视和关照当代文化生活中某些精神情感的变化和表现。
焦雨虹:类型化的市井生活场景表示诗人对生活本身并不信任。他们关注的是别处的生活,自己的生活仅仅存在各自的诗歌理论宣言中。
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感慨道: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对于坚而言,生活在别处:金斯堡死了在他的祖国/我像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于坚:《短篇》P109)。
在唐亚平等现代女性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负担,新进女性诗人却只是琢磨一个缓慢但不可逆转的身体变质过程:一个女孩需要多少年/的经验和泪水,才能长成一个大妈(尹丽川《今天上午》)。
无奈的诗人把理想投向古代,那是闲适、与当前事实无关的前现代生活,充满音乐性:在清朝/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牛羊无事,百姓下棋/科举也大公无私/货币两地不同/有时还用谷物兑换/茶叶、丝、瓷器(钟鸣《在清朝》)。
更有些人貌似虔诚地走向上帝:我需要一个上帝,半夜睡在/我的隔壁,梦见星光和大海/梦见伯利恒的玛利亚/在昏暗的油灯下宽衣/我需要一个上帝,比立法者摩西/更能自主,贪恋灯碗里的油/听得见我的祈祷/爱我们一家人:十二个好兄弟(西川《上帝的村庄》)。
当初大声疾呼返回“诗本体”的个性张扬的人们,如今却过着同样无聊的、别人的生活。不管他们的主张、外表和性别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生活却惊人地相似。这就是诗歌死亡的原因?
类型化的零度写作导致诗歌没有生活,没有独特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感悟,生活不需要诗歌。我们必须承认,零度写作不是汉语诗歌的方向。知识分子转向上半身,转向西方,民间口语诗人转向下半身。他们一路误入歧途。
王贝贝:诗人注定在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里言说自己的生活理想,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忽视了周遭的存在,他们其实并不关注诗歌本身,而更多的是陷入自恋状态,诗歌是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属于一种简单而精致的思维,写诗也是个不断发现自己、发现世界的过程。所以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当代诗歌也许缺乏时代深度和心灵厚度,更多的是继承了传统,却无明显的革新,但无论如何都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真实表达,其中也不乏真挚明朗、富有思想活力的告白。而且应该有理由相信,依托于更加发达的传播媒介,诗歌将会有一个可观的产出量,而大的产量正是精品涌现的前提。
李湟水:朦胧诗的最大意义在于对“人”和“自我”尊严的发现,以一种悲剧般的英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震撼了80年代的青年,追求一种社会人格,拯救主题,他们的意识不是孤立的自我,而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精神有了一种诗性的连接。新生代的诗人们的最大特点是反对崇高、张扬分裂,强调自己的个性化和现代性(或是后现代)。他们更多的注重一种技巧和语言的卖弄。我也在最近翻阅了2004年《诗刊》上半月刊第一至十二期,我很欣赏诗人刘虹的话:“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诗歌不仅要坚守诗性的精神,还要保持语言的清洁和高贵。
焦雨虹:自己的诗歌语言在哪里?这是一个能让所有诗人发疯的技术难题。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蕴藏在自己语言中?这是一个更加深刻的本体问题。
先锋诗人于坚对此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细读某些先锋诗歌,不过是词汇的变化史。基本的构词法——‘升华’,从50年代到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是把红旗换成了麦地,把未来换成了远方而已。像海子这样的人进入神话,也可以看出在这个国家形而上学有多么广泛的基础。海子的写作还反映出所谓的先锋派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大词癖。脱离常识的升华式写作必然依靠大词。”
于坚自己的写作实践就朝向另外的极端。细小、物质,成为严正的追求。可是小说还贡献了“一地鸡毛”这样目光锋利的琐屑总结,当代诗歌又到达了哪里?
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的诗歌语言?许多权威的诗人及其理论保护人都宣称新诗的现代化在于“我手写我心”,用白话方式来言说完全不同的内心,但关键在于:只有这些语词系统包含的是已经变革或者直指生活的所指体系,那才是新诗的目的。可什么是变革了的生活内容?什么样的生活所指才符合新诗的目的?问题纷至沓来。
诗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西方,但是,为什么要向别人的生活(西方)借取灵感、词汇和意义?用外来诗歌参照、评价、指导现代汉语诗歌一直是学术的固有方式。在语言的所指和能指的层面上,现代化确实使得汉语不断吸收、转化,但语言不是天生的诗。构成方式完全不同的域外诗歌不能作为唯一标尺。
王贝贝:所以那些将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方完美结合的诗歌成品往往成为人们称道的对象。比如余光中和非马的诗,但并非说这就是诗歌语言的完美典范,语言在发展,我们也许还有别的选择。另外诗歌的生命并不仅仅存在于语言,晚清黄遵宪在“诗界革命”时就曾说过“我手写我口”,可见诗歌语言的真实生命力就在于以最坦白的方式来言说内心,历代诗人的追求莫过于此,诗歌不一定载道,但一定宣泄情感,而又正基于此,个性化的写作将产生个性化的诗歌语言。就像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
李湟水: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就像中国古典的诗词,李白、杜甫、白居易、南唐后主、李清照、柳永、苏东坡,除了各自一目了然的独特的风格,他们流传最广的还是那些语言简明、情感真挚而蕴积深厚的作品,或者说语言是非常清明流畅的。当时,当代诗歌好像缺少那么一种雄浑的内在品质,五四时期郭沫若《凤凰涅槃》,抗战时期《黄河大合唱》那样的高歌和气势不大被人们提起。可能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于优美的细致和颓废,特别是宋以来,中国文化在走向一种精致或者说衰微,而秦汉之风,大唐之气久已消失。这样的文化趋向或者成熟,反映在诗歌上,诗人的审美和抒情只是在情感的小河里倘佯,在语言的技巧上翻着小花样。
焦雨虹:中国汉字语词确实具有独特的描述性、表意性、构造性,但在诗歌的所谓现代化写作中,特别是诗歌宣言和权威的争夺中诗人们却不经意地抛弃了传统。
西方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比如维特根斯坦的能指与指理论虽然风靡西方,但是显然并不适合象形的方块汉字。单纯用西方言说体系进行现代化操作注定要失败。在新诗历史上出现过格律、新民歌和新自由等体裁,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成就。
以为诗歌止于语言,那是无知。以为诗歌与语言无关,那是无情(不懂情感)。
其实诗学建设只要规划基本的评价标准指针信条就足够了,指导、总结、期望、宣言、争夺常常无济于事。
经过百年的革命、解放、疯狂和平静的历程,现代汉语早就是成熟的,而且出现了众多杰出文体和文本。汉语现代诗歌的缺乏成就在于过多追求文体革新,不触及内心和灵魂。
正如张万新所说,“诗歌本来就是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前沿,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运动,我以为可能是现代汉语出现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性写作。在眼下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诗人们对汉语的想象可以说发挥到了极限,对汉语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也几乎到了极限。二十年来的诗歌写作所积累起来的语言经验,对未来的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大约不能充分估计。”
朝向未来向度的写作是一种无能的借口。只为历史档案和辞典、诗歌选集的诗歌写作是谬误。极端信奉记录的意义是自恋。
李湟水:诗歌,有时候应该触摸的是心灵最为伤痛的地方。雨虹所说“无知”“无情”的对面,是不是说,诗歌是审美情感之上语言艺术的极致!不是专门的挖空心事的写作就能达到艺术的创造。
当我翻完2004年12期《诗刊》的时候,突然发现“诗刊”两个字是那么瘦俏。从《诗刊》到《星星》,给我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的乡土诗是主流,也是大多数诗人们得心应手的视角和材料;从现代性的普遍表现来说,就是诗歌想象的贫乏和叙述的流行,意象单薄,情感干涩,也就谈不上出色的意境、象征或隐语等等诗人个人化的想象、创造和感悟。
焦雨虹:诗歌写作应该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写作,而不是私人写作。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特性,强调不可替代;私人化通常的含义是隐私的个人,也就是人人有而且彼此都心知肚明,没有必要公开说明的生活动作。个人化探索无限可能,真正的多元。而私人化却可能导致粗鄙化、表面化。
诗歌应该尊重语言的精神。存疑,而不是追问、消解,是汉语的优良传统精神。存疑使语言获得一种包容、再生和诗意的能力;追问将一直回到生命的源头和宇宙的尽头,那里即使产生过抒情和理性,也是上帝的事情,与生命无关,更与知识、思考和诗歌无关。
现代汉语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特点和内核。即使经历所谓的巨大断裂,整个语言体系的所指系统几乎全部转换了内核,能指系统所构成的语境要素却保存下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构造模式和功能。传统作为“前身”的他者,其语境、话语系统和文本势力,是当代诗歌的参照系统。
诗歌应该主动发掘获得语词赋予的生命,并且挖掘语词生命更新的潜能。语词的生命在于包容和再生,很显然,当代汉语诗歌在语词的创造方面的活力不足。
李湟水:就文学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散文繁盛的时代,是一个小说泛滥的时代,是一个戏曲衰微的时代,也是一个诗歌缺失的年代。这里的缺失不是说缺少诗人和诗歌的创作,而是我们许多人的生活里缺少诗意和心灵的自我审视,也是我们的整个精神文化生活注重浮泛的物质,而忽略了人性的真正关怀。
焦雨虹:诗人们的野心就是赋予个人生活的言说以经典的意义。这是所有写诗歌的人不能抑制的欲望。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分歧与争夺,只是焦虑。与其在纷争、讨伐中建立功业,不如在自我和心灵的田野上耕耘,引领当代诗歌建设关怀我们情感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
王贝贝:那么我也来乐观地畅想一下吧,当代诗歌的出路在于:在喧嚣中沉静、反省,然后回到诗歌的本原,寻找新的突破口,能否取今复古、在新的范式和审美创造中突围而出,将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李湟水:就此作为结束语吧!
2005年1月3日复旦文学咖啡座(博士论坛之六)
李生滨主持并校阅编辑
具体发表于《朔方》2005年第4期
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和自由写作
在对20世纪末尤其是90年代文学诸多众声喧哗的批评中,我想从更为宽泛的视阈里就世纪末中国小说做一些正面的梳理和回顾阅读。虽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媒体和大众文化对文学的侵蚀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我们也应在历史的批评中从积极的方面作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