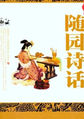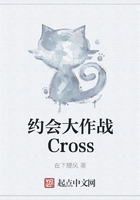白驹一瞬,岁月苍茫,了然会心的还是张元济先生的一句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所以心情极度伤悲时,他乡望月,涂鸦释怀:乡关不入梦,长歌也无情;慈颜已远去,翰墨了平生。教书谋生,舌耕三尺讲台,读书写作已经成为生活。翻阅一些专家学者的著作文论时,非常认同陈平原先生的一段话:“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这样的情景虽不能完全遭遇并且体验,却心向往之。也正如京派批评家李健吾安慰自己所言:“一个人生命有限,与其耗费于无谓的营营,不如用来多读几部作品”。个人崇尚文学阅读的审美批评与性情之说,不求雕龙画凤之富丽堂皇,只想在人生的匆促中读点书,打磨自己的文字与思想,成书一册,取名《雕虫问学集》。古人有论学集,诗书不精的我,只能以问学集奉答读者和师友。
求学读书最难以忘怀的是古城西安,特别是读硕士那三年紧张的生活,与几个师妹和三位导师朝夕相处。这样相处的时间,改变的不仅是我的读书生活,而且从个人的性情来说都有不少反省和变化。这些熟悉的名字应该在这里记下来,她们是马为华、牛鸿英、黎荔、王宾,还有杨柳、宓瑞新、崔蕴华等,要么是她们的才华横溢,要么是她们的宽容,使我收敛了粗野莽撞,多少涵养了心性,有了生活和读书的某种平静。最让人铭记于心的三位导师,从不同方面影响并给予了我帮助。阎庆生老师为我的上学前前后后操心,他的人格精神是我钦佩和景仰的。李继凯老师不仅关心我的毕业分配和工作,而且在具体的科研教学方面及时地点拨帮助我,督促我抓紧时间考博继续攻读学位,而他自己的勤奋和不断追求前沿,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傅正乾老师那么严厉地督导我的功课,一字一句地批改我的作业,让我学会了写作一般学术论文的规范和要求。因为本科的学习和硕士研究生的读书,西安南郊的那所古树与灰楼掩映、玉兰花和红叶李盛开的校园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正是陕西和西安的那种文化氛围进一步影响了我读书的爱好与追求。
我像麦田的守望者一样守望着读书的生活。博士论文要写后记的时候,夜深人静,却顾所来径,发现大多数的时光是“在读书的生活里守望岁月”。俗语说,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但我好像天生懒散,无法真正精明练达起来。所以过往的人事,在我,都是平凡的,唯有读书和文字的结缘,星星点点,却都是那么美好。
到复旦读书,应该是我人生最愉快的事,所以要感谢复旦大学和导师朱文华先生给了我这样的读书机会。生命之所以没有沉沦,是因为母亲的叮咛和念叨,生命因为读书而有一些长进和乐趣,却要感谢老师。复旦,以她宽松而又严谨的学术传统、校园文化,影响着我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子。上过课、看过书、聆听过学术讲座的学者师长很多,从图书馆、资料室,到办公室,内心钦佩和感激的老师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将他(她)们藏在心里,成为滋养我生命优美的永远记忆吧。因为在复旦的读书,我会自豪,因为在复旦的读书,我会更加惕厉谦冲。
后记写到这儿,突然想起,有两篇应该收进来的文章,却割爱了。其一是发表在《名作欣赏》2004年第7期的《叙述带给我们的亲切精致和心灵伤痛》,“碰到一个契合心境”的作家作品,竟然三次成稿!但从学术文章的规范和不重复自己着想,选择了谈毕飞宇《玉米》的另外两篇。其二是写王国维清明理性绝望的论文,这是我最早潜心写的东西。我想有一天我可能还要回去再次阅读王国维。少年多磨难,父亲的不顾生活,只有母亲在刚强的劳作中供养我上学读书。欢乐而又孤寂的日子里,千方百计搜寻到的几本旧书开始陪伴我。王国维先生关于美术与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问题同样搅动着我的心。哲学的东西让我蒙眬地思考人生和社会,美术的东西却鼓励我的内心,让人憧憬未来。在这样卑微生活向上的努力中,两个人激励了我。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一篇报告文学的女主人公。《一个平凡的灵魂能走多远》,这篇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报告文学,写一个北京街道办工厂糊火柴盒的女工,自学考上大学,特别是以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精神,竟然通过严格的留学选拔,令人钦佩!然而在美国开始学习不久,却染上了绝症,但她仍然乐观地完成了学业,在硕士学位授予的典礼上,所有的人都向这个平凡的中国女子致以敬意。郭沫若,我不一定非要去诟病他歌功媚上的“新华颂、百花诗”,当我从中学语文课本上学到《科学的春天》时,我知道这是与王国维性情完全不同的人。后来我选择郭沫若的研究作硕士论文的原因,一方面我的导师傅正乾先生是郭沫若研究的专家,也因此成为新时期陕西师大第一批搬进专家楼的教授之一;另一方面我始终对郭沫若怀有敬意,虽然90年代郭沫若研究好像开始冷落下来,我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郭沫若。出夔门,游学东邻,在五四风气初开的时候,能写下《凤凰涅槃》这样恢宏长诗的郭沫若,肯定有超常的才情;医学专科毕业追求文艺,比鲁迅弃医从文的境况,更加难能可贵;当血雨腥风来临、诸多文人知识分子彷徨动摇的时候,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的长篇檄文,可以说豪气干云;十年留学,又十年流亡,1937年抗战爆发,五十岁(已经是中国人称老守成的年龄)却又抛子别妻回国参加抗战,不论怎样的原因背景,那人生张扬的激情和勇气让我折服。
人生进取,应该多一份坚定,应该多一份烟火气。当然,读书做学问,更需要严正宏深的沉潜,所以博士学位论文我选择了鲁迅,所以结合自己的读书我开设了“京派文学”选修课。二十多万字鲁迅研究的初稿,已经让我在问学的路上知难而进了。为了走得远一些,我又师从河南大学关爱和先生、申请进站作博士后,准备雕琢打磨自己已经开始的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研究。
匆匆走过四十个春秋,而这不多不少的岁月和岁月守望,大半的时间是在寻求读书的机会。生活的压力从来没有减轻过,而能在推着清贫面对生活的奔波与忙碌之余,拥有一份读书的奢侈,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母亲范增梅和妻子李红霞,是她们用女性的坚强和勤俭支撑着我和家庭走过那些生活的风风雨雨。当然,还有那风风雨雨之中援助和支持过我的朋友亲戚,今生永远难忘。
回首过往,欣喜成书的时候,首先追怀遥谢的是湟水故里的同学师友,特别是平安教育上的领导和同事,他们的无私支持和包容,使我走向远方;其次感谢并祝福因为求学、问学和投稿而结缘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包括题写书名的朋友李松林先生,一起共事和新近结识的崔宝国、孟悦朴、赵明、郎伟、王岩森、郭文斌、闻玉霞、贺秀红等性情美好的人,还有佐红、攀峰、杨丽、马宏富、吴松鹤等喜欢读书的众多小友;最后,特别感谢宁夏大学党委宣传部、宁夏大学学报、校报,尤其是人事处、科技处和计财处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大地无言,花月有情。其实,自己的平庸,谈不上读书做学问,更何论做人,只是喜欢校园的热闹和平静,喜欢读书而教书的生活而已。当然,今后一定还要不断努力,对帮助和期望我的师长以及朋友们有个交代,也以此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慰女儿妻子清贫生活中快乐的守望。
湟水李生滨
2006年12月3日草于贺兰山清风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