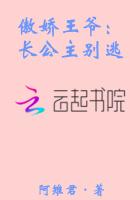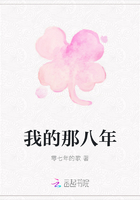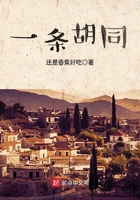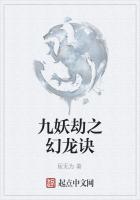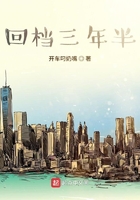展现生命诗意和大地浪漫的文学
——张炜小说创作述评
张炜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富有创造力和勤勤恳恳的作家之一。张炜在心灵的莽野跋涉,在生活的现实大地上耕耘,在抒情的优美里表现愤怒与反抗、沉思与超越,这是张炜给喧嚣的文坛提供的源于生命的热情和浪漫。想对张炜二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做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回顾。一方面厌烦了过于学术化的操作,另一方面想到文学杂志的阅读情趣,还是随意而谈好一些。也许能谈出一点自己的文学感受。
从20世纪80年代我个人一直在阅读的小说家有三个,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张炜,还有老作家汪曾祺,后来多了余华、莫言和几个女性作家。这样的阅读是比较狭窄的,但也算是一种选择吧。
贾平凹的小说大多是一种贴近生活的热闹且富有清新的气息,人物描写细腻传神,而且还有点内在的煽情味道。莫言是个渲染故事的能手,像《红高粱》的红,《檀香刑》的黑,作品大块泼洒的色彩感很强,又有强烈的音乐似的内在律动。而余华则是一个聪明狡黠的小说家,早期人性恶的肆意描写和后来长篇小说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同样浸入人的的命运,以及活着的本质意味。汪曾祺的清明如画,几个女性作家铁凝、王安忆、方方和林白她们的温情、聪慧和语言叙述的灵秀就不一一赘言了。而这一切之中张炜的作品意义最明确,个人化的追求也是一目了然,那就是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和努力,以及为此而堆积、而抒情、而营造的小说的浪漫情调。而这一切作者又要建立在生活的大地和生命的热情之上,所以不得不在道德和生命双重规制之中反复突围。这使张炜的写作永远处在一种小说想象和人性理念相抵触的十字路口上,张望左右而紧张。这种紧张就是,既要保持生活的东西又要去拥抱大地、发掘诗意的东西,二者在现实与想象的冲突中成为张炜作品的两极。这种两极的疏离或者悖反也就是张炜作品丰厚的意蕴和诗意生长的地方,是他作品存在的意义的大海滩。
一、纯真的田园牧歌(1984年前的创作回顾)
张炜的创作从描写胶东西北部小平原那条叫芦青河(原名叫永汶河)两岸的人物风情开始。作者在生活的种种波折和矛盾中写出芦青河两岸的人们的希望、理想和他(她)们的歌哭,还有他(她)们的善良和美好。“女的,没有一个不是伶俐秀气;男的,没有一个不是英俊端庄!”
研究张炜早期创作有三个集子是重要的,第一个是宋遂良作长序的《芦青河告诉我》,1984年11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个是明天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的《他的琴》;另外一部也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的《芦青河纪事》(名家处女作系列),是1997年7月版。因为《他的琴》是在张炜成名后,从他早期的创作主要是废稿里精选的一些优秀作品,“是一种悲哀意味的追念”。而《芦青河纪事》是在原作基础上“尽可能克制地做了一些更动”。《芦青河告诉我》收1980年至1983年创作的19篇小说,全是写芦青河的,而作为早期创作定稿本的《芦青河纪事》收了22篇,加了作者最早的写于1973年6月的短篇《木头车》,还有1979年10月创作的《初春的海》,这两篇又都是收在《他的琴》里的早期存稿,另一篇是发在《松辽文学》1984年4期的《泥土的声音》。《芦青河纪事》所收22篇从内容上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前面的9篇,以《声音》为代表,在乡村生活中捕捉少年男女蒙眬而又纯真的那份羞涩情愫。第二组13篇主要是对生活的思考和委婉批评,对老人的保守、某些青年的不良行为与做法以及社会的一些阴暗等等。其中《达达媳妇》写得最有生活情味,而且几个人物的描写也形象新颖,但真正写出了生活新意和情趣的,还是故事情节有点接近《小二黑结婚》的《黄烟地》。
接下来我们得谈一谈《一潭清水》和丰盈的秋天意象。有人说过,文学是孤独者的事业。那么张炜,孤独的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奔跑遐想,泥土的温情触动他的心,他的笔,使他的写作蒙上一层大地的湿润和对万物的悲悯。当然,这是压抑心底的忧伤里洋溢的诗情在涵养他的笔墨,他写得越来越好。野地里的情怀——有一种生命的冲动,以及对人的心灵净化、滋生美好情感的天然和纯真。如果说《声音》的诗意是湿润的林间晨曦在朝阳的明媚里有着粉红色的眩晕,《一潭清水》却是秋月洗过的乡野大地的澄静。两个老人生活的枯涩是包容在大地的生命和各自的劳作沉默里,那个叫小林法的男孩是生命和大自然纯真的精灵,秋天的乡野因此而更有希望和温情,但人性的隐约伤害却是那么不经意间出现。张炜的少年时代是有过内心忧伤的,但这忧伤却在大地的绿色和生命聆听的热情中滋生了美好,使他不至于走向心灵的黑暗,使他永远有一种生命的浪漫。文学不仅讲述了我们的生活,还讲述了我们的内心。
真正奠定张炜作为作家独特品格的,是收在《浪漫的秋夜》、《秋天的愤怒》、《秋夜》等中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从秋天的“浪漫”到秋天的“愤怒”,作者已经从表现“美的自然,美的心灵,感情真挚”且富有个性的抒情和意境,进而有了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与揭示。就像《你好!本林同志》,生活无法调侃的苦笑尴尬里是压抑不住的沉重和灰暗,不像有些作家在抒情或写实的描写里给生活涂上一层虚假的亮丽面纱。张炜的浪漫来自他对生活的执著和热爱,他的眼里容忍不了那些丑恶的行为和世故的做法,所以,一直被称为浪漫作家的张炜恰恰不能像另一些写实的作家那样粉饰太平——像《草楼铺之歌》里轻微嘲讽的“郭老师”那样习惯于寻找“主题”。对张炜的早期作品的批评,最为充分地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社会拨乱反正的时代里,依据历史惯性而来的、无法摆脱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和制约。张炜多少有点自己的坚守,不是急功近利地追寻文坛和社会主流的热闹,他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乡野的生命里发掘自己的文学感悟和思考。《浪漫的秋夜》,我觉得是张炜最初表现的“萌动的青春情怀”的一次欢呼与告别的庆典。时光荏苒,他作品里的女孩子在长大,生活也越来越多地展开了它的严峻和真实。所以《秋天的思索》里的老得也就成为作者自己喜欢的一个单纯而执拗的人物,而且不止一次在他的作品里出现。李芒和老得两个人物,是作者对这种生活进一步理解和思考的见证。特别是老黑刀、王三江、罗焕成和肖万昌,这样一连串人物的不断丰富,一方面说明了张炜对生活的真实观照,另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引来一些正面描写生活和正面叫好的“批评家”的不理解和指责。
所以我们很难用我们习惯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来界定言说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本意义,当我们回头阅读张炜早期的小说创作时,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作者贴近生活的作品氛围和创作意识。恰恰在这些作品中,对大自然的细致描写里灌注了作者浪漫纯真的极大热情。不仅兼具赵树理小说的质朴和孙犁作品的清秀,还有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受。“那些作品更多地抒发了一个人对大自然眷恋的情怀,写了大自然怎样安慰和哺育一个人的童年。那时一个人的不幸和哀伤,比起大自然对他的恩赐,立刻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他整个儿来说是欢畅自由的、无所拘束的,所以他总是幸福的。这种总体情绪贯穿在我的那几本书中。”
张炜早期作品的优美和抒情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想指出来的是作品蕴含的作家更深的那份忧伤。他对生活的纯真是那么渴望和热爱,但生活却有着它难以消除的忧伤和苦难,甚至一些污浊的东西。苦难和忧伤不仅在作家的作品底蕴里静悄悄地流淌,忧伤还在农民的心里,苦难灌注在父老乡亲的命运里。张炜装不下这许多的忧伤和苦难,所以他用少女的美丽和清纯来淡化心里的忧伤,他用歌咏大自然乡野的生命来抚慰苦难中的人们,他要用一再的流浪和回归田园来坚守他心中那份对生命和父老乡亲的同情,还有自己的善良、温柔和羞涩。
二、“男人的歌唱”——1986年《古船》创作的前后
张炜早期的创作清新质朴,生活感受很强,作家的个性也已彰显,对大自然的尽情描写,对女性的美好和善良的诗意绘写,还有那些性情纯真的儿童与老人形象的丰富塑造,特别是他们在海滩、在田野、在劳作里的天然性情,他们纯真而活跃的生命的情趣。这一切在《古船》的写作中有了一次历史的回溯和沉思。其实在创作《古船》的这一时期,张炜有好多短篇小说精致而有意味。
“他先写出了过度性作品《一潭清水》,随后写出了标志性作品《秋天的愤怒》。往后几年,他相继写出了《秋天的愤怒》、《古船》、《梦中苦辩》、《远行之嘱》,这些都是他最有力度的作品。凭着这些作品,张炜成了当今文坛上一个重要的存在,一个在讨论文坛格局时不可遗漏的作家。”《古船》的创作就张炜的创作来说是一个提升,也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二者重合的意义上对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提升。张炜的《古船》是从乡土的意义上对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反思,心事浩茫连广宇,作者对现实生活在思考,更是在近现代历史的视野里寻思琢磨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的人们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根脉和缘由。历史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演进的漫漫长河,而中国这条“古船”穿越几千年历史的风雨驶向现代、驶向20世纪的时候,诸多的因素加重了外辱内乱的激荡和危难,这样的历史沉重感和文化的破败感,好像已经渗透到不少人的感觉和意识中。这种文学的比喻和想象在《老残游记》中已经有过充分的发挥。在张炜这儿就变得更为具体和可触摸的文学寓言,虽然这种创作思路萌发的契机源于省城博物馆的那艘“古船”,但真正的热情和艺术想象来自他的生活感受和内心思考。说到这种生活的感受和思考,我不得不提到《烟斗》这篇短篇小说,这应该是在冬天写的,它的氛围就是冬日阳光下清冷又温暖的感受。就是这篇作品说明了张炜已经懂得了生活和生活里那些无声的东西。一年多以后张炜写出《古船》,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一些批评者的拔高和作者的某种解释,都不能排除《古船》产生在那样一个时代所受的整体氛围的影响。它能够超越当时《芙蓉镇》等优秀作品的地方,在于它的视野更开阔,对历史的审视更多地摆脱了当时还未消除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社会批判的庸俗价值观,对历史和生活的钻探更深一些,所以对人的生存和历史原态的民间生活有了更为客观和冷静的叙述与揭示。这种超前的敏感在后来《白鹿原》为代表的反复叙述历史和家族的世纪末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里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三、秋天的情怀——“融入野地”和《我的田园》的故事
张炜在秋天的景色里讲述了许多不无生活色彩的田园牧歌式的故事,就连《古船》凝重的史诗性营造里都无法抹去这种生活情调。在随后的作品里这种情怀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东西,越来越充分地成为张炜不同层面上的文学表达和诗意灵魂。《融入夜地》,是张炜1992年写的一篇长散文,《九月寓言》出单行本的时候用它来代后记。这可能是张炜自我言说最能传达出个人心情和写作追求的文字,所以广受重视和关注,以此为名的散文集《融入野地》,成为小说《古船》和《九月寓言》之外,张炜作品中流传和影响最广的文本。所以,说它是张炜对以往文学创作的自我总结,特别是《九月寓言》创作的经验和感悟之谈,一点也不偏激。如果说《九月寓言》之前,张炜的语言是外在的描写和叙述,那么《九月寓言》的文本叙述已经转化为一种内省的语言。融入野地,是张炜一直有的大地情怀,特别是秋天的野地,秋天的树林、海滩和葡萄园。这也是张炜生活热情和少年情怀的大地记忆,是他创作的本色和底色。融入野地,是张炜自我守护和磨砺的言语方式和行为,在偏远处认真于“传播文学”的热情,是他生命浪漫的外在表现,《我的田园》是他少年记忆和旅居生活的文学整合,是想象的真实故事。这就是文学和文学的浪漫。融入野地,是文学的想象和心灵的审视,张炜是“一直在不停地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力的人”,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莽野”,“文学是自己的事业,民族的事业,个人生存和自救的事业。如果说它有力量,那也是通过对心灵的慰藉产生的”。张炜是在为人们诗意栖居的大地在争取尊严和权力。张炜在内心的自省中,对大地和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超脱的诗意表现,不再是早期的纯真,而是为大地上一切生命和人的生存争取尊严的内心审视和文学坚守。
这是孕育《九月寓言》活跃而又澄静的时期。
这也是张炜逃离省城旅居胶东半岛的生活时期,至今还没有人注意过张炜另一面的数量更多的抒情文字,这也是一个抒情滥觞的漫溢时期。“我于一九八七年底来到登州海角”,“在至今为止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我们在一起交谈、切磋、幻想,度过了数不清的美好时光”。“就这样,日积月累,有了这二十几万字。”这是作者在散文随笔《葡萄园畅谈录·后记》里的说明文字。其实这一时期最早完成的草稿是《我的田园》,1990年春天开始写出草稿,1991年《峨眉》一、二期分别登出上下卷后,作者还一直在修改。可见作者对它的钟爱很深,后来还整理出它的姐妹长篇《怀念与追记》。秋天和葡萄园是孕育张炜灵感和激情的温床,张炜无法忘记那一段时光和情怀,不仅在1996年作家出版社给张炜出六卷本自选集时,他将长篇《怀念与追记》、《我的田园》和长篇随笔《葡萄园畅谈录》选进文集,而且2002年还出版了《我的田园》这个长篇的改写本(漓江出版社)。
四、1992年《九月寓言》——创作的一次澄静和升华
张炜说:“我的希求简明而又模糊:寻找野地。”我说,对于张炜越来越丰盈的秋天意象好像已经说得很充分了。《九月寓言》的产生出人意料也是理所当然了。这是一个长期的孕育也是一个秋天偶然的发现和惊喜。真的,像大地上一切生命的成熟一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