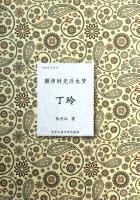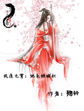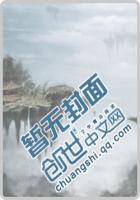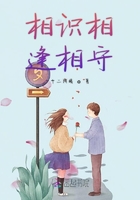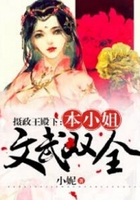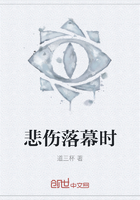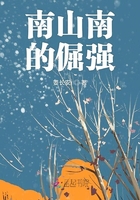这种淡然如实的记述风格也同样体现在《竹荫读画》《下乡去》等篇章中。先看《下乡去》的长文记述:下乡时简陋卡车上的幽默与欢笑;林园拜访清苦中译著的李侠公;白果树下回想往日的热闹和童稚;抗战艰难的生活中难得的门阶聊天;同仁离合悲欢中的聚餐;夜来风雨和车上的司机;水牛山公园的变化和路上的采购。行文中充满欢乐的情绪,虽然每个人都忍受着长期战乱带来的艰难和窘困,但大家信心坚定,简朴的生活里洋溢着很高的生活热情。全文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掩不住荡漾的乐观精神,一种团结抗战的坚定和力量就在简洁质朴的语言中流露出来,整个行文像奔流的河水,心情像夏日阳光下的绿叶,欢快的语言是非常生动自然的。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作者始终微笑的面容,正如老舍所说:“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种随时的,真诚而并不正颜厉色的,对朋友们的规劝。这规劝,像春晓的微风似的,使人不知不觉的感到温暖……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作者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抗战生活的一页,其自我的性情也在字里行间闪现。这些文章不仅语言自然简洁,描写亲切平易,现实生活的内容更是广泛,具有早期散文所少见的开阔视野和生活的丰富多彩,使文章在简朴的叙述中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性。生活是平常而又厚朴的,只有作家深挚淳厚的心地与感悟,才会享受其美、其善、其真。有人说诗歌如酒,散文如水。那么没有明净的心湖,盛不了纯净的清水,没有久经磨洗的亮眼,寻不到幽静美丽的湖光山色。水是平常的,生命因水而常绿;生活是平凡的,但人生因艺术而变得更美好。散文之水啊,只有明净如秋,才会亮丽而淳厚。水在眼中只是伤感的泪,水在心湖,才会涵养世界的灵秀;水只有滋润了生命,才会有光华;水洒向大地,才会有勃勃生机。郭沫若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因反映生活的真实和内容的广泛,更具有了大地般的质朴和深厚。郭沫若的内心忘却了自我、容纳了大众和祖国时,思想变得开阔,行文更加清明流畅,滤干个人嘈杂的情感自恋,才有如秋山般的清爽。敞开了心扉,山野的大气才会滋养无私的胸襟。作为最自由的散文创作,在郭沫若的笔下是随意而质实,自然而简朴,没有文饰的矫情,没有故作的高深。从生活中来,如山野的绿叶清风;从生命的感悟中来,在心泉上轻轻歌唱。你听,《丁东》在心灵的深处叮叮淙淙,让人有回味不尽的思念和隽永。你看,《白鹭》从心尖飞上云端,在空中飞出一个美丽的音符,让人感受着清新和优美。《下乡去》是奔向远方的河,《飞雪崖》是清浅的田间溪流,《水石》所感悟的细微,《石池》所赞美的绿洲,还有《母爱》中无言的焦尸,已滤尽了《小品六章》里的伤感和浪漫。作者的深挚的情感有了水一般的清明和深永,不着一字议论,尽得生动意蕴和强烈的思想感染力。《雨》的闲话,《小皮夹》的故事,作者信手拈来,写得诚挚感人,旨趣深藏,读来平易隽永。散文的题材源于生活本身,作者的智慧和天才在于把生活中琐碎、平凡的事和物发掘开拓,写出让人回味的东西,加深人们的认识,使之接近实质和真理。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看似信手随意,但皆缘情因事而自由抒写,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所以朴实自然中有雅致,平易亲切中有大义——妙手出玄机,文章自天成。胸臆直露,不显激励,人性真淳,不为文饰。至性至文,生命的清纯是一种自然的流淌。不仅体现了语言的明净如水,更主要的是心胸开阔的深挚情感表现得冲淡而含蓄。可以说这是最深沉的爱国情怀、时代精神和美好心灵的结合。
因此,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内容广泛深入,语言质朴简洁,读起来有一种成熟的气息,一种了无杂尘的明净。这不仅是文章的内容和语言文字所造成,最关键的是内在情感的深沉和人生境界的高远所孕育。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从思想内容上早已脱去了昔蜀那种感时伤怀的哀愁,不是停留在社会人生的感慨、自我境遇的抒发上,而是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乐观向前的精神,个人的品格在峥嵘的岁月里展现了另一种清明和爽朗。在大时代的纷扰和艰难中有了难得的在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中静观沉静的审美心态和悠闲心境。
第二,审美意象的变化和境界的开阔。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相对于20年代郭沫若散文情绪化抒写,以及优美亲切的特点,40年代郭沫若的散文更加冲淡、含蓄、深沉。这表现在面对相同的审美对象,有不同的审美意象和情感蕴藉。内容的现实意义和所表现的人生境界、艺术境界是开阔的、深沉的。生活情感的变化引起作家审美情绪的变化,苦闷和乐观就有不同的意象的审美对象化。
比较郭沫若前后两个时期的文艺性散文,审美意象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小品文——《路畔的蔷薇》和《芍药及其他》。同样是“被遗弃(抛弃)的鲜花”,前者是“供养在断颈的破土瓶中”;后者是“插在小巧的白瓷瓶里”。这情绪化的“伤感和欣喜”是再明显不过的。同样是自然花草充满生机的赞美,茅茨、山茶花从山中采来,清秋活在黑色的壁上的铁壶里,这是田园牧歌的诗人情怀,虽然诗人在生活上碰壁以后,在自然的清新的花草描写里显出了热情和希望,但终究没有脱离开个人的生活点缀的审美范围;“青青的野草”却在石池的弹坑里长成绿洲,这是抗战最艰难的大背景下的对象化感兴,是对生命顽强的感动,是对无数敢于面对艰难、面对现实的生命的默默致敬!这二者所含蓄的审美情感表现了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境界。同样是面对“尸骸”,在《墓》中是哭自己的灵魂,在《母爱》中抒发的却是对侵略者残暴行径的审判、愤怒和对被残害者的悲痛,其现实的意义和情感的意象蕴含是大不一样的。
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生命。散文是作者对于实际生活中所接触的事物、事件、人物以及对环境、自然景色所引起的感情与思想的记录。郭沫若文艺性散文最突出的就是情感的真实。人生境界的变化和时代对人生的影响,带来郭沫若散文整体风格的不同,特别是文章所表现出的气势和思想说明了作者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不断变化和开阔。《菩提树下》和《竹荫读画》记叙的都是一种树阴下闲静的生活情景图,一个是树下饲鸡,一个是竹荫读画,都以亲切真挚见长。《竹荫读画》一文里表现的是朋友相聚的畅谈,深情厚意,亲切放达;《菩提树下》表现的是家居生活的场景,欢欣喜悦,温馨优美。《竹荫读画》里不仅写了读画的情趣和友情的融融,还伸展开去,谈笑间写出了画家对艺术的执著及其永不消磨的生活热情,突出了傅抱石贫贱不移的素朴精神、抗战的民族精神,民族大义洋溢在平实的文字记述里,意境是十分开阔而深挚的,为文为人的境界不言而喻,表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胸怀。《菩提树下》只是表现一种日常生活的平静心态和妻子为儿女家庭操劳的喜悦,浸染的是作者闲适的田园情怀,一种亲情的感动弥漫开来,意境亲切,情感优美,描写是很生动活鲜的,但其审美境界的开阔与深远是无法与《竹荫读画》相比的。《竹荫读画》看似信笔随意,却深藏着大义,无形中现出了大境界;《菩提树下》文笔清新自然,着意描绘个人情绪,意境优美,但内容稍显单薄。
从另一角度,我们来看看同样富于情感色彩、以抒情性见长的《卖书》和《丁东》。《卖书》把人格化的“书缘友情”极尽悲郁的情致表达得缠绵悱恻,是郭沫若早期一篇至情至性之文;《丁东》也是反复咏叹对少年友情的怀念思恋。《卖书》是作者难以割舍的心灵追求的美好象征,《丁东》是心头缥缈的对珍贵友谊永久的思慕。“书”是我真正的朋友,生活让我不得不忍痛放弃;“丁东”是我少年之挚友,天却早亡我友,二者都让我思慕怀想。《卖书》写实:我思念旧友——回忆放弃文学爱好的经历——分别时所受书贾的侮慢——寄付了二位老友后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不忍回首的往事、人事,还有那居住过的“小屋”——我的神魂借着你们(《庾子山全集》《陶渊明全集》)永在。《丁东草》虚写:思慕丁东——清洌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的那种丁东——清永的凉味——嘉定一眼水井——丁东声里的少年挚友——记忆的咏叹——回嘉定的实感——心里倾听丁东清永的凉味——我永远思慕着丁东。经历的详细实录和诗意渲染的隽永,创造的是一种相似的境界,营构的是同样的氛围,情感的轨迹也是有些相似的。《卖书》中激愤的情感一泻而下,越写越峻急,心灵悲愤的忧伤灌注在每一行文字里,情真意切,深挚感人,读该文时读者被流贯的情感所打动,引起深深的同情和共鸣,但一种阅读的感动过后,没有深永的东西。这是一种实事诉说,是一种情感倾诉。是优点,又是缺点,文以情采显,意以浓情累。而《丁东》好像发酵的陈酿,清幽的思念和情绪在聚集、在疏散、在弥漫,在似真如梦的诉说中反复,氤氲成一片迷蒙的忧伤和思念。空中之音,云外之信,久在心头回响,欲罢不能,梦寐俱是,不可释然,已经在若干隐曲之处显出深切和丰富,这是浓郁而又淡远的意境营造,是把情绪化成了隽永的音乐。余音绕梁,使人在沉静中慢慢地回味,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和文字表现的造诣。同样是友情的描写,往事的回忆,但意境有高下之别:《卖书》虽也真情感人,但原态的情感没有艺术审美的过滤,情太盛太烈,妨害了文章的意趣和境界;《丁东》却是情隽永而文简洁,生活形象和情感意蕴达到有机统一,从而获得了一种深永美的境界。
散文有较强的主体性。写“自己”可以说是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总是在感受社会生活时,敏锐而精微地把握“自己”。善于捕捉“自己”的经历、趣味以及情绪中的纯然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散文作家成熟的标志。举凡真正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表现作家本人的胸怀。画家傅抱石在艰难里顽强拼搏的艺术精神,就是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人格精神。他们的身上表现了生活最善良的优秀品质,他们的人生和艺术追求里是最赤诚的生命之真。避难流亡的生活没有消磨画家的艺术热情。这样一种精神也是郭沫若在《银杏》里所讴歌的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也是抗战中“一瓣心香敬国华”的郭沫若自己的写照。如果说2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细致地写出了诗人独特的感受和情愫,怡然自得的田园情怀和浓郁的悲伤情调体现了一种亲切和优美,那么,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在亲切、优美、生动里更显出一种庄重和责任心,特别是始终扣合着历史的艰难而壮阔前进的自信。虽是小品文,却有一种鼓舞人的精神。作者的确在叙写个人的际遇经历、悲欢愁忭、爱憎喜忧,但也同时叙写着时代的痛苦和奋进、动荡和骤变,生活中的真善美透过作者的笔反射或折射出来。从这样一个较深入的层面上来讲,郭沫若后期的散文明显地比前期散文所反映的生活面深而且广。这是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使然,而深层的则是作家的创作艺术水平、审美能力及思想境界的提高和进步,更是作家人生阅历的开阔和自我不断完善的表现。这种变化和表现是一些伟大作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作家伟大人格在不同阶段的丰富性所致。
在舞台上铺陈历史风云,在现实的血雨腥风中战斗的郭沫若,其文艺性散文的笔触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土壤和心灵的深处,用娴熟的、朴实而优美的文笔表现了作者生活的各个侧面,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如果说朱自清散文文词清丽、情致优美;冰心的散文秀丽亲切、思想纯洁,那么郭沫若的散文朴实而流畅、简洁而富有诗情画意。虽然没有鲁迅的深刻犀利,周作人的至味冲淡,但另具坚贞和质朴,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真诚和通达。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是自我的发现,是真情实感的结晶,它们通过不拘一格的形式、自由的抒发和诗意的表达,作者把最真实的情感和心灵交给了读者。文章的散淡,文字的熟落,生活的情趣和审美的感受,是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从这样的探究可以看出,郭沫若40年代在沉静和思考中留下的文艺性散文,虽然数量不多,却表现了郭沫若在人生进取、社会斗争中较为平静沉思的一面。郭沫若以诚恳、炽热的心灵感受生活,以亲切质朴的笔墨记录抗战时期自己的活动,时代的烟云,人事的际遇,思想情感的明暗晴晦,都体现在一种最真挚最质朴的文字叙述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从另一种意义说,也只有质朴的东西才能打动人。”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皆“坦坦白白地记事写人,发抒情怀”,很少哲理的说教和凭空的遐想。短章把瞬间感受的事物简洁地勾画出优美生动的意境和旨趣,长篇的则平易自然地记述日常生活的经历,在朴实的行文里透出诗意的活鲜和感人的蕴藉。
三、40年代文艺性散文创作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