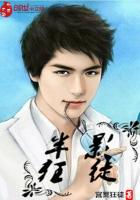以吻封缄。
二楼欧式雕栏的阳台上,夜色如同一朵暗色的蔷薇,妖娆地盛开在脚下。
望着那个在雨中缓慢前行的清丽影子,林斐扬靠着栏杆,拿起酒罐拼命地往喉咙里灌着。
“你又来找她了。”知了不知何时走到他的身边。
这些日子以来,林斐扬几乎每天都会来以吻封缄。并不会直接去找谭惜,每一次,他都是远远地、坐在不起眼的卡座里,像暗夜里影子般默默地注视着她,守护着她。
知了是何等世故的人,这一切的一切她当然都看在眼里。
可惜林斐扬却并没有将她看在眼里,他只是漠然地挑眉,接着又猛灌了一口酒:“这跟你无关。”
知了看不下去了,她一把抢下他手中的啤酒罐子:“你这样只会害了她。”
林斐扬冷笑了一声,眼神浓郁得仿佛浸在夜色里的酒:“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周彦召那样的男人耍弄?”
“你都知道了?”知了眼神复杂地看他一眼。
神情瞬间变得萧索,林斐扬想着那日谭惜决绝的话语,闭了闭眼睛,又打开了另一瓶啤酒,蓦地一口仰尽:“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整个海滨城里,有谁不知道?”
知了仰头看着他:“既然如此,你应该也知道了,她是周彦召的女人,又何苦继续纠缠她?”
林斐扬暗暗握拳:“周彦召要是真把她当做自己的女人,就不会把她拉上台面来!他根本就只是在利用她!”
“利用又怎么样?干我们这一行的,跟客人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利用的好,就能飞上枝头,财源滚滚,利用的不好,就身败名裂满盘皆输。谭惜是个聪明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一向做的很好。如果没有周彦召,又何来今日在以吻封缄风光无限的她?”
苍白的灯光照下来,映着知了秀丽的面孔,仿佛蒙上了一层苍然的风沙:“可她唯一的威胁,就是你。想要往上爬,想要在这个夜场里生存下去,就不能动真感情。你的存在,只会让她束手束脚。”
蓦地一下将啤酒罐捏扁,林斐扬回头,目光暗烈地逼视着她:“你千方百计地劝我离开谭惜,到底是什么目的?”
知了无畏地直视着他,目光平静而冷酷:“我不怕告诉你,我今年已经30岁了,在这个夜场里,我混了将近五年,背后整个家都是靠我一个人撑起来的。我见过各式各样的人,经过各种各样的事,知道什么人对谭惜有好处,什么人对谭惜没好处。”
“这个游戏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知了顿了顿,神情肃穆地说,“林斐扬,你们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要是真想她平安,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你把她当游戏?”林斐扬却突然笑出声来,他指着她,黑沉的目光里尽是讽刺,“你这三十年,活得真是了无意义!”
话不投机,他拿起剩下的酒转身就要走,猝不及防的,他的目光却似是钉住了。
烟雨下的小巷里,一辆黑色的轿车挤过人流,悄无声息地开道清丽的影子身边,然后像是飓风般,将她轰然吸了进去。
“谭惜!”
血色倏然间从林斐扬的唇上褪去。
几乎是想也不想的,他一手撑起自己的身子,从阳台上一跃而下,狂奔向那辆黑色轿车!
双腿被震得发麻,头顶是知了的惊呼,但他已顾不得许多。
白茫茫的雨雾里,人流拥堵,轿车开得并不算快,但眼看,它就要挤到交通便利的大路上。
“怎么你很关心吗?你既然这么关心我,为什么半年前出事的时候,都不肯回来看看我?一定要等我被学校开除了、等我受尽冷眼来到这里,你才知道关心我吗?”
如同是黑白色的噩梦,又如同是寒光透刃的利剑。
这记忆腐蚀着他,穿刺着他。
半年前,他抛下了她。
半年后的今天,他绝不能再让她掉进那黑色的湍流!
林斐扬深吸一口气,随手从路边的行人那里抢了摩托车,直冲着追向它……
……
远处。
在谭惜拐进小吃巷之前,黑色的宾利缓缓降下了车窗。
“周先生,要过去看看吗?”望着独自走进阴暗处的谭惜,曾彤皱了皱眉。
“不必了。”
周彦召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别处,连语气都是淡漠的:“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曾彤于是也收回了目光,恭恭敬敬地回他:“这周末中午,十二点的飞机。”
“他一个人?”周彦召揉了揉额角。
“应该会带着文昊少爷,还有……”曾彤小心地觑着他的神色,低声说,“萧董。”
周彦召点了点,发现曾彤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于是又道:“想说什么就说吧。”
曾彤深吸一口气,似是作了一次短暂的思索,最终还是决定说:“三元巷的事情,董事长已经知道了,是文昊少爷说的。”
“还有呢?”周彦召低头,不动声色地看着汽车背椅上夹着的报纸。
曾彤也顺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他恐怕还说了你和谭小姐的事。听说在飞机上,董事长看到了那份载有你和谭小姐新闻的报纸,脸色不太好看。”
周彦召沉默不语,片刻后,又问她:“报纸的事情,查清楚是谁做的吗?”
曾彤一边回想一边说着:“昨天知道谭小姐上了您的车、跟您走的人,除了林斐扬之外,就只有公司的那几位高层,当然了,还有会所里的人。现在看来,可能是文昊少爷收买了公司的人,时刻盯着您。您放心,我会尽快查出那个人的。”
“嗯。”周彦召神色淡漠地点了点头。
“您……”曾彤张了张唇,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问道,“您不打算跟谭小姐解释一下吗?”
“走吧,去公司看看。”
车子重新发动的时候,周彦召微阖上眼,一股子寒,却莫名地钻进他的四肢,又渗入到他的心肺之中。
“你极少出入这种场所,是因为周伯伯对你严令禁止吧?如果让他知道你跟一个陪酒的好了,你猜他会怎么做?”
“周彦召,不要以为你姓周远夏就会是你的。你他妈就是一个婊子生的!”
“周先生,越灿烂的星光消逝得越快。越激烈的爱情,也一定结束得越快。我们之间,既然注定要结束,那就不要开始。寂寞的游戏,本身就是个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可笑,而且可怕。商人是天生的赢家,而一个陪酒女……她根本输不起。”
茫茫黑夜里,周彦召微抿起薄唇。
谭惜,你知不知道……
人生这场游戏,无论是谁,都一样输不起。
所以我不能输,只能赢!
……
同样的雨夜。
灯火在车窗外辗转流离,而谭惜的眼前却漆黑一片。
“放开我!”四肢都被尼龙绳绑得结结实实,谭惜在未知的恐慌中挣扎着,“谁派你们来的?你们想干什么?”
“那要问问你自己到底得罪了谁。”身侧的男人低哑地笑了,与此同时,车速变得更快。
手心冒出一涔涔的冷汗,谭惜紧紧攥住自己的手指,脑子则急速地转动着,她得罪了谁?她一没钱二没势,谁又会跟她过不去?
在几个剧烈的颠簸后,车子又在相对缓和的平地上行驶了一阵子,才缓缓停下来。
有人粗鲁地拽起谭惜的手臂,将她连推带搡地带下去。
谭惜看不到,只能跌跌撞撞地走着,周围的空气渐渐变得阴冷,她不由得瑟缩了一下。
接着有人按了把她的肩膀,她被迫坐在一张椅子上。身侧响起有序的脚步声,好像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空旷的房间又寂落下来,这让谭惜更加不安。
远处,还有雨水不断滴落的声音。
嘀嗒……嘀嗒……
紧凑得仿佛谭惜此刻的心跳,她努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面前突然刺啦一声锐响,像是有人搬了张椅子过来。
她不适地皱起眉头,下一刻,一只干燥温热的手已经抚上她的脸颊,接着是颈间,锁骨……
肌肤如同被毒虫爬过,谭惜微微战栗着,侧过脸:“谁?”
男人不说话,染着烟味的修长手指却蓦地向下,嗤地一声撕裂了她的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