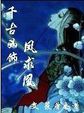这怎么可能?明明前几天我们才做在一起唠家常,商量着给两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我还特意去岐山上的龙隐寺给两个孩子一人求了一张平安符,可岚拿到手中时,笑得温暖如花,满心满眼都是殷殷地幸福和期盼。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
“她都已经怀孕8个月了,还是双胞胎,怎么可能会要不成!”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周晋诺背靠在走廊的圆柱子上,从兜里抽出一根烟点燃了,乳白色的烟雾更衬得他神情萧然:“今天早上检查后,医生说胎儿的脑部缺氧严重,如果非要生出来的话,很有可能是脑瘫。”
“脑瘫……”我心里猛地一刺,下意识地扶着身侧的墙壁,“怎么可能会是脑瘫?”
周晋诺闭闭眸子,漆黑的瞳孔里满是疲惫:“现在来不及说这些了,你快去劝劝可岚吧,劝她把孩子打掉。她现在情绪很激动,我真怕她会做出什么傻事。”
我咬紧下唇,忽然想起大约一年前,他也是这样神情颓然地对我说:“可岚在上面,你去劝劝她吧。”
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我能做的都只是劝,而不是阻止悲剧的发生?
勉强定了定心神,我伸手抹去眼角的泪珠,一步一步地向病房里走,还没进房间,就听见有女人嘶哑绝望的哭喊声:“我已经怀了他们8个月,整整8个月,早上的时候他们还在踢我呢,昨天晚上他们还在梦里找我,对我说,他们真的好爱我,你现在说这两个孩子不能要了,我不信,我一点也不信!我求求你,医生,我求求你,让我生下他们吧!”
仓促间,我推开了门,只见可岚正不依不饶地拉住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一张白皙的脸因激动而胀得通红。
医生则愁眉紧锁,一脸无奈地捏着一张单据,递也不是,不递也不是:“秦小姐,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是为你好,请你快点签字吧。”
“可岚,可岚。”几乎不能相信眼前这个女人就是昔日里柔婉娴静的可岚,我一连叫了她两遍。
“叶子姐——”
见到我来了,可岚的两眼满是希望的光芒,扑上来,她一把扯着我的袖子:“你来的正好,我知道你以前是学医的,你一定有办法救我的对不对?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帮我救救我的孩子。只要能生下他们,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啊,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他们的命,只要他们能好好的生下来,哪怕死,我也要把他们生下来。我已经怀了他们8个月,盼了他们8个月,我真的不能没有他们,我求求你了!”
“可岚……”我无比心痛地握住她瑟瑟颤抖的双肩,一双眸子深深地看进她的眼里,希望能给她安定的力量,“可岚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可岚却猛然推开我的手,因为动作太大,连系着的长发都散开来了,落在她白瓷般毫无血色的腮边。
而她的神情则像是在黑夜里熄灭了烛火,只能声嘶力竭地哭喊:“我不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们就要离开我了,叶轻,我求求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行不行?我求求你……”
不忍心看着她再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我一咬牙,扬起手重重掴在她的脸上,霎时间整个房间都悄静下来,空留下那一耳光的余响。
看着呆若木鸡的可岚,我痛心不已,一字一句大声地喝斥着:“你就算不要你这条命非要生下这两个孩子,他们也已经注定是不健全的了。你自己好好想想看,这样的两个孩子,除了你谁还有会要他们?周家会承认他们吗?你爸爸会承认他们吗?没有周家的帮助你自己一个人能养活起他们吗?你和我都是这辈子吃尽苦头的人,你愿意你的孩子和咱们一样一辈子遭人白眼、一辈子痛苦无依吗?”
她一怔,纤弱的身体已摇摇晃晃地瘫倒在地上。她捂着自己红辣辣的脸颊,什么也不说,只是定定地盯着自己依旧隆起的小腹。蓦然间,一滴清泪从她眼角滑落,她颓然地闭上了眼睛。
“秦小姐?请你快点签字吧,这件事拖得越久,对您的身体越不利。”医生又开始催促了。
我猛然抬起头,眼光如刀一道道狠狠地剜在那个医生的脸上:“你去告诉周晋诺,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得什么主意!他再敢逼可岚一次,我绝对不会——”
“叶子姐,”可岚却打断了我,缓缓仰起脸,她看着我,空洞的双眼里再没有一滴眼泪,“拿来吧,我签字。”
看到她这个消沉的样子,我的心好似被利刃剖开了般,痛得发紧,也再说不出什么话来。
周晋诺请来的主治大夫是这方面的专家,技术精湛,因此可岚的引产手术做得很顺利。被推出手术室的可岚躺在浅蓝色的病床上,整个人像是一条脱水的游鱼,软软地瘫在纤薄的棉被里。她的脸色白得像簇新的雪,唇间发出淡淡紫,眼神则空洞洞地,越发显得脆弱而凄惶。
周晋诺留下来简单安慰了她几句,她都只是睁大眼眸不说一句话。周晋诺说得久了,自觉没趣,便出了房间跟医生去办理出院手术。
按他的意思是,他要把可岚接回家里慢慢调养。
屋里很暖和,我却依稀感到有股子凉气直溜溜地蹿到心口,带来锥刺的疼,我忍不住战栗了一下,伏在可岚的床边,轻轻抚摩她的发:“可岚,疼不疼?”
可岚沉默着摇摇头,刚做完引产她几乎没有半分力气,只是倦怠地侧过脸,眸光如遥远的雾霭。
我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握住她的手轻轻地安慰她:“我知道你伤心,可是你还年轻,还会有孩子的。”
可岚置若罔闻,眼中有晶莹的泪光一闪,却终究没有落下来,只是平静地说着:“不,你不知道,你没有怀过孕,就不会知道那种痛。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从我的身体里流出去,那样撕心裂肺的痛,就和生产时一个样儿,可别人生下的是喜悦,而我生下的却是孽。我知道,这辈子我已经完了,今天从我身体里流走的不仅是两块肉,还有我的心。心没了,人还活着做什么?”
说完这话,她仿佛很倦,不堪重负地侧过脸,阖上眸子,清亮的泪便大滴大滴地落在她因失血而苍白如纸的肌肤上。
我心疼退后一步,捂住自己的胸口,我知道,可岚的豪门梦,已经彻底碎了。
走廊里,周晋诺贴着墙壁站着,默默地抽烟,一向飞扬的脸庞也苍白得吓人,眼底尽是血丝,显露出一抹从未有过的憔悴。
是啊,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亲身骨肉,他又怎么会不痛?
“她怀孕前是不是吃什么药了?”走出病房后,我心底一片冰凉,抬起头死死盯着的他,“你说话啊!”
起初周晋诺只是一味的沉默相对,但后来被我逼问得急了,只得叹息一声:“是,我是让她有助于怀双胞胎的药,可我是想,一旦她为我们周家生下两个男孩,我爸就不会再找她麻烦,我就可以……”
“你就可以什么?难道你真的会娶她吗?”我走到他跟前,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害她,不是在帮她!怀上双胞胎是天大的喜事没错,可如果是乱吃药怀上的那也是天大的危险。”
周晋诺重重一拳捶到旁边的墙壁上:“我知道,都是我的错,可我只是太想有我们的孩子,太想让她进门了。”
“进门?”我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忍不住心底的悲愤与怒火,我狠狠一个耳光就这么扇在周晋诺的脸上。
这一掌拼尽了我全身的力气,震得我手腕发麻,这么多年的恨和忍耐都在这一掌中倾泻而出。
响亮的声音震得走廊里的医护人员都纷纷停下来回顾,我胸口不断地起伏着,伸出手指直指着他:“这一巴掌,我是替可岚打的,周晋诺,这辈子你要是敢辜负可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周晋诺被打得偏过头,白净的皮肤上也现出几道指甲勾出的血痕,眼中有愤怒像流星般一闪而过,但却难得的隐忍下来没有发作。片刻后,他反过来冷冷看着我:“我承认,我是很花心、脾气也不好,不算是个好男人。但是我也知道可岚是个好姑娘,我是不会亏待她的。”
其实我心里也有些后怕,但我还是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记住你今天的话,可岚是个心性很高的女孩,如果你要是辜负了她,她就活不成了。”
回家的那段路上,车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疾驰,路旁枯败的花草飞快地从两边掠过。也许是道路太过于颠簸,我忽然觉得有一股酸味从胃里翻山倒海似地往上涌着。不得已,我拍着玻璃叫司机停车。
双手扶住路边的栏杆,我难过地弯下腰,胃里冲涌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只吐出了胃液似的酸汁。
最近两天我总是这样。
慢慢倚靠在栏杆上,我用倦怠的目光凝望着这座逐渐被夜色笼罩的海滨城,忽然想起,这也许就是孕吐。
“别人生下的都是喜悦,而我生下的却是孽。”
本以为自己可以很镇定,可当我重新坐回车上,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可岚说这话时的悲凉眼神。我偏过头,注视着车窗外不断消逝的景色,终于还是难以抑制地崩溃了。
在这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唯独没有尽头。根本就没有尽头。
悲伤的尽头,痛苦的尽头,命运的尽头。
我看不见的是这一切的尽头。
……
回到家后,晚冬的一天已经投入幽深的暮色里,寒风依旧沙沙地呼啸着,扰得人心绪不宁。
我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中,确认无误后,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兜里拿出包装好的验孕试纸。一切就绪后,我深吸一口气,定睛注视着试纸上的条纹变化,心却慢慢冷却下去。
对照线和检测线都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是阳性无疑了。
欧阳琛一整个晚上都坐在书房里处理公事,我几次想进去跟他谈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启齿。更何况那扇木门正紧紧地锁着,跟他的人一样冷漠严肃,令人无法进入。
站在门口驻足良久,我终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抱着枕头坐在床上,我想,我必须为自己的将来盘算一下了。
一周后,欧阳琛外出谈生意。
趁着这个空档,我决定离开。
“叶小姐,您这是要去哪?”
一大早朱管家就看到我提着行李箱从楼上走下来,急得她立马放下手中的早餐,直奔着我跑过来。
我把行李放在地上,顿了顿,说:“去我该去的地方。”
“欧阳先生还没有回来,您等他回来再走好吗?”朱管家为难地皱起眉头,“或者,您给他打个电话?您要是就这么走了,他一定会怪罪我的。”
我不听她的话,坚持要走,朱管家拦不住我,很是为难。
“让她走。”忽然,门口响起一记声音。
“欧阳先生。”
我顺着朱管家的目光望过去,欧阳琛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
没想到他会提前回来,我心虚地低下头,半晌才说:“你随便说什么都好,让我走吧。”
“想走就走,我绝对不会留你,”欧阳琛的语气一如平日般淡漠,“不过……走之前我想先告诉你一个消息——”
“嘭——”
手里的行李箱应声坠落,我呆在那里,整个人如遭雷击。
……
那天下午我就径直去了医院。
“叶太太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尤其是肾脏,”主任科室里,刘医生将检验单递给我,“你来看这个检查单子,各项指标都不太好,这是慢性肾衰竭的征兆。”
“肾衰竭?”
我脑子轰然一响,双手下意识地扶住墙壁,几乎就要站不住了,慢性肾衰竭就意味着要换肾才能治愈,而换肾就意味着更多的钱。
“我们医院是没有与你母亲血型匹配的肾,我帮你问了问附近几个市县的医院,都是一无所获,”刘医生抱歉地摇摇头,“对不起叶小姐,要救你母亲,我真的爱莫能助。”
我浑身的血液似乎都要逆转了:“那我该怎么办?”
“叶小姐,说句医生不该说的话,叶太太现在的情况,能醒过来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甚至于活着比死了更难受,你为什么非要这样执着不可呢?”似乎是心存怜悯,刘医生看住我叹了口气,“如果你放手,不但叶太太会得到解脱,你也不会挨得这么辛苦——”
“刘医生,您肯对我说这番话,这说明您是个好人,”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我疲惫地垂下眸子,心里一片黯然,“但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还活着,还留有一口气,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所以为了我,妈妈一定不会放弃她自己。”
说完这句话,我含着泪闭上双眸,默默地对自己说:为了妈妈,我也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
海滨市的夜晚静悄悄的,尝惯了灯火酒绿的滋味,这样的悄静反而像是一根尖锐的针,狠狠地刺入我的心窝。
再一次的走投无路,再一次的不知所措。
命运为什么从不眷顾自己分毫?
我烦闷地坐在路边的凉椅上,一遍一遍地翻着手机,想从中找出什么救星来,忽然我脑袋一转,想到初来海滨时曾拜托过的那个地头蛇赵志勇。
我听说那个人手底下也接一些倒卖人体器官的私活,也许这是一条活路呢?
可这毕竟是犯法的……
犹豫了再犹豫,最终我还是一咬牙拨通了赵志勇的电话,听完我的叙述,赵志勇沉着声音说:“你的情况我大概解了,黑市上也许能找到可以匹配的肾,不过这个价格吗……”
“价格大概是多少?”
赵志勇的声音浸透着黑商的冷漠:“你也学过医,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现在的市价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肾至少也得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我只觉得心中怦然一跳,整个人都跟着软了。
离开欧阳琛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他送给自己的值钱东西都放在房间里了,我几乎是身无分文的离开的。先前可岚也给了我一笔钱,但那些钱跟五十万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
钱钱钱,从来没有一刻我是如此地唾弃钱,却也从来没有一刻我是如此地需要钱。
初春暮远的街头,新木未发,天意清寒,每一缕风都流淌着无尽的萧索。
我失魂落魄地在坐在小吃店里,明知道自己身体虚弱,应该吃点晚饭恢复力气,但脑子里却一遍遍地回响着刚才和张玉的对话——“玉姐,我想回来上班,可以吗?”
“叶轻,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上面有人特意交待过,整个海滨的娱乐会所,都不能再收留你。”
不能去CLUB上班,就不能快速的赚到钱。他竟然这样逼我。
那么,我该怎么办才好呢?难道真要这样没有志气地回头找他?
不,我不可以!
牙齿轻咬住殷红的唇,我再度拿出手机,找出电话本一条条地翻看着,还有谁能帮我呢?
可岚?不行,可岚现在已经足够伤心了,我不能这么自私地去让可岚多一份忧心。
那么,还有谁能帮我呢?
慢慢地在屏幕上拨划着,终于,在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上顿住——易北辰。
唇紧紧地抿着,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拨通他的电话,与此同时,小吃店里的电视机却不知被谁打开,里面传来一条刺耳的新闻播报——“据坊间流传,近日,国内知名房地产商龙腾集团掌门人易兆龙先生,因突然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生死不明。专家预计,这一消息将导致龙腾的股市大跌,甚至会引起业界的一场风暴,下面请看一组视频——”
心跳似乎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我怔怔地抬起头,屏幕上画面跳转,变成易北辰从龙腾大楼里快步走出的镜头。
十几家电视台报社的记者蜂拥而至:“易总!听说易老先生早在两年前就瘫痪在床,不再处理龙腾的业务,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
“易总!听说您要和远夏集团的千金周晋雅小姐订婚,这是不是真的啊?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
“易总!易总!”
易北辰阴沉着脸推开多家电视台的话筒:“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手中的号码再也按不下一位,我只是仰面呆呆的看着电视,倏然间,就泪流满面。
最后一扇门关上了,我再也无路可退。
与此同时,手机骤然响起,推开屏幕一看,显示出来的号码再熟悉不过。
胸口涌过一阵深沉的痛楚,我知道,我逃不掉了。
寒夜料峭的尽头,天光微微亮起来,弱小的光晕一折一折地镂穿了别墅铁门上的欧式花纹,投射在我的脸上。
欧阳琛见到我,只淡淡说了一句:“怎么不走了?”
我慢慢仰起头,微微笑着,语意凄凉:“你说过的,什么时候我需要钱,什么就来找你。欧阳琛,我认了。”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没有骨气,也很没脸没皮,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的尊严,和妈妈的命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欧阳琛,他并没有拒绝我,甚至,也没有嘲笑我。
那晚他坐在书房里办了一晚的公,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走了。我连他的面都没见到。
这样也好,省得彼此尴尬。
只是我肚子里的孩子该怎么办?既然回来了,就得想办法,赶紧解决掉,不然留下来迟早会被他发现。
到时候,他一定会更嫌恶我吧。我还没忘记他上次误以为我怀孕时的表情。
我到底在奢望什么呢?
越想越觉得自己愚蠢,我霍然而起,在门口打了车,直冲向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
……
候诊休息处在楼梯旁边,楼上大概是病房,头顶的放下微微传来婴儿的哭啼,此起彼伏的,声声刺入人的耳膜。
生孩子的女人和堕胎的女人居然坐在一栋大楼里。
休息处的牌子下面是一排蓝色的塑料长椅,因为长时间无人坐落,一股子凉便顺着我的大腿猛然蹿进心窝,我一个战栗,只觉得肺腑之间仿佛被一块沉重的大石死死压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别人生下的是喜悦,而我生下的孽。”
我又毫无征兆地想起这句话,我怀上的是孽,是孽。
可是孩子总是无辜的啊!
我抓紧手边的包,就在我几乎想要逃离的时候,护士却叫了我的名字。
低头看着自己还无征兆的小腹,我渐渐地蜷起手指。
既然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就最好趁热打铁,尽快把这个不该来到世上的孽解决掉。否则,于我于他,都是负累。
我知道这样想很自私,可这就是生活,现实不是言情小说,也不是韩剧,现实容不得我幻想。
验完血,我被护士领进手术室时。
大概因为是阴天,房间里阴森森的,在护士的帮助下,我踏上手术台,无影灯的光亮幽暗的像是深夜里的灯塔,使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坠入汪洋大海的恐惧。
“叮——”的一声,针头上的套膜被拔掉,我隐约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好像在前些日子的某个时刻曾特意留心过一般,但此刻混沌的脑子,却让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要开始麻醉了,可能会有点疼,等下您记得跟我一起数数。”
注射器的尖头扎进白皙柔软的手腕,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口也被什么利器狠狠地扎着,疼得我眉头紧缩,下意识地微微挣扎着。然而,手术台上的金属扣子和皮带却牢牢捆住了我,我像一个落入虎口的麋鹿,再也没有脱身的可能。
耳畔依稀还能听到婴儿啼哭的声音,若远若近,仿佛是从自己的身体里传出来的,我猛地闭上眼,忽然就觉得心如刀绞。
只要再过一会儿,那个栖息在我肚子里的小生命就要永远地剖离我的身体了。对不起,孩子,对不起!
如果你是孽,那么妈妈就是那个作孽的女人!
妈妈对不住你,下辈子,下辈子你再来做妈妈的孩子,妈妈一定会全心全意地爱护你、保护你……
眼眶里,大滴大滴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涌出来,护士用纱布静静地替我擦拭着,声音轻柔地好像小时候妈妈唱的童谣:“一……二……”
“一……二……”
我麻木地跟着念,语调却渐渐含糊、迟缓。就在忽然之间,我仿佛坠进黝黑的大海里,被无边的水浪紧紧包裹着。
我疲惫地挣扎着,想脱离这片无垠的苦海,却不知该游向哪儿去。
瑟瑟凄冷的海风中,依稀有道微弱的光亮穿云破雾地映过来,我仿佛抓住了希望的稻草,朝着那抹亮光拼命地游过去。
“三……”
耳畔又传来柔软的声音。
我仰起,最后一个灯塔的光亮倏然间熄灭了,整个世界都陷入绝望的漆黑之中。
……
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还没有回来。
其实男人不回家多正常啊,何况这儿又不算是他的家。
不再等他,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也许是因为妈妈的病,又也许是因为我那个可怜的孩子。
人在脆弱的时候总想找个寄托,我也一样,这么多年来,支撑我走下去的那个寄托——就是易北辰。
我坐起,小心翼翼地从一本书里拿出大学时易北辰跟我的合照,反复摩挲着,仿佛只要这样,那样美好的时光,就全都能回来了。
可是,“嘭——”的一声钝响,门被人用力地踹开,时光也散了。
我猛然抬头,是欧阳琛。
今晚他不是说自己去应酬,不会回来了吗?怎么又突然……
而且……他的脸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那样狭长而狰狞的一道血痕?就连眼角都破了皮,显露出可怕的淤血。
又是“嘭——”的一声,门被重重地带上。
欧阳琛斜斜地倚在门边的墙壁上,黑瞳里散发出一股被酒精浸泡的危险:“过来。”
“你喝酒了?”我抬眸,故作镇定地瞥了他一眼,并没有任何行为,握着照片的手却下意识地向背后缩,且止不住地战栗。
欧阳琛薄唇紧抿,冷峻的嘴角边忽然就溢出一抹笑,不知道为什么,这看似平静的笑容却让我心里发毛。今天的他,看起来说不出得可怕,就像是从地狱里走出的魔鬼。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欧阳琛已经快步走近我,长臂一伸将我拽进自己怀中,而后上身往下倾弯,把我重重地压倒在床上。
“躲什么?”
危险而灼热的气息喷薄在我的肌肤上,激得我一个激灵:“我没有。”
唇角微扯,欧阳琛却蓦然抓住我的手腕,轻易就把我的手心翻转过来。
时间在这一刹那倏然止住,我几乎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照片里易北辰的面部已被我在匆忙中撕去,只剩下一个高大挺拔的男子身影,然而,只需这么一个身影,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你在流血!”想要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大着胆子抚上他淌血的脸颊,轻声说,“再不去医院处理,伤口会裂开的。”
“你只看得到这里……”
对方没来由地冒出这么一句话,我正迷茫,他却一手紧紧攥捏着那张照片,将它揉碎了狠狠地丢出去,另一只手则突地按住我的肩,接着一低头,吻住了我微张的唇:“你就只看得到这里!”
双腿被他紧紧压迫着,双手则被他箍起来抵在头顶的枕头上,我想到那个孩子,扭过头躲避着。
“今天不行——”他的袭击几乎没有任何技巧、每一个动作都透出征服的欲望,我想反抗,但每次都被他重新压回来,我是真的怕了,睁大了眼睛哀求他,“求你。”
“今天不行?”欧阳琛顿下来,一双黑瞳深深地凝视着我,那里面交错着各种情绪,似是胁迫又似是惘然,“为什么不行?”
趁此机会,我咬咬唇,警觉地向旁边退了一步:“我例假还没过去,这样不安全,也会痛的。”
“痛?”
“是这里痛,”欧阳琛冷冷睥睨着我,手却轻轻按住我的心口,低笑连连,“还是这里痛?”
听出他的语带双关,我侧过身子想要躲开他,却被他一伸长臂抓过来。
“说话!”欧阳琛捏起我的下巴,将我的脸用力地抬起来,“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怎么现在变成哑巴了?”
我凝眸看住他,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眶流出,滚落腮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让我说什么?还想听我说什么?还有什么话能让你满意、能让你开心!”
“还知道哭?”欧阳琛冷硬地替我拭去泪,语气寒得似冰,“知道哭就好,还能哭出来,就说明你还不够痛。”
我微微蜷缩了一下,也不肯说出一句话,眼泪却掉得更凶。
“可惜我却一点也不想看到你哭。”
他用双手慢慢捧起我的脸,方才还阴霾满布的瞳孔里竟闪现出孩子似的憧憬:“我喜欢看你笑,叶轻……你为什么不肯对我笑?”
我偏过头,打下他的手:“欧阳琛,你喝醉了,脑子不清楚了,我求求你别再闹了好不好?”
黑眸瞬间沉下去,欧阳琛深深看住我,手掌微微下挪,蓦然间掐住我的脖子:“你不是卖笑的吗?怎么让你笑一笑比哭还难?还是你跟我在一起,就只会哭,不会笑!”
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冷酷的话,我僵在那,心痛让我不顾一切地推开他:“是!我是卖笑的!那你又算是什么?”
“我妈妈都病得快要死了,你还逼着我对你笑!你知道你有多残忍吗?”
欧阳琛一把扯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得贴近自己的胸膛:“你以为你很可怜吗?你以为这样就算痛吗?不,你还不够可怜,你还不够痛,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痛。”
“欧阳琛,你不是人,你是禽兽,你……”我喊叫着,咒骂着,拿枕头砸他,用腿踢他,他似乎疼了,闷哼一声将我翻过去。
我被他重重压进被褥间,连呼吸都快要湮灭了,好艰难才侧转头深吸一口气,便看见雪白的床单上有一大滩刺目的鲜红,就连我的衣服上、肌肤上也全都是血。
惊愕地抬起头,我抓住他的手臂上的衣料猛地掀开来看,几乎是倒抽一口气。
好几道血肉翻开的创口正像蜈蚣一样蜿蜒在上面,鲜妍的红色顺着他的肌肤淌出来,简直触目惊心。
倏然间,我呆呆地愣在那里,直到他望着自己布满血迹的手臂,同样怔然地顿住了,我才问他:“你的手臂怎么了?”
欧阳琛没有理我,解开一半的衬衣颓唐地贴在他的身上,饮过酒的双眸似乎再没有聚焦的结点,只是一瞬不瞬地盯视着自己的手臂,空洞的、麻木的、忧郁的、甚至于悔痛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在其中反复交融着。
“欧阳……你说话啊!”
已经习惯了那个果决雷厉的他,这样惘然甚至于脆弱的欧阳琛反而让我于心不安,我小心翼翼地捧起他的手臂,仔细查看着,眼睛因为焦急而流下滚烫的泪水,一滴一滴地顺着腮边滴到他皲裂的肌肤上,晕开了斑驳的血迹。
越看越觉得心惊,这些伤口个个都深得可怕,可偏偏那个受伤的人却似乎丝毫觉不出痛般,纹丝不动地坐卧在床边,我急得哭喊出来,连声音都是断断续续地:“为什么……这些伤都是怎么回事?你回答我啊!”
“我是个禽兽……”
热烫的泪好似在火上浇过的油,就这么淋在肌肤上,渗入肺腑间,欧阳琛终于有了一丝反应,他长臂一弯,将我的后脑深深按进他怀里,而后仰面躺下。
疲惫地阖上眸子,他像个穷途末路的野兽般颓然地阖动起唇角,再次重复:“我是个禽兽。”
“欧阳……”听出他嗓音里的不同寻常,我蓦然一惊,难道他在流泪?
我想抬起头看看他的伤势,却被他死死的压制住,一下也动弹不得。我带着哭腔近乎恳求地问他:“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接下来是死寂般的沉默,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片冰凉的唇才贴着我的耳缘,低低呢喃:“……今天是我父母的忌日,也是我的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