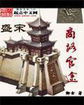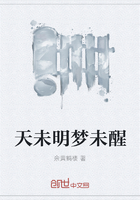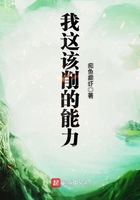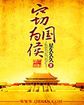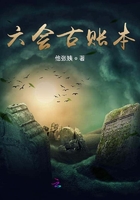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一下子使得经营盐铁的商人们富比王侯,但他们往往为富不仁,没有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常常进行各种边疆战争,需要大量的钱财,中央财政日益窘迫但富人们却对此无动于衷,汉武帝对此大怒,便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三国、两晋注重专卖,南北朝时征税制复起。隋至唐前期,取消盐的专税,和其他商品一样收市税。唐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盐专卖又开始实行。
从上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虽然各个朝代也有过把盐进行民营的情况,但当国家财政一吃紧的时候,他们便往往先拿盐开刀,把经营权收归国有,顿时财政收入大增。
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大臣刘晏很善于理财。他为了解决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对改革传统的盐铁专卖制度进行改革。当时虽然进行垄断专卖,但得到的利润往往被官员们私吞,而且政府在长期的垄断后也逐渐失去了活力,使得这一项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
刘晏决定实施政府与商人合作的官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度。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一次产权重新划分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政府对商人说,盐是我的,我生产出来,但由你们来进行运输和销售,我负责保护你。不过前提是,你要成为盐商,你得先交一大笔钱,以获取成为盐商的资格。大家都能看到做盐生意是块香饽饽,那些平时家底雄厚的大农民和大商人都赶紧交钱,做起了运输、买卖食盐的生意。这项政策在开始有效减少了走私食盐的情况,给国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唐德宗之后,盐价跟现在的石油一般,价格一路攀升。而原来的盐法时间长了,弊端越来越多,当然空子也越来越多。因为利润丰厚,贩盐成为非常有效的致富手段。
这时搞食盐走私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中小商人,他们无论是钱财还是权势都不够,无法进入体制内参与财富分配;二是大量破产逃亡的农民。他们加入贩卖私盐的行列,成为非法的个体户;三是所谓的“官商”。包括盐商、为官府放贷的高利贷商人在内的富户大贾,他们有钱有势,在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参与走私。
到了帝国后期,其他方面的生产差不多都很凋敝,收入不多,盐税因此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支柱,占整个财政税收的半壁江山。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只能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走私,甚至采取连坐法,一人走私,邻里家人都要受牵连。
但打击的结果是对那些在各种政治势力庇护下参与走私的富商大贾毫无影响,而那些体制外的小商小贩则大受其害。在严厉打击下,私盐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他们互相联系或者聚伙走私,或者遥相呼应,有时候贩盐,没盐可贩的时候就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当然也有人平时就是老老实实的商人,而有机会的时候便是典型的盐贩。
黄巢干的就是这种事情。
黄巢,曹州冤句人(现在的山东曹县西北),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曹州是贩卖私盐的“重灾区”,是私盐的重要集散地。当地有很多贩卖私盐的家庭,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贩卖私盐,到了一定的年龄便开始谋取其他的出路。
唐代的商人可以通过买官捐纳、参加科举考试和参军三条途径谋求政治出路。一般的小商人没钱买官捐纳,由于自身地位卑微,一般情况下科举中第的可能性也很小。而募兵制的实行虽然为小商人们提供了入仕做官的可能,但由于募兵制长期被宦官操纵,能够获得军籍的也只有那些家资丰厚的大商人。到了帝国末期,由于延揽人才、招募军队的需要,无论中央政权还是地方藩镇,都极大地降低了招贤纳士的门槛,这就为那些文化素养不高、财力不厚的私盐贩通过参军改变命运提供了可能。
黄巢小时候爱读书,读过一些经典、传述,能写诗。据说有一次,黄巢父亲与一老人以菊花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黄巢父亲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应声咏了一首《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青帝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主管万物的生长。在这儿黄巢为在秋天才开放的菊花大鸣不平,认为天气太冷连蝴蝶都不愿意来光顾了。他雄心勃勃地说,以后要是我做了主管万物生长的青帝的话,我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开放。
既然是出生在盐贩子家庭,家人不仅仅教他读书写字,还教他舞枪弄棒,这估计正是黄巢的诗歌与那些酸腐的读书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写所谓的爱国忠君、讥讽时弊,也不写感时伤怀,更鄙视那些什么孤高自赏,清风玉洁,他要的是直接的改变,而这改变则是由他来完成的。
家里自然能够希望他中第做官,然后一方面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对家庭生意也可以多加“照顾”。据说父亲给他取名为“巢”,就是指望儿子日后能够荣登科榜。“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于是他便带上一笔钱兴冲冲地奔赴长安,准备去寻求他的成功之路。
唐代的长安可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这儿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官员,与大官们大太监们甚至与皇上沾亲带故的更是数不胜数。而且满大街都是古惑仔,他们都往往是各地的楞头青,觉得家乡小地方不适合自己这“蛟龙”发展,于是都到京城寻找机会。还满大街都是读书人,这帮读书人都是来求取功名的,他们在长安没事可干,先把自己的作品复印多份,然后哗啦啦地抛撒出去;要不就是像陈子昂摔琴那样惊世骇俗地表演上几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长安的大人物听说有自己这么一号人物。再一个就是满大街的酒铺子和妓院,当然还有满大街的富人,其中有印度人、波斯人、朝鲜人、吐蕃人,各种语言、肤色、身高、体重都有。
所以京城不是好混的地方,据说当年白居易也跑到京师去求取功名。他爷爷还当过宰相呢,也算是典型的世家子弟,但长安的世家子弟实在太多了,他一到长安便感觉整个人被融化掉了,什么都不是。一个大人物听到他名叫白居易,笑着说,恐怕你在长安居住的不容易啊。后来小白赶紧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献上去,这位大人物过目之后大为赞赏,说,嗯,这么有才的话,是可以在长安白白居住的。
黄巢当然没有白居易那么有才,所以他每次总是花完盘缠之后便灰头土脸地跑回家了。他还是挺本分,知道老爸赚钱不容易,也不敢过多地留恋京城。
几次落第后的黄巢终于绝望了,他越来越郁闷,求取功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每次进京都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最后一次落第,他题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他在心里恨恨地发誓——一定要以另外的身份进入长安,他要让长安的百姓们夹道欢迎,要让长安的豪贵们在他面前颤抖。
科举之心死,他没有选择参军,而是正式步入贩卖私盐的行列。在这个行列里,他碰上了首倡起义的王仙芝。
有压迫就有反抗。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的那一年,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朝廷的高压政策,王仙芝聚集了几千个农民,在长垣发动起义。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直接打出均贫富的口号,谴责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口号得到百姓们的热烈欢迎。
黄巢看到当年的哥们已经动手了,于是也起兵响应。这场颠覆帝国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起初进行的很顺利。黄巢起兵后不久便和王仙芝汇合,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朝廷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眼见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黄巢得知这个消息,气极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责备王仙芝,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
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自己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
这么一来,哥俩个也只能分道扬镳了。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被唐军打败,他也死在乱军之中。王仙芝失败后,残余的兵将在尚让的带领下与黄巢的农民军汇合,大家推黄巢为王,又称冲天大将军。
王仙芝的死给了黄巢独立领导起义机会,也给了他与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筹码。其实,无论是王仙芝还是黄巢,作为游离在国家体制外的私盐贩,他们都一直没有放弃过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梦想。黄巢之所以反对王仙芝此时受招安,只不过是因为此时他们的筹码还太小,完全不足以与朝廷谈判,至于骂王仙芝的“同心协力,平定天下”云云,估计他自己也是不太相信的。
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大批兵力准备围攻。黄巢看出敌人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到占领广州,形成与长安形成对峙的局面。
早在围困广州的时候,他便通过唐浙东观察使崔璆和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二人替他向唐朝廷上书:只要朝廷授予他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他便愿意归顺。之所以是天平节度使,而不是其它地方,一是因为天平富饶,二是因为黄巢本人是山东人。当然朝廷没有接受。
黄巢一怒之下攻破广州,大肆掳掠。但同时他开始犹豫了,看着远方的长安,他不由得对前途有些厌倦,他再次找人上表,要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看样子他是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了,不用到山东,在广州当个地方诸侯也不错。但朝廷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对于这种地位卑下的盗贼,朝廷一贯的政策是诛之而后快。他们的逻辑是对于那些地位比较高的如节度之类的叛乱可以姑息养奸,因为他们也算是上等文明人;而对于这些犯上作乱的草根阶级则决不姑息。在这一点上,帝国的阶级论一清二楚。
朝廷没有回应,而广州城内却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手下的将士们开始想念北方的煎饼和大葱,都纷纷请求向北发展。黄巢对朝廷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他决定带兵北上。于是黄巢带领人马一路北上。朝廷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击,被黄巢起义军各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朝廷寄予厚望的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出来应战。黄巢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直奔东都洛阳。
朝廷差不多绝望了,高骈此时并非真的中风,而是有人告诉他说,主公你如果打赢了那地位也上升不了多少,而且还有功高盖主的嫌疑;而万一打输了,赔了老本那就不划算了。高骈想想觉得很有道理,便按兵不动了。高骈直接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的节度使也依样画葫芦,来了个隔岸观火。
高骈狠狠地玩了帝国一把,但帝国除了写封信恨恨的骂高骈一顿之外,对当前的局势完全束手无策。而高骈也毫不示弱,他写了封回信,把责任都推卸到僖宗身上。于是君臣之间两地鸿雁传书,展开口水战,这不仅仅在帝国历史上罕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估计都只有这么一次。君不君,臣不臣,帝国也快不再是帝国了。
趁着这对君臣大打口水仗的时候,黄巢迅速渡过淮河,占领洛阳,掳掠一番之后挟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
潼关失守,长安已经是直接暴露在黄巢的眼下。僖宗和宦官田令孜匆忙带着妃子和一些宗亲,抛下大臣,逃到成都去了。
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尚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黄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了。”
黄巢实现了他的理想同时也超越了他的理想。他终于以另一种身份来到了长安,但他仍然是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朝廷对立,他依然没有能够进入国家的政权体制之内。现在攻下长安,他已经无路可退,于是宣布建立大齐政权,原来的体制既然无法接纳自己,那么干脆重建一套体制。
他在长安严惩皇族、公卿,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降官张直方家夹壁中藏有高官显贵百余人,被发现后全部处死。另外没收富豪的财产,号称“淘物”。黄巢终于把自己当年在长安所受的种种怨气发泄一空。
带领将士们南北纵横,转战大半个中国,黄巢迎来了他的辉煌,同时也迎来了他的黄昏。在长安驻扎时间未久,各地诸侯们眼见僖宗逃至成都,天下无主,便都抖擞精神,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准备在这个乱世里边分一杯羹。于是各路兵马包围长安,城中粮草缺乏,军心涣散。
没过多久,黄巢被迫离开长安,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从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反正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便这么失败了。
这场起义由盐贩子发动,同时也为更多的盐贩子们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舞台。在这场起义里,王建、钱镠、朱宣等私盐贩则选择了一条与黄巢截然相反的道路。王建少年时代贩卖私盐,后来参加忠武军,起义爆发后,投奔避难成都的唐僖宗,被田令孜收为养子,在藩镇兼并战争中壮大,成为前蜀政权的缔造者。钱镠年轻时以贩卖私盐为业,后应募参军,在镇压起义军中名声大噪,在藩镇兼并战争中因战功担任镇海节度使,先后被朝廷封为吴王、越王,成为吴越王国的建立者。朱宣的父亲因为贩卖私盐被依法处置,朱宣受父亲牵连遭鞭笞刑罚,后参军镇压起义军,因战功升任濮州刺史、郓州马步都将,在藩镇兼并战争中被朱温杀害。
由食盐带来的税收养活了帝国的大部分官吏,但也正是由食盐带领的一场起义把帝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场起义中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李克用和朱温,但也正是后者,把帝国直接推向了灭亡,后世史学家痛心疾首地说,帝国亡于朱温之后。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