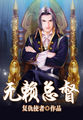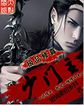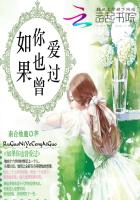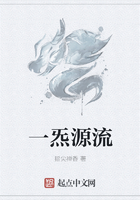他上朝很勤快,每逢单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举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
他很节俭。他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驸马戴了很贵重的头巾,他提出批评。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驸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有一个官员穿着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桂管布是桂林地区生产的一种木棉布,布厚而粗糙,较之绫罗绸缎自然略逊一筹,文宗见他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纷纷效仿,致使桂管布的价格上涨很快。
即位之初,他就下令放宫女,各地额外的进献和上供的奇珍异物也不要,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也都停废。他自己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十月十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被立为“庆成节”,文宗也不允许宰杀猪牛,只许食用瓜果蔬菜,他还特别诏令京兆尹暂停在城南的曲江池宴请百官和在宫中为他祝寿。
有一次他对臣下说:“我身上的衣服已洗了三次了。”众人都赞誉,只有翰林学士兼侍书的柳公权认为,皇上君临天下应该选贤任能,使天下太平,皇上穿洗过的衣服,只是生活细节而已。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文宗先是提拔宋申锡作宰相,宋在朝廷中一向以忠厚正直著称,因此大家都很希望他能够改变一下朝廷的现状,做出一点改善来。但结果宋申锡毫无动静,大家看到的宋申锡完全变了,他只忙着进进出出和皇帝讨论各种问题,朝政却很少理会。这其中的缘由在王守澄死后才被人们隐隐约约地猜到,宋申锡要干的是大事,所以只能暂时把朝政搁置一旁。
后来文宗又宠信郑注、李训,李训还做了宰相。不过他们同样是要干大事,做大事不拘小节,他们不再理会朝廷百官的议论,文宗也顶住了大臣们对郑、李二人的弹劾。这些伤透了大臣们的心,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皇帝唾弃了。甘露事变中自宰相王涯以下六百多官员被杀,这让大臣们彻底绝望了——这就是皇帝干的好事!
宦官们也在问文宗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当他们摆脱李训的纠缠,抬着文宗一路跑进宣政门的时候,他们终于从死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不禁喜极而泣,看到在旁边暗自懊恼的文宗,他们纷纷质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居然伙同李训想把我们赶尽杀绝!
这时候的文宗跟这时候的大唐帝国一样的心境,一切辉煌都已经过去了,太阳一步步地落下山去,除了等待天黑的来临,还能做什么呢?
文宗索性闭上了眼睛,因为噩梦开始了。
慢慢地,文宗的话越来越少,上朝的时间越来越短,他已经不再读书了,开始整天耽于音乐声色。他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一下就更坏了。
就这么过了四年,文宗一直未曾治愈的风病再次爆发,没有了郑注莫名其妙的手法,文宗这一次恢复的很慢。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最后一次上朝,大臣们见皇帝精神不佳,朝会草草结束,文宗回到后殿。
自从生病以后,他的眼前便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幻影,挥之不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他望着远方,沉默良久,忽然问身边的翰林院使,今天当值者何人?
翰林院使有点奇怪,不过据实回答,是周墀。
文宗让人把周墀叫了过来。
文宗并不太了解他,他颇有兴趣的打量了周墀一番,命座,赐他三杯美酒。然后缓缓的说,依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
这时的唐文宗已经完全在宦官的掌握之中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同时也失掉了泱泱大唐的尊严。大权在握的仇士良对他动辄冷嘲热讽,甚至直接训斥有如小儿。
曾经有一次,翰林学士崔慎由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睡觉,忽然有人传令让他立刻入朝。深夜急召,必有要事,他迅速换上朝服直奔宫中。
来到秘殿,不见文宗却只见仇士良高坐堂上,屋内帷幕重重,门窗紧闭,看样子仇士良已经等候多时了。
仇士良看他来了,劈头便说,皇上得病很长时间了,怎么也不见好。而且他即位以来也没干什么事情,导致现在朝政都荒废了。皇太后看着很着急,便想让我早点帮他立个嗣君,今天就是找你来写立嗣君的诏书的。
崔慎由不是二百五,他也知道这种立嗣君的行为是很危险的,首先是文宗并没有表示过要离个嗣君;而且无论立谁都必然要把自己的宝贵前程身家性命甚至整个家族的人头都赔进去,赌赢了自然很好,输了那就彻底完了。所以他拒绝立诏。
仇士良没有料到他这么决绝,一下子不好办了。想了一想,他带着崔慎由从后门穿过庭院到了另一个小殿,一脸愁容的文宗正在那儿。就当着他的面,仇士良一条一条地数落着文宗的过失,而贵为天子的文宗却只是低头不语,任凭仇士良肆意辱骂。
类似的种种事情在大臣中间悄悄流传,周墀也知道。
不过,文宗猛然间询问到这个问题,周墀吓得差点把刚咽下去的酒喷出来,皇帝们都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有的是想找点自信,有点的是想求得一些认可,有的就是为了测试测试大臣么的忠诚度。反正这样的问题技术难度很大,稍有不慎估计就把皇帝给惹恼了。因此,自古以来的大臣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摸不透皇帝喜好,那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皇帝大大的歌颂一番,所谓不打笑面相迎之人是也。
周墀是明白人,他立刻趴在地上,说,皇帝英明神武,兼有尧的圣德、舜的聪明、禹的节俭和汤的仁心,尧舜禹汤这是古代帝王们的模范,韦小宝不知道这四位爷,单知道“鸟烧鱼汤”就已经让康熙龙颜大悦了,因此他们是皇帝们的软肋。
不过文宗现在已经没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久违的恭维了,他真的很想知道大臣们怎么看他,天下人怎么看他,虽然他也知道,谋诛宦官不成,沦为仇士良手中的傀儡,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供炫耀的政治资本,但他还是想问,哪怕得到一点安慰也好。
但周墀并不知道皇上现在的想法,他不知道现在的文宗并不是一个皇帝,不知道文宗现在只是一个渴望得到安慰的失败者,他只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皇帝,一个可以掌握他生死的主宰,于是只能趴在地上等待皇上的反应。
皇帝听完他的话惨然一笑,再次低沉地说,你这是因为爱护我才不得不这么说,我那可能比得上尧舜禹汤?
周墀大气都不敢出,半天他听到皇上长叹了一口气,再次问他,你看我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
周墀终于反应过来了,他听出了文宗语气之间万念俱灰的味道。周赧王是周朝的最后一位天子,面对虎视眈眈的秦国,他无能为力;而汉献帝时天下大乱,各地诸侯蜂起,逐鹿中原,天下终分为三国。
周墀赶紧劝文宗想开点,不要那么悲观。但他又实在想不出什么有点效果的话来安慰文宗,只能是在一个劲的在地上磕头,一边歌功颂德,把各种文宗的小八卦说了一遍又一遍。
皇帝并没有看他,他的眼神空洞无物,不知道指向何方,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许久,文宗以更加坚决的口气说,其实我知道,我比周赧王和汉献帝都还不如,他们仅仅是受制于诸侯,而我则是受制于家奴。说罢,他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不由得俯首痛哭。
周墀还能说什么呢?内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搀扶出殿,透过模糊的泪光,他看了文宗最后一眼。
自那天后,文宗再也没有上朝,一个月后,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文宗就这么走了,带着满腹的遗憾与不甘。可这又能怪谁呢,开启大唐帝国宦官当权的是唐玄宗,高力士虽然是一个忠诚而睿智的老人,可惜他是一个宦官,还是一个有权力的宦官;之后掌握权力的宦官越来越多;但真正让宦官掌握权力制度化的却是唐宪宗,在他眼里,宦官不过是家奴,踩死他们比踩死一条狗还容易,但最大的讽刺也就在这儿出现了,极端蔑视宦官的他却死在宦官手里,让儿子、孙子以致以后大唐帝国的皇帝们都饱受宦官之苦。
在这个过程中,甘露之变不仅仅是一场没有成功的冒险,它更像是帝国的又一次自杀。帝国已经老了,在南衙和北司的斗争中,南衙一败涂地,大臣们日益沦为发布文书布告的工具;皇帝们经过了一次次的血的教训,他们已经不再想有所作为了;藩镇们安于与中央维持下的平衡,独霸一方,倒也平静……一切都不再需要也不再想作出改变,大家都是利益的既得者,因此便只剩下了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于是,大臣之间的党争便日益浮出水面,并成为烦恼帝国安睡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