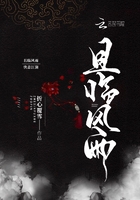走到了珈蓝面前,南云起执起衣袖,擦了擦珈蓝鬓间的汗珠,动作温柔,却不越矩。
一旁的人见到南云起罕见的动作,全都惊得酒醒三分,齐白更是连怀里的美人都忘记搂着了。他没看错吧,这万千花丛过,片叶不沾身的南小王爷,难道是看上这番邦女子了?
为珈蓝擦完汗后,南云起却喟然长叹,“何必呢。”
珈蓝一愣,“什么?”
“我说,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南云起眼里的温柔灰飞烟灭,有的只是怜悯,和佛度世人的超然,“无论你是一朝公主,还是市井舞姬,我都不会喜欢你,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你。”
一字一句,柔情,又最是无情,当真是字字诛心。心里一恍惚,珈蓝腿上一软,跌坐在地上。
美人失魂落魄,看得周围一圈惜花客都于心不忍,不过他们也只能叹口气,南云起是什么秉性,他们是再明白不过。珈蓝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垂着眼,南云起伸出手,将珈蓝拉起来。收回手,转而负在背后,南云起不带任何情感地看着她,说,“这番话,就当做是回敬你这支舞的谢礼,明日就别再来了。”
话说到这里,南云起拿起刚刚未饮尽的酒壶,长饮一口,慢慢走开。
在挑起珠帘的一瞬间,珈蓝突然向前跑了两步,脚踝上的银铃清脆作响,“别走!”
看着那一袭宝蓝的身影,珈蓝刚刚的那些难受全都一扫而空,转而变成了心中的汹涌,怎么都按捺不下来。这就是她喜欢的男人,这才是她喜欢的男人,那些为容,为财,为权而喜欢自己的人,自己怎么会看得上。
珈蓝微微一笑,嘴角带着自信和骄傲,“我一定会让你收回今天的话,一定!”
手穿插在珠帘间,南云起只是停顿了片刻,接着翩然而去。
第二天,南云起坐起身,候在门外的几个随从走进门来,为南云起梳洗换衣。昨晚宿醉之后的后果,就是时隐时现的头痛,脑袋里有根筋绷得紧紧的,十分不舒服。
换了一件淡黄的长袍,南云起擦完了热帕子,递回了随从手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哄闹声,吸引了南云起的注意力。
简单系好了腰带,南云起推门走出去,阿寅随后跟了上来。整理着袖口,南云起一边走,一边问,“这一大早上,怎么这么吵?”
阿寅支支吾吾了半天,只憋出句“主子自己去瞧瞧吧”,便低头装不存在。
挑挑眉,南云起一甩广袖,循声走了过去。还没有靠近花园,就见一个男子被扔到了自己脚下,疼得哎呦一声。倒在地上的男子一咕噜爬起来,整张脸就和个苦瓜似的,皱巴巴的,“小王爷”
见到南云起走过来,齐白立马挺着肚子,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老大,这个女的是疯了,你快帮帮我们啊!”
南云起走近两步,只见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一群公子哥儿,个个都皱巴了一张脸,不是捂着腿就是捂着肚子,那叫一个狼狈。再看中间,珈蓝得意地拍了拍手,昂头看着一群手下败将,“哼,你们再叽歪一句我听听,来一个我揍一个!”
阳光下,珈蓝难得盘起了一头黑发,换上了一身红色骑马装,广开的流云袖配着雪白的肤色,娇艳欲滴。手里的长鞭用力地向地上一抽,长长的红靴用力踩上前,鞋面上的金线绽放出一朵金色牡丹,活灵活现。
珈蓝收起长鞭,瞥到前方的南云起,立马欢喜地跑过去,“喂,死人脸!”
南云起皱眉,“你怎么还在这儿?”
“本公主想在哪儿就在哪儿,想让我走,除非你和我一起才行!”
南云起道,“那你大早上在这动手又算是怎么回事,别告诉你是手痒痒,所以来拿我的门客们练手。”
哼了一声,珈蓝说,“当然不是,是这些人出言不逊,说本公主的坏话,我才出手教训的!”
齐白不服气了,小声嘀咕道,“本来就是嘛,配得上我们老大的,那只有金吴金公子一个!”
珈蓝冷哼,道,“别拿我和什么臭男人比,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谁敢撕齐白的嘴,是不是要先问过我这个臭男人?”一道似笑非笑的人声传来,齐白眼里一亮,一个劲儿地招手,“二当家,你总算来了!”
荆芜嘴角不自觉抽了抽,幸好脸上抹得漆黑一片,不然当场表情就淡定不了。齐白这二货,自从知道他们两人黑白双煞的事情之后,立马改口,喊南云起老大,喊自己二当家,整的就像是人家山寨的悍匪一样。
不理会齐白的星星眼,荆芜一个个扶起了地上的小弟们,语气不善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一个外邦公主,凭什么在大原国土上放肆?!”
看荆芜霸气全开的样子,齐白同一群小弟的星星眼更甚了。不愧是他们的二当家,果然是浑身上下都是王霸之气,不要太帅哦!
打量着这个凭空冒出来的金公子,珈蓝眼里闪过一丝疑惑,满是怀疑。不管许多,珈蓝直接宣战,“想给你的手下报仇,那要先问过我手里的鞭子!”
荆芜嘴角勾起,“那么,恭敬不如从命了!”
练武场的梅花桩上,两人各占一方,南云起则是和一群人候在一旁。看荆芜胸有成竹的样子,南云起心里却稍稍有些忐忑,他之前和珈蓝交过手,珈蓝的功夫确实不错,底子扎实,一条长鞭更是舞得凌厉无比。
而荆芜,她使的招式有些奇怪,平时练习的方法也有些奇怪,虽然常常能出现出人意料的效果,可是严格算起来,她并不是正正经经的武人。如果能够使用吹箭还好,偏偏这众目睽睽之下,暗器是很难使出来的。
显然,荆芜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与别人玩近身战,那对于她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她必须要扬长避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