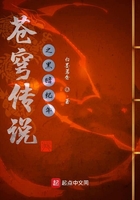说是杂草,那是在外行人看来的,虽然荆芜也不知道这几种花草是什么,但是她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就是关键所在。
这几株花草都还没用枯萎掉,肯定不是从千里之外的大月带过来的,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些东西是在大原朝境内置备的,并且最有可能是在京城中购买的,用来一解燃眉之需。
想到这里,荆芜福至心灵,翻看起那几盒颜料来。打开所有盒子的盒盖一瞧,果然有一盒红色的已经见底了。
握着手里的草,荆芜心里有了大概的轮廓,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荆芜循声望去,桃锁单吊着一只脚,蹦蹦跳跳地走进来了。
见荆芜看着自己,桃锁默默地低下头,站在她身边不敢瞧她。
荆芜叹了口气,刚刚孙妙香回来好一通发火,再想想时间,正巧是撞上了桃锁去的时候,估计这伤和孙妙香也脱不了干系。
等了半天,桃锁见她一直不说话,小心地抬头,说道,“小姐,您生气了吗?”
荆芜回道,“你说呢?”
“我和你吩咐的话,你是不是当成耳边风了?”
桃锁摇摇头,“没有,我记得好着呢!”
自从之前在陆家,被孙妙香打伤之后,荆芜就和桃锁下了三条军令状。被骂要还口,被打要还手,被人欺负了,一定要双倍奉还回去。
开始的时候,桃锁还不敢多惹事,平时有人排挤欺负,忍忍也就算了。直到有两次被荆芜撞见,那几个下人全都被整的凄惨无比,桃锁也被罚每天跟着荆芜跑圈,差点没有被累趴。于是从那以后,荆芜自创的泼妇门首席大弟子就这么慢慢养成,越来越牙尖嘴利,谁来咬谁。
当然,比起荆芜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荆芜搬来个凳子,让她坐下,“你就光会说,等伤好了和我上梅花桩去,跑个五百圈再下来!”
桃锁委屈地点点头,不过还是没有忘记正事,“小姐,我刚刚出去的时候,见到陆佩蓉了。你上次还叮嘱我要多注意她,她果然是不正常!”
荆芜瞧着她,“怎么说?”
“我在一家叫茗苑的楼前见着她了,凭陆家现在的本事,她是万万进不去的。燕将军派人去打听了一二,说是茗苑里正巧来了个贵客,还是从宫里来的。”
荆芜一皱眉,“燕将军有说,是哪个贵客吗?”
“没有,只是说不在宫里的那个就是。”
荆芜一思索,顿时一拍桌子。对了,陆昼前几天还一直念叨,说是今天六皇子是要去国子监说课,想去看看来着。这么说来,陆佩蓉背后的少爷,就是九皇子了?
南恭冽,郑妃,瑞王妃,南行水。
很好,现在敌人都站在一条线上,也省的她多费心思对付了。
明月当空,月华洒在院子中,却被院中的灯火比得黯淡无光。无名府的前厅里灯火通明,四周都用轻纱围起,正中间还燃着一鼎四方铜鼎,让整个室内全是酒肉暖香,半分深秋的凉意都没有。
主位上,一个衣衫凌乱的男子坐在那里,宝蓝的外裳松松垮垮地散开,露出了雪白的里衣。只见他整个人偎在椅子里,左脚架起,胳膊撑在膝盖上,一副微醺的不羁模样。偏偏这酒不醉人,男子还举着个白玉壶,扬起脖子就往嘴里灌。
再看座下,全是一群喝得正美的男子,个个寻欢作乐,好不快活。众人推杯换盏,秀丽婷婷的侍女在人群中穿梭,当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沉醉在这美梦中。
男子将酒壶放下,抹了抹嘴角的残酒,清冽的嗓音响起,“歇了吧,弹得我头疼。”
乐姬们收了音,抱着瑶琴,恭敬地退下。
端起酒壶,男子又开始喝起来,半闭着眼,玉白的手指搭在壶盖上,简直比那玉酒壶还通透两分。
坐下的宾客们都有些醉意,调笑着说,“小王爷,这喝闷酒多没意思,要不小弟去金楼里,找个漂亮的花魁,也好解这长夜漫漫啊!”
哄笑一阵后,又有人接话,“嗨,齐白你这不是扯淡吗,那金楼哪个花魁不是拜倒在咱们老大的脚下?要我说,那就该找个烈性的,最好还带点脾气,这样才带劲儿不是!”
话头一扯到女人头上,这群酒鬼就完全停不下来了,唧唧咕咕地说起来,还不时不怀好意地齐声大笑。
话一字不落地进了南云起的耳朵里,或许是今晚喝了不少酒,让他的脑袋里开始不听话地转起来。要是让他说,流连花间算什么大丈夫,有本事就独守那一人,从年少到年老,从生到死,生同衾,死同穴。
那一个女子,应当是全天下独一个的,偏偏就只有那一个。她当然要漂亮,漂亮到像团火一样,让人想要靠近,却又怕被燃成灰烬;她也应当可怕,只要她一个眼神,就能够让人怕得无处可逃,生不如死才对。
她也应当柔弱,在倾盆大雨的时候,埋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哭泣,连眼泪都被雨水打湿。
最好的话,平日里有些冷冰冰的,但算计起人的时候,又笑得那么狡黠,仿佛一只狐狸,能够蛊惑人心。
这样一个人,之于南云起来说,是幸,也是不幸。他幸,他遇到了这么一个人,并且可以守在她身边,同她并肩;可是他又不幸,他无法将这份黑夜里的动情说与她听,他和她,都背负着太多东西,阻拦住了他们的脚步。
将手臂遮住眼睛,南云起掀开了酒壶了盖子,对着壶口痛快地喝起来。
今夜,且让他一醉方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