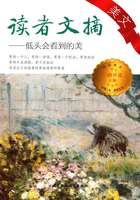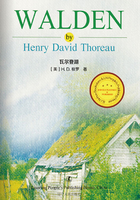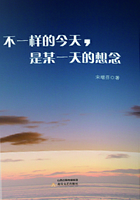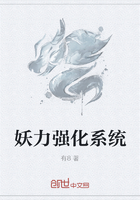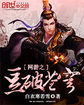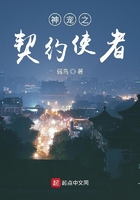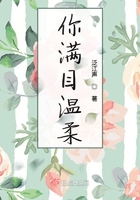对于时间,我曾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畏惧,因为我亲眼目睹它能残酷且不容置疑地把一切新的东西变旧,把所有鲜活的生命都消耗得枯萎、凋零。而随着时间在我身后慢慢流淌成岁月,如同涓涓溪水汇集成江河,我又不由得对它生出一些庄严的敬重。
在时间面前,世间的万物都只是匆匆的过客。从时间的目光里走过的每一个事物,都会被它烙上或深或浅的印记。一个又一个印记连接起来,便构成了历史。人有人的历史,物有物的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物亦有不同的历史。岁月就是靠它们保存着自己的记忆。不管是人还是物,生命跨越的时空越长,内容就会越丰富;穿越时空的存在,即是一座看得见的丰碑,一种摸得着的活化石。
正因了这样的缘由,二十年前,每当我遇到一个满头华发、踽踽独行的老人,我都会从心底涌上一股浓浓的悲哀,为他的行将老去;而现在,每每注视着老人们蹒跚的步履、衰弱的背影,我都会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能够活到一大把子年纪真是件不容易的事: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要躲过多少明枪暗箭,要承受多少天灾人祸,要挣脱多少命运的摆布。很多很多的人因为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或之重,倒在了自己的幼年、少年、青年或中年时代(当然,他们当中不乏流芳百世的英雄或伟人,他们的昙花一现便照亮了生命的苍穹),只有极少数人能长寿。这些长寿的人也许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甚至活得很卑微,但在时间面前,他们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他们的每一道皱纹、每一丝白发,甚至每一片指甲里,都包裹着一嘟噜一嘟噜故事。他们本身就是一部人生和社会的活字典,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在他们怀里揣着。面对他们,面对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面还多的老寿星们,我们除了敬重,还能跟他们说些什么?同他们谈金钱吗?他们脸上的每一片老年斑都比荣华富贵值钱得多!同他们谈功名吗?他们每一次呼吸吐纳的都是贯通古今的气息!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对老人尤其是百岁老人的敬重都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关注。一位老寿星,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整个村庄、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骄傲。虽然他们已不能下地种田,不能驰骋疆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但他们生命体的存在,就是一面面旗帜,就是一座座精神的宝藏。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有一句很普通的话—“只要活着。”每次读到这句话,我都会怦然心动,眼前立即浮现出那些神态安详得波澜不惊的老寿星们。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的,不仅是血液,还有岁月和历史。
在几乎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处旅游胜地,都有一株或几株老态龙钟的古树。它们不一定长成参天的俊伟,但每一根虬枝都直戳岁月的时空;它们有的甚至被岁月掏空了主干,被雷电劈裂了顶冠,但每一片绿叶每一寸皴裂的肌肤都凝结着历史的烟云。没有人能计算得出树的寿命究竟会有多长,我只知道,千年的古树并不罕见。一棵树一旦活到了和所在村庄、城市的历史相同或更长的年纪,就不再是一棵普通的植物了,便接通了地气和人气,便成为精灵。最早知道这个道理,我正上小学。邻村的一个懒汉实在忍受不了严冬的寒冷,在一个傍晚抡起利斧砍向了村里的一棵唐槐。哪料一斧下去,砍伤的枝干立即汩汩地流出了“鲜红的血液”。懒汉见状吓得赶紧跪地求饶。事情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传闻反映了人们对古树的敬畏。如今,对古树的保护早已列入了不少国家的法律条文中,以法律的形式为它们撑起了生命的保护伞。
在许多的地方,甚至是一些荒郊野外,我常常会看到一棵棵被人们用栅栏保护起来的古树。树身上悬挂的标牌也很耐人寻味:“请不要打扰它,它正在撰写我们的村史”、“它已经活了800年,它还要再活800年”、“保护树木就是保存我们人类的记忆”等。显而易见,在人们眼里,它们已分明并不仅仅是树木,而升华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皈依,被顶礼膜拜。我一直以为,懂得珍惜树木的民族一定是个伟大的民族。据说二战期间,列宁格勒被围困了900多个日日夜夜,在那样的残酷环境里,人们卖房屋、卖农具、卖首饰,卖一切可卖之物,以换取一点可怜的食物和棉毯,却没有一个人试图砍树取暖,就连一个早夭的小孩的小棺材也是用旧铺板钉的。正因为此,列宁格勒的树木才得以保存下来。那里的人们记不得的事情,树木都替他们想着。它们的每一圈年轮,都如老人掌心的纹理,流淌着密密麻麻的岁月印记。
同老人和古树一样,能够引起我对岁月敬畏的,还有古建筑。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那么古建筑就是一段年代久远的乐曲,穿越时光的隧道击醒历史的记忆。每一座古建筑都标志着当时的文化和科学水准或具有特殊的人文意义。万里长城、金字塔自不用说,如果没有它们,中国、埃及和世界的文明史将会显得多么浅薄和脆弱。
当然,有价值的古建筑并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在英国伦敦的许多大街小巷里,许多街巷口、店铺和住宅的门口都悬挂着很有特色的小匾牌,告诉人们哪一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或者是对历史有杰出贡献的人曾经在这所房子里居住,经常在这里散步思考。这样的匾牌,全英国有700多块,绝大部分分布在伦敦。2003年11月25日,伦敦又为老舍故居挂牌,使其成为“英国遗产”,缘由是老舍1925~1928年曾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了3年。
正因为这些陈旧甚至破败的短街小巷,才形成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品位和深厚底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已有400年的历史,在加快城市建设中,他们舍不得拆掉旧的建筑,便把老城划为一个特区保护起来,所有的新建设都在老城区以外的地方进行。所以,现在到蒙特利尔,还会有幸参观到一座完整而典型的十七世纪的城市。另外,古罗马的教堂、西班牙的角斗场、我们国家的孔庙,也都历经岁月的沧桑依旧巍然屹立。因为它们的存在,这些城市和国家的历史才显得更加博大和精深,才让人们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没有古建筑的城市是健忘的城市、贫血的城市、浅薄的城市、没有根系的城市。国家亦然。
时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正如孔老夫子的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岁月总会在历史的隧道中留下一座座路标,比如一位老人、一棵古树、一座古建筑,等等。岁月不仅靠它们记录自己走过的历程,也让它们时时提醒人类不要迷失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