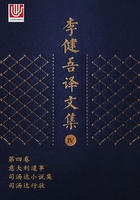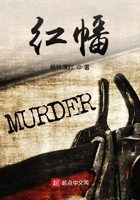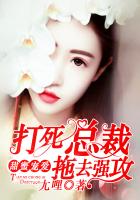让路
奶奶是一个小脚女人,三寸金莲给她的行走带来了极大困难。
何况我的家乡属丘陵地带,沟沟壑壑间的羊肠小道原本就让人头疼。
因为行走的不便,大多数人家的小脚婆娘只是在家里操持,但奶奶没那个福气。由于爷爷常年有病,她不得不用一双小脚承载着里里外外的重担。奶奶的金莲印,因此盖满了小村的山山岭岭。
奶奶走路有个习惯:如果对面来了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甚至连一些牲口家禽,她都主动退到路边,谦卑地给他们让路。即使自己身负重物。奶奶的这一做法曾让很多人过意不去,但奶奶总是坚持着自己的习惯。
奶奶常对我们说:“给别人让路就是给自己让路哩。”年少的我们似懂非懂,但我们真切感受到的是村里人都对奶奶和我们一家很友好。有几次我家遇上了困难,不用奶奶求亲告友,左邻右舍都主动地倾力相助。
挪动着一双小脚,奶奶活了七十八岁。出殡的那天,全村人都站在路边为她送行。目之所及,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就连平日里胡飞乱窜的鸡狗鹅鸭们也似乎通了人性,自觉地为奶奶让出一条路。
一辈子都保持着给别人让路习惯的奶奶,这一次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别人让的路。
拾遗
奶奶喜欢拾东西。
因为是小脚,奶奶走路时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地面,以免踏空。
正因为此,奶奶常常会在路上发现一些东西:一串钥匙、一把农具,或一只新鞋、一个玩具。偶尔也会发现像手镯、钱包之类的贵重物品。
古人云:路不拾遗。可奶奶一旦发现这些还有些用的东西,都要拾起来,在路上逢人便问是谁家丢了。遇不到失主,奶奶就把它们带回家,动员全家人四处打听。看着人们面对失而复得的物品庆幸又高兴的神情,奶奶的脸上总会流露出少有的满足。
时间长了,我家几乎成了一个失物咨询处和领取处。
农忙时节家里常常没人,为了让失主能尽快拿回自己的东西,奶奶干脆用玉米裤子编了一个小筐,把拾到的东西都装在里面,挂在大门口的那棵槐树上。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去冒领那里面的东西,即使村里最不懂事的顽童。
奶奶临终前,筐子里已积攒了许多无人认领的物品。奶奶为此感到很遗憾。她反复叮嘱家人一定要把它们保存好:“说不定哪天会突然有人来找呢。”
泼茶
奶奶在世时,每次喝茶或喝酒,都要将第一杯往地上泼一泼。
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总是拉着慢腔说:“祭先人呢。”那神情,严肃而虔诚。
奶奶是一个不幸的人。六岁时,她的父母去地里看瓜,被暴发的山洪冲走,从此再无音信。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奶奶艰难地长大,十五岁就进了我们张家的门。
奶奶对那些帮助过她的人都铭记在心。虽然没有条件常去看望他们,但她总是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随着时光荏苒,那些好心人相继作古。每次噩耗传来,对奶奶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逢年过节,是奶奶心事最重的日子。她真想亲自到故人的坟上一一拜祭,以表自己的缅怀之情。但她一次又一次忍住了。因为家乡流传着“好女不上坟”的古训,上坟是男人的专利,如果女人去上坟,等于是对坟里人断子绝孙的诅咒。
不能到坟上祭奠先人,奶奶就“创造”了自己的祭奠方式:每次喝茶或喝酒时,第一口都敬给先人喝。
我曾问过父亲:奶奶的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父亲说,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也不清楚,但他知道我奶奶就是为这个才学着喝点茶和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