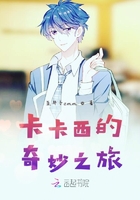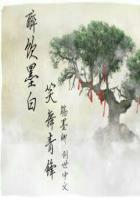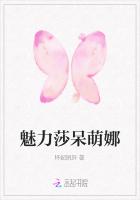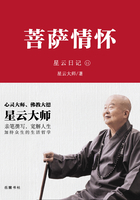乡下的日子如线团,被干不完的农活牵扯得黏黏糊糊。
牵过了春天扯过了夏季,就把一个欢蹦乱跳的秋给网住了。
秋天的田野,褶褶皱皱都兜着丰收的喜悦。天高气爽,微风拂面,原本青翠欲滴、被誉为青纱帐的玉米秸逐渐干枯,怀里揣着的玉米棒子却长成了头戴红缨、身穿黄袍的壮实小伙儿。它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锻炼得结结实实的,密密地排列着,犹如一列列等待检阅的士兵。“庄稼长颈鹿”—高粱最经不起风的挑逗,有风从身边路过它都羞红了脸,并且一红起来就不落火,拘谨得使劲低着头,真是关公的脸、林黛玉的心。大豆通常是与玉米套种的,个子比不过玉米,就扬长避短,多长豆角,多育豆粒,浑身上下都长满了丰收的希冀,一阵风吹过,立即奏响丰收的乐章,让高高在上的玉米不敢小觑。就连山岭薄地和地头沟边点的花生、秧的地瓜,也一不小心就用臃肿的身躯撑破了地皮,顿时把整个秋天都惹笑了。站在田间地头,无论朝哪个方向吼一嗓子,都会立即有人来迎合。那种气势,即使天下所有的文人墨客们都扯了嗓子一起喊,也是相形见绌的。
人们再次掀起一个农忙的高潮。秋收显然比忙麦要繁杂的多,但人们却忙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哪块庄稼熟得早,就先收拾哪块。
通常是先将玉米、高粱、大豆之类的收拾利落,倒出地来种上小麦,最后再慢慢地去收拾花生、地瓜。不管收拾什么,都是一样的大刀阔斧又小心翼翼。秋天的忙碌与以前有明显的不同:以前的劳作是付出,现在是收获。因此心情也就大不一样。虽然汗流浃背,心里却嘿嘿地笑。平日里浇水施肥锄草总嫌地多忙不过来,现在却恨不得多些再多些,一秋收不完再搭上一个冬天才过瘾呢。
田野里登时热闹起来,一场在天地间上演的大戏悄悄拉开了帷幕。男女老少一起上阵,三轮车、小推车、拖拉机一起出动,天籁、地籁、人籁互相呼应;地里人山人海,路上车来车往,场面壮观而宏大。玉米棒子确实长得粗壮,还没等掰上劲就装满了一车,只好在地里堆起一座座小山,催得负责运输的人紧紧张张的,连玩笑也不敢多说。高粱也毫不逊色,穗子不但有关公的脸色,更有关公的体格,多亏根多根深,要不实在托不起那硕大的头颅。玉米秸一割倒,大豆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却被一嘟噜一嘟噜的豆荚坠得实在直不起身子。这些庄稼一股脑儿涌进村,平日里有些空荡的农家小院顿时热闹、拥挤、生动起来。人们尽管白天忙得热火朝天,可晚上也不歇着。吃罢晚饭,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扯上一个灯泡,一家人围坐着剥玉米。人们边干边拉呱,甚至隔了墙头还一呼一应的,浑身的疲劳似乎也随着玉米裤子被一点一点地剥去。一直忙到接近半夜,整个村庄才渐渐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第二天一大早,剥好的玉米棒子就上墙的上墙,爬树的爬树,懒洋洋的太阳一露头,满院子的金黄顿时刺得它有些睁不开眼。
一直耐着性子的花生、地瓜终于等来了收获的人儿。似乎是一夜之间,山岭上长出许多的人字形草棚。远远望去,仿佛一些调皮的顽童随意涂抹在宣纸上的儿童画,简朴而浪漫。花生刨出后,连秧一起晒在地里,等晒干了再摘下来运回家,既缓解了拥挤不堪的院子里的紧张程度,又减轻了运输的分量,还省了一份对付鸡刨狗蹬的心。地瓜可以生着卖,刨出来送到随处可见的收购点,马上就会变成花花绿绿的钞票,省心又省力。但大多数人家是舍不得的。
他们考虑的是:现在手头宽松了,将来怎么办?还是晒成瓜干放在仓里踏实。晒瓜干是比较麻烦的一项农活。你想,要把膘肥体壮的地瓜一个个切成片均匀地摆在地里,晒干后再一片片拾起来,需要花多大的工夫?这种活急是急不上去的,忙碌了大半个秋季的人们正好趁机喘一口粗气。既然在地里搭了草棚,就像临时安了一个家,一家人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坡里度过,村子里的家倒像成了一个摆设。
每到饭时,隐隐约约的小路上就会出现一粒粒隐隐约约的人影儿。
仿佛提前商量好了似的,一律的跨篮提壶。不一会儿,一家人就在草棚前一围,把大地当餐桌,吃得津津有味又野性十足。好喝口的男人等老婆孩子都吃罢了,还捏着个茶碗细细地咂摸,眼睛却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检阅着满地的庄稼,仿佛一不盯紧它们就会飞走似的。
也有的人家干脆把锅碗瓢盆带到坡里,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灶,柴火是满坡半干的野草和花生秧,就像城里人的野炊。虽然忙了一秋,等拔寨回乡,人们竟相互发现人虽黑了不少,膘却猛长。为什么?
吃多了烧花生、烧地瓜是也。这东西,实在是养人。
忙碌了一个漫长的秋季,家家户户都是仓溢屯淌,满院生辉。
接下来的日子就悠闲多了,打着饱嗝串门,趿着拖鞋逛街,哼着小曲赶集,就连夜里的呼噜声也从容而安详—把整个金黄的秋天全都收进了家里,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放松享受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