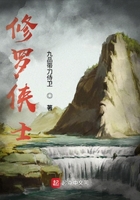可惜,美丽的曾小影并没有被我们的气焰镇住,而是老练地一笑,一弯腰,道:“谢谢,可‘美’这个词太抽象了,谁能来一段对女孩的美的形象描绘吗?”
一时,我们傻住了,没有一个敢站起来。
曾小影仍笑,浅淡如菊,用鼓励的眼光望过来,大概看我蠢蠢欲动吧,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亮了一下,一点头。我站起来,道:“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曾小影伸出大拇指,赞一句:“背得不错,真了不起!”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一脸得意,也让刘小浏他们一脸妒忌。
哼,谁让你们不认真学习语文,后悔了吧。我心中暗暗得意。
我们是曾小影的“粉丝”,每天,仰着头盼望着语文课。
我们爱听曾小影的笑声,还有曾小影的语言,尤其回答问题时,曾小影会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我们,抿着红红的唇“嗯”一声,一笑,然后,拍拍回答问题的学生的肩,让其坐下。
那“嗯”很好听,也如紫藤花香,蒙眬而婉约。
于是,到提问时,我们会争先恐后地举手,没有被叫到的,心里会特不舒服。我被叫的次数较多,每次,曾小影都会“嗯”一声,一笑,拍拍我的肩,很轻很柔。
我骄傲地掉转头,巡视一下四周,如一个得胜的将军,坐下,腰挺得更直了,头仰得更高了,气得同桌刘小浏说:“小心,头仰过去了。”
当然,我们也问曾小影一些我们急于想知道的问题:“老师,我们叫你姐姐好吗?”
“好啊,我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弟弟妹妹,真幸福。”她笑,一脸阳光。
“老师,你有男朋友吗?”冷不丁的,刘小浏蹦出一句话。
我们眼睛都望着曾小影,心里很是忐忑,怕她点头,可又不相信美丽的曾小影会没有男朋友。这么美的曾小影怎么能没有男朋友呢?
她脸红了一下,一笑道:“有啊,所有的男同学都是我的男性朋友啊。”
我们都高兴,高兴中,有些失落,因为,她眼里流淌着温馨。我们知道,有一个家伙,一定抢着做了牛粪,让曾小影这样一朵鲜花,插在了上面。
我们的心中,袭上一丝少年的忧伤,尽管,我们是曾小影的“男朋友”,可仍失落。
刘小浏负责给我们班级送信,因此,他的消息很是灵通。
这小子,最近特别让我们烦,好消息不报,专报不好的。
“曾小影老师送信了,信上还画着丝带呢。”他说。
“小影老师收到一封信,笑得一脸阳光。”他很神秘地告诉我。
我们在心里,更暗暗恨那个给曾小影写信的小子,那家伙一定幸福地跳迪斯科了。我们暗地里发誓,好好学习,将来和那家伙比比能力的高低。
一次,曾小影接到信,拆开,流了泪。刘小浏跑来,一脸愤怒地告诉我们,立马,我们都愤怒了,我一脚踢在一块石头上,仿佛那块石头就是曾小影的男朋友。
我们去曾小影办公室,曾小影的门关着。
轻轻敲门,一声“请进”,我们进去,曾小影眼圈有些微微的红,我们怒火更旺了。
刘小浏问:“老师,是不是你男朋友惹你生气了?”
曾小影听了,愣了一会儿,“扑哧”一声笑了,“说什么啊,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劝我们去上课。我们无奈地走了,私下里商量,由我写信,给曾小影的男朋友,告诉那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人想得到我们曾小影老师的爱都得不到呢,千万别把自己当个人似的,惹我们的曾小影老师不痛快。
信写好,没地址,刘小浏自告奋勇,去偷盗那封信。
以刘小浏的贼溜,那封信顺手拿来,我们打开一看,瞪大了眼。原来,信是一个被曾小影资助了的学生写来的,信的内容充满感激,很有感情,让人读了,感动不已。
曾小影那次落泪,不是伤心,是感动。
于是,我们责备刘小浏,说他傻瓜,现在恋爱,谁还鸿雁传书呢。
“那用什么?”那小子傻得不可救药,问道。
“手机啊。”我点拨着刘小浏,白了他一眼。
事实证明,我的智商,比刘小浏不知高了多少倍,经过深入细致地观察,我们发现,曾小影爱打手机。她有一款很好看的手机,小小的、红色的,拿在手中,如一件小小的艺术品。她经常拿着那个手机打电话。
在校园后边的走廊中,一架紫藤花,到了春夏,一片珠光宝气。曾小影在珠光宝气的紫藤花中,如一只紫色的蝶儿,很好看。
她拿着那个手机,放在耳边,侧着头,一脸的幸福和微笑。
“一定是的。”我们心中,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兴奋,同时,又弥漫着一种失望。我们派刘小浏去偷听,谁让那小子手脚滑溜呢。刘小浏去了,一会儿回来了,一脸沮丧,说小影老师用暗语,老是就一句“是啊,呵,是啊”。
根据蛛丝马迹,我断定,是恋爱。
“为什么?”刘小浏傻傻地问。
“她男朋友问她,你爱我吗?她说是啊。又问你思念我吗?她又回答是啊。”我的分析,让刘小浏眼睛发亮,大拍马屁:“老大,你好聪明耶。”
懒得理刘小浏那小子,没心没肺,我烦着呢。
曾小影的男朋友,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结。
我们把曾小影男朋友的样子,想象得很丑,反正,不配曾小影。心里,又有些不甘,这么美的曾小影,一定要有一个白马王子,才能相配啊。
我们就又想象曾小影的男朋友的样子,长得如陆毅一般。
反正,我们心里矛盾。
曾小影不知道,上课仍微笑着;下课时,常打电话,由原来的走廊,发展到了楼上,靠在楼上走廊的栏杆上,用手捏着自己的一缕头发,歪着头,一脸栀子花般的笑。
我们假装经过,侧过耳朵,不放过一个字。
“噢,准备来啊?好啊,什么时候?我去接。”看样子,那家伙要来我们学校,炫耀自己的帅气。
“啊,过两天就来,太好了!”曾小影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感受,让我们有些受伤。
“曾老师,谁啊?”又是刘小浏,牙尖嘴快。
“一个慈善机构,要来看看,准备资助一批学生。”曾小影说着,挡不住一脸兴奋,扑面而来,让我们的心,轻松了许多。
“还以为是你男朋友呢。”我说,轻吐一口气。
“怎么?你们那么思念他吗?”曾小影一脸惊喜,望着我们,眼睫毛一眨一眨地问。
“谁思念他啊?”刘小浏还准备说,我咳嗽一声,他忙捂了嘴,一缩脖子,跑了。
曾小影笑笑,摇摇头。
那笑,真的,很好看。
慈善机构来了,还有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
曾小影陪着,给当翻译,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普通话,说得老外翘起拇指,“good!verygood!”连连地夸。
曾小影笑,摇摇头,长长的头发,如水荡漾。
我们心里充满了阳光,感到十分得意,仿佛那老外夸奖的不是曾小影,而是我们。
慈善机构走了。
曾小影一脸微笑,回到课堂,还没有说话,我们一起翘起大拇指,一声高呼:“good!”曾小影一头雾水,接着明白过来,又一次弯腰,一头长发洒下,连连道:“谢谢,十分谢谢。”
一学年结束,我们的语文成绩,如紫藤花开,一片灿烂。
我们以为,曾小影会一直教我们,到我们毕业。
可是,曾小影告诉我们,她要走了,要回学校了。原来,曾小影是大学支教团的,一年之后,要回去读研。
显然,她舍不得我们,声音有些低沉。
她说,和我们在一起,她的心干净极了,一片水光。她说她舍不得我们,会把我们每一个学生的笑脸藏在心中,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到老了,七十岁了,也会回忆起我们。
泪水,滑出眼眶,挂在睫毛上。
班上的女生,都低下头,啜泣起来。
尤其刘小浏这家伙,一点儿男子汉气概也没有,“呜呜”地哭开了。本来,我们都极力忍着,被他一引,都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教室的哭声响了起来。
曾小影忙用手擦了脸,道:“同学们,老师离开,喜欢你们笑脸相送,别哭啊。来,唱一首歌,送别老师吧。”曾小影哑着喉咙,起唱了一支臧天朔的《朋友啊朋友》。
歌声响起,开始是一人,接着是所有人,一边擦泪,一边歌唱。
歌声中,曾小影又一次弯腰、低头,向我们致谢,然后,快步走出。隔着窗户,我们清晰地看见她的肩头在耸动。
曾小影走了,我们在学习上没有松懈。
我的心里,有一个梦想,好好学习,毕业了,力争考取曾小影所读的那所大学,像曾小影一样,去支教,去做学生的朋友。
当然,心中,还有一个希望,如果曾小影留校任教的话,我还可以做她的学生,喊她“曾老师”。
上课时,有时语文课上,我仍会想到曾小影,想到她低头、弯腰致谢的样子,就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曾小影走时,留下自己的Q号,说她想我们了,可以聊聊。
我几次上Q,可她的头像都是黑的,打开她的空间,上面一句话很瞩目:“我支教时,遇到一群很好很好的学生,永远,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思念,我心中的天使。”
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任泪流满脸,心中暗想,曾小影,你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思念,我们心中永远的天使。
史蒂文的微笑
史蒂文坐着一张桌子,占着一个空间,很是霸道,不许别人去坐。班主任麦妮尔小姐笑笑,竟然不加反对地答应了。
詹妮见了,很不高兴地大声喊:“史蒂文,你是撒旦吗?凭什么不许别人坐在你身边?”为了打掉史蒂文的嚣张气焰,也为了表现对史蒂文的强烈不满,詹妮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史蒂文的旁边,还对着他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一个鬼脸。
史蒂文气红了脸,大声警告詹妮:“詹妮,我以上帝的名义警告你,离我远点儿。”可是詹妮一点儿也不害怕史蒂文的凶相,还有他的那个全能的上帝,毫不犹豫地坐在了他的旁边。
史蒂文很无奈,一耸肩道:“詹妮,你-你会后悔的。”
詹妮却一脸的不以为然,说:“我不怕,我等着。”然后趴在那儿写起日记来。
詹妮的家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医生世家,她的爷爷奶奶是当地的着名医生,她的爸爸妈妈更是出名,开着自己的诊所。
詹妮因为这而十分得意,并且一边吃着比萨,一边还得意地介绍,她的爷爷最近研制出了一种新药,一种治疗艾滋病的新药。贝特听了,睁大了眼睛望着她,不相信地大喊:“詹妮,你在吹牛!”
詹妮并没有生气,仍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耸耸肩问道:“你凭什么说我吹牛?”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属实,詹妮当即和贝特打赌,让他去采访自己的爷爷。“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输了,你怎么办?”詹妮问道。
贝特皱着眉想了想,连说了三四种惩罚的方法,詹妮都摇头否定了。最后,詹妮自己提出了一条惩罚方法,如果贝特输了,他得在全班,甚至是整个校园中收回自己的话。
贝特笑笑,点着头答应了。
这次打赌贝特很显然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第二天一早到了教室,大家都在读书,詹妮就打断了大家的读书声,要都静下来听她说话。大家停下来,望着詹妮。史蒂文有些不满他的这个霸道的女同桌,瞪了她一眼。
詹妮一点儿也没把史蒂文的白眼放在心上,甚至还笑了一下,带着优胜者的得意问贝特:“你昨天去我家采访了吗,贝特?请你告诉大家。”
贝特站起来,失去了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灰溜溜地低着头轻声道:“去了。”
“我说的是假的吗?”詹妮稀疏的眉毛挑了一下问道。贝特忙摇摇头,表明詹妮说的不是假的。谁知道詹妮得理不让人,“别摇头,大声说出来,大家没看到,是吧?”
大家都喊一声“是”。这一刻,有一个声音颤抖着,也说了一声“是”,是史蒂文发出来的。
贝特很无奈,抬起头来大声告诉大家:“詹妮说的是事实,我去采访了詹妮的爷爷,詹妮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大家一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其中史蒂文拍得更响。
詹妮那一刻满脸阳光,得意地吹着泡泡糖。大家围着她,让她介绍那种药物,詹妮摇着头拒绝了,因为这种治疗还处于实验阶段,自己的爷爷还想申请专利呢。
贝特显然很生气,为这一次詹妮逼迫自己当众认错的事。贝特在班上是有名的学生头儿,啥时候伤过这么大的面子啊?
因此,詹妮越是要保密,贝特越是把消息暴露得更彻底。
原来,詹妮的爷爷是个着名的医生,退休后一直致力于艾滋病药物的研究,他从中国的中药中得到启示,采用多种中草药和化学品混在一起,碾碎之后制成一种药饼,绑在肚脐上,就能治愈艾滋病。
大家听到这样神奇的药物,都睁大了眼睛惊叫道:“上帝,怎么可能?”
贝特见大家不相信自己的话,很不高兴地一耸肩,抛出一个证据,自己亲眼见到一个患者来感谢詹妮的爷爷,因为詹妮爷爷的药饼治好了他的艾滋病。
大家听了,又发出一声“啊,上帝”的惊叹。
贝特很得意,“嘘”地吹了一声口哨,扬长离开,全然忘记了自己打赌的失败。而且,他还抛出了一个消息,詹妮在自己的文具盒里就藏着这样一个药饼。
就在这时,铃声响了,体育课开始了,大家一哄冲出了教室。
体育课上,大家玩得很高兴,忘记了一切,下课后才想起上节课贝特所说的话,都一哄跑到詹妮的课桌前,找到她的书包,打开文具盒,里面空空的并没有那个药饼。
詹妮知道了,瞪着贝特大声喊:“贝特,都是你说出来的吗?”
贝特一吐舌头,忙钻出人群跑了。大家都怂恿着,让詹妮拿出那块儿神奇的药饼来看看。詹妮找了一会儿没找见,拍着脑袋恍然大悟地道:“对不起,我已经拿回家了。”
大家听了,无精打采地回到位子上。下午,詹妮打开文具盒,里面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詹妮,谢谢你,还有你的爷爷。
这以后,史蒂文开始笑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凶人了,他就像一片阳光一样,走到哪儿都会给人带去一片温馨。大家都喜欢他,称他为“上帝的宁馨儿”。
史蒂文是带着微笑和幸福闭上眼睛的,他的肚脐上绑着一个药饼。
史蒂文之所以对大家凶,不让大家坐在他旁边,是因为他染上了艾滋病。在一次输血时,他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在医生那儿检查后,非常害怕,心情也越来越糟。
从此,整天,他都在灰色和痛苦中度过,性格变得越来越暴躁,人也越来越痛苦。
就在这时,詹妮的爷爷制造药饼的消息传出来,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听说詹妮的文具盒中有一个药饼,就悄悄趁上体育课时拿走了它,绑在自己的肚脐上。
当同学们再次回来,要看那药饼时,他又慌了起来,怕大家发现是自己偷了。就在这时,詹妮一句“我拿回家了”给他解了围,让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于是,他写了一张感谢的纸条放在詹妮的文具盒中。
面对着满面微笑已停止呼吸的史蒂文,全班同学都落下了泪。詹妮更是泪流满面,望着史蒂文道:“史蒂文,原谅我,我不该骗了你。”
史蒂文检查出艾滋病的同时,詹妮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史蒂文是在詹妮爸爸的诊所检查的。
詹妮的爸爸回到家里,很痛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詹妮默默的没有说话,当她发现史蒂文越来越暴躁越痛苦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主动和史蒂文坐在一起,并制造了一个谎言,说自己爷爷制造了一种药。她又怕大家不相信,就串通贝特,两人合演了一个双簧。
看见詹妮很难受,贝特红了眼圈劝道:“詹妮,你是对的,你没骗史蒂文,你以一个谎言给他带来了阳光和幸福,你这谎言是美丽的。”
其他同学听了贝特的话,也都流着泪点着头。
碾过青春的自行车
十七岁,我在小城读书。
我有一辆自行车,骑着它,穿过小城烟雨,还有青青的石板,小小的巷子,上学,或者放学。当然,有时,也会骑着它,在马路上飞奔,让一头黑发迎风飘扬。
可是,我的自行车,会经常跑气。
这时,毛小乐会骑着自行车,滑到我眼前,一脚点地,很阳光地一甩额前的黑发,喊道:“皮珊珊,怎么的,车子坏了吗?”
我会噘着嘴唇,站在十七岁的阳光下,很无辜地看着这个破车子,一脸沮丧。毛小乐就又笑了,他的笑很洁净,如一片冬日的雪花,据学校的女生透露,毛小乐的笑,至少在十几个女孩的梦中出现过。
然后,毛小乐又会很大方地说:“来,我带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