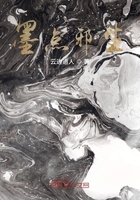任家济世堂,虽自前朝便在大理行医百余载,但其老馆主却是姓段,名曰段素履,其年岁已不可考,相传乃是当年大理国皇族后裔,后经朝代兴替,沦落至此。
相传这段素履本非济世堂中人,本朝初年曾在太和县中开办武馆,后经太祖禁武令后,各地武馆多数被封,而段老爷子失了饭碗,便被其长婿弟子任天佐接至济世堂中赡养传武,并尊其为老馆主。
且说段素履在大理行医授武数十年,也颇有些名望,周边老辈对他皆赞誉有加。只是近些年中,老馆主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不问馆中诸事,久之已遭乡民淡忘,唯太和县与大理城中尝有老者,可偶尔见其身影。
早在数月之前,任家便有言道老馆主正在闭关修炼,静处房中深居不出,故馆中新入弟子如杨坎、小皮等,也仅是听闻事迹,却未尝见其真容。
今日馆中忽有传言,道是老馆主已然出关,又于昨夜亲自指教馆中学生,而馆中弟子多数并未见过老馆主几面,故此番消息传出,众人亦是议论纷纭。
今日上午,老馆主依旧没有露面,众弟子还满心期许他能来指点一二,此时不禁失落不已。而杨坎虽是知晓此事来龙去脉,却也只在心里暗乐,并未告与他人。
午休之时,杨坎便去老馆主房中觐见。其实昨日在大理城中见得老馆主者,还有小皮一人。杨坎本想喊上小皮同往,但不知为何,今日小皮忽然告病未来馆中,杨坎也就只好作罢,只是心中奇怪,为何小皮师兄昨日还是活蹦乱跳,今日却突然害病无法前来。
见得老馆主只好,杨坎笑颜参拜。这段素履倒也不是拘于礼教之人,抬手便让杨坎起来,而后探身说道:“小伙,我听我那徒弟说了,你叫杨坎是吧?”
杨坎揖手回道:“正是弟子。”
“诶嘿,你这小子,我今天早上才想明白,我昨晚是不是进了你的套了?”
杨坎笑道:“师尊说笑了,弟子真心想在任家学艺,而前辈也是师道尊严,诲人不倦,见得弟子好学,自然肯传授些武艺,哪有什么套不套之理?”
“哈哈哈哈,好你个巧舌如簧。”老馆主大笑道:“也好,既然你已拜入这济世堂门下,那我段家武学之中,你想学什么,我便教什么,至于你能否学会,那我就不管啦。”
“咦?师尊既然姓段,那你所授武学传入济世堂中,又成了任家武功?”杨坎话说一半,又将后半句生生咽了下去,乃是心中想到,若真是任馆主习得段老前辈武功,再将其易作任氏绝学,那岂不是欺师灭祖之罪?倘若自己如此说来,又有离间师徒之嫌,倒不如闭口为妙,以免多生事端。
却听老馆主笑道:“这有何奇怪的,我教的是我段家功夫,他教的是他任家功夫,这当然不一样了。”
“那你们所授武功也是不一样的?”
“那是自然。”老馆主笑答:“我曾在此地开设武馆,欲将祖宗所传武艺教授众人。可我段家功法皆是阳春白雪之流,寻常之人若无些许内功造诣,学之难如登天。而任天佐跟我学了一十二年,方略微窥得门径,又经他数年苦修,才将其化为己用。”
老馆主口中说着,脸上满是赞许之色:“我段家武功经他这么一改,削减了调气内修之法,补以身形手势之变,虽是力不如前,却巧变更甚,便是市井众人,亦可修习。自皇帝禁武以来,他在济世堂中以强身健体之名传武,也算能保我段氏武学不息了。”
杨坎闻言方悟其传教不易,心中感慨,问道:“那不知师尊都有何种武功可以传授?”
段素履笑答:“我段氏武功,皆以实战为先,决无花巧,可以隔空指力,伤敌于十步之外,尤以前朝先祖创有‘一阳指’绝学,玄异非常,乃是一指制敌之法,你可要学它么?”
杨坎教老宗主说得心动不已,刚要开口承应,忽又想到前日沐讲禅师所谏,道是自己内功不济,若是一昧修习招式,无非舍本逐末之举。况自己本有上乘剑法傍身,既然手有兵器,又何必去学什么拳脚功法?
于是,杨坎拜谢道:“师尊好意弟子心领,但前辈门下神功,只恐在下资质愚钝,不胜教化,实在不敢窃学,只愿师尊肯授弟子内功运行之道,好以足履实地之后,再学招式。”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小子机灵。”老馆主大笑道:“若是寻常小辈,都是贪图神招奇法,却不屑埋头筑基,最后一事无成。我昨晚交手之时,试过你身上内力,若按你这等修为,想学我‘一阳指’来,是要难过登天啊。”
杨坎心中窃喜,暗笑道:“弟子多谢师尊谬赞,其实弟子也是受得高人点拨,才能有此觉悟。”
“哦?我就说你这剑法使得诡异,果然有人指点,不知你是哪位高人徒下?”
杨坎答曰:“弟子不敢妄称师徒,只是前些时日沐讲禅师云游至此,在下得幸能与他研修几日武艺,故有所悟。”
“哎?沐讲禅师!”老馆主奇道:“可是那个打虎的沐讲禅师?我虽未曾与他交手,倒也知道他是个厉害人物,怕是我那两位徒儿联手,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杨坎惊问:“禅师如此厉害?连馆主兄弟二人齐上,也不能匹敌?”
“我那徒弟闯荡中原之时,打的多是些二流高手。而那和尚本是默默无闻之徒,好似二十年前突然冒出来一般。与他交手之人均有言称,这和尚武功不弱少林、武当顶尖好手,怎是我那俩徒儿可比的?”
杨坎全然不知沐讲禅师竟然如此厉害,一时惊得张口无言。却听老馆主继续说道:“既然沐讲禅师让你先学内功,应是有他道理,不过那老和尚为何不自己教你呢?”
“回师尊,禅师当晚所言乃是他所修内功太过刚猛,而弟子并无内功根基,学之有害无益,故未授与在下。”
“原来如此。”老馆主眯眼学想了片晌,便拍着身旁座椅,向杨坎招手道:“来来来,坐到这边,让我来给你号号脉。”
杨坎不明所以,便走到椅边坐下,将左手抬放扶手之上。老馆主信手三指搭在杨坎脉上,口中喃喃自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将手拿开,口中说到:“好了,我明白了。”
“不知师尊号出什么结果?”
老馆主笑道:“嘿嘿,那老和尚说得没错。我刚给你诊脉之时,发现你是阴寒之体,所修内功也应以阴柔为佳。若你真的强学了什么至刚至阳的功法,事倍功半不说,倒怕要了你的小命嘞。”
杨坎闻言,方觉后怕,自言自语道:“想不到修习内功还有如此讲究,弟子也是头回听闻。”
老馆主继续说道:“这内功阴阳之论,乃是由我所创,武林之中尚无人钻研,故你不知晓它,倒也无怪。记得我父亲曾收治一位病患,乃当时丐帮帮主,便是以其阴柔之身硬学了一路阳刚掌法,以致双臂瘫痪,险些丧命。好在先父通晓阴阳之法,为他开处调阴补阳之药,方才有所补救。”
“那敢问这阴阳之论当作何解?”
老馆主答曰:“世人皆分阴阳太极之体,武功亦如是。若论体内寒热之气之强弱,周身经脉之盛衰,乃是人各有异。而各路武功运行之术,内息调用之法,亦是大相径庭。故而有些功法,可为此之甘饴,彼之毒药,其原因皆出于此。”
杨坎闻言顿悟道:“原来武功运行之理,竟藏如此玄妙,真是武道高深,难攀莫测。想必若要运用段家绝学,非要先精通段家内功不可吧。”
“这也不对,其实我段家绝学与我本门内功并不相合。且拿这‘一阳指’说吧,乃是以阳刚之气集于指尖而发,可我段家内功又是阴柔驭气之法,故自此武功创立以来,段氏非内力雄厚者,练成之人寥寥,倒是天龙寺众高手辅以他们寺中功法,精通之人反胜我段家更多。而一阳指练至高阶,化气为剑,又成了一门阴柔武功,如此阴阳互转,非内功大乘者不可修习,故而百余年来,达此境界者仅有寥寥两三人耳。”
杨坎听得仔细,道:“如此说来,段家内功既是阴柔功法,那我可学得吗?”
老馆主笑道:“我这路内功你自然可学,但若你以后使的都是剑上功夫,只怕我这内功对你无多助益嘞。”
“师尊此话怎讲?”
“我段家内功,名曰‘正经六合功’,其要义乃是调和经脉,内气外发。若你使的是内家拳法,若运行此功,则使拳掌之风威力倍增。但你若用剑法,则仅作筑气之用,并无增辉之效。若如此,你还肯学吗?”
杨坎稍加犹豫,回道:“弟子愿学。”
“也好,以你这般体质,修习此门内功倒是有益无害。这样吧,我来将此功法口诀传授于你,你且好生记住。”
说罢,老馆主便将正经六合功的口诀纲要,细细述来。杨坎在旁静听,待他说完一遍,已是记得七八分。老馆主再念罢一遍,问得杨坎已然记住,便对他详叙其中道理。
原来,这正经六合功乃是调行真元,贯通全身十二正经离、入、出、合之气,是以十二经脉,两两对称相合,其中手太阴肺经、足厥阴肝经为一合;手阳明大肠经、足少阳胆经为一合;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为一合;足太阴脾经、手厥阴心包经为一合;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为一合;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为一合,真气通注,周而复始,如环无端。
杨坎盘腿而坐,依照内功口诀,闭目调行周身真气,似觉一股清流自丹田之中沿奇经八脉循环相注,心中大喜。可他如此稍一分神,便使体内真气顿时消散无踪,再也调行不出,只好睁眼向老馆主道:“禀师尊,弟子方才感觉经络之中有真气流动,但未过多时,便忽地没了,现在无论弟子如何运功,也无济于事。”
老馆主笑道:“你练功之时,喜形于色,像你如此分神,真气不散才怪嘞。而你本无内功修为,真气散了便是散了,须再等上几个时辰方能重新修炼。”
杨坎怅然问道:“那师尊,如此说来,我现在岂不是练不得内功了?那敢问弟子如何才能修炼内修呢?”
“这内修可不是刻意修炼而成,而是在你打坐调息、调行内功之时,使得经脉之中真气相流相生,循环往复,便可有所增益。因此,只消你每日勤习内功,真气修为自会增长。”
杨坎忙揖拜道:“谨遵师尊教诲,弟子一定勤修苦练,顿学累功。”
老馆主摆手道曰:“这内功虽要你每日修炼,但若练得太多,便是有害,只需一日再习即可。倘若你调行真气之时,运行过快,以致真气流错了经脉,应当立即停下,否则要走火入魔,轻则伤身,重则毙命,切记,切记啊。”
“弟子谨记于心!”
待二人授业完毕,杨坎谢过师尊,出门之后,不觉间已是下午。此时,院中习武弟子早已各自回家,院中仅有马教头一人独自练拳。杨坎想起今日去老馆主处求教武功之前,并未告知教头,怕他责骂惰怠之过,便贴着墙边,欲悄悄溜去前院,却不料还是被马教头瞧着了。
只听马教头唤杨坎道:“杨慕云,你给我过来。”
杨坎“喏”了一声,低头走来,又听马教头训斥道:“呔你这懒散小子,今天小皮猴子没来练拳,你下午也不来了。你且说一声,可是不想在这学拳了,我这便禀告师父,送你回唐门去。”
杨坎忙解释道:“教头息怒,弟子今日与老馆主有约,受他指点武艺,一时忘形,未有通报教头,还望恕罪。”
“哦?师公能亲自教你功夫,你这小伙福分不浅啊,他都教了你什么?”
杨坎回道:“禀教头,老馆主所授武功乃是‘正经六合功’,但在下愚钝,还未通理清明。”
“咦?这可是师公门下内功,若按常理来说,须在馆中学艺两年才可修习内功,而你这小伙虽有些功夫底子,倒也不至能有两年功力,奇怪,奇怪。”
“弟子不解何来奇怪之有?”
马教头回道:“这内功可非一般招式即学即用,就算练上一年半载也未必能有成效。故我门下弟子须要先学两年拳脚,简其心性善学者再授内功,以免其久日不见功力长进,而自行荒废。可你这小子初来乍到便能学得师公武艺,想必师公是慧眼识才,你可莫要辜负了他。”
“弟子定当每日勤修,朝乾夕惕。”
马教头又将修炼内功之时,时辰、风水之选,子午打坐之法,以及对此内功之心得要义,述与杨坎,而后便对杨坎说道:“既然能得师公如此看重,你可不要像前些日子一样敷衍了事。”
杨坎谢过教头,便辞去回房了。
当夜子时,杨坎卧于房中,听得馆外打更声起,起身见同榻师兄均已安睡,便爬下床来,走到院中天井打坐运功。当是时,夜深人寂,万籁无声,杨坎静坐院中,凝神调息,重新调行丹田真气,引入经脉之中,循环流通。
运功之时,杨坎虽不能内窥其貌,却能隐约感到真气以经脉六合之序,遍流周身,恍然有神清气爽,灵台明净之感,顿觉此功之法,妙不可言。
然而,杨坎心中虽是又奇又喜,但念及今日午后散功之事,断不敢妄分心神,只能每每察觉心猿意马之时,强行扼念凝神,以保内息延绵。
杨坎在院中打坐修炼,已是过了些许时候,直到丹田之中再无真气聚出,方才停止。运功完毕,杨坎起身吐纳,略微舒活几下筋骨,只觉清风飒来,怡然自若,飘乎有凌云之意,仿佛拳脚之上亦有平添几分劲力。
内功练罢,杨坎小欢颜悦,颠步漫回房中,想及日后功力大成之景,至乐而笑,倒在床上,左右翻滚,折腾许久才入眠去。
次日,馆中习武弟子依旧早起练功。杨坎昨日新习得内功,本想今天向小皮显摆一番,却不料他却依旧告病未至,也就只好作罢。
正当后院众人练武之时,忽闻前院之中人声嘈杂,而后便见任天佑领有一队捕快,鱼贯跑入后庭之中,对马教头耳语几句,让他遣散练功弟子回房静候,然后便去各房搜证。
杨坎等人一头雾水,只好回往弟子居中相待。过了约莫一个时辰,便有捕快进入房中,依次带房中弟子单独审讯。
轮到杨坎之时,只见两名捕快将杨坎带入花厅,问他昨夜凌晨所做何事,有何见闻,并有吏员在旁书记。杨坎一一据实以答,而后便被喊出去了。
午后,杨坎练完内功之时,院中捕快皆已返回大理府,馆中各位弟子也就照常习武。可正练得一半,又见任天佑跑回馆来,唤杨坎过去,道是馆主相找。杨坎不知所为何事,便跟着去了。
二人回到正厅之中,只见馆内诸位长者与大理捕头同坐其中,面色严肃,似有大事发生。杨坎虽自觉并未做得什么错事,但偏偏只有自己被带到此地,心中不免有些发毛,正欲开口询问馆主为何传唤,却听任天佐先行说道:“你先坐下,我与你有要事相谈。”
杨坎搬了个凳子坐于门边,问道:“馆主唤晚生前来,可是馆中出什么事了?”
听得任天佐开门见山道:“馆中昨夜失窃,你可知晓?”
杨坎惊道:“何时失窃?晚生不知!”
又见李捕头倾身问道:“我们知道不是你干的,但你昨夜睡得最晚,可曾看到有什么外人潜入馆中?”
杨坎答曰:“在下昨夜子时在后院天井打坐练功,并未见有外人前来,也未尝听有什么动响。”
李捕头转头问馆主道:“你门下这小伙可信得过?”
“可信。”
李捕头闻言,点头道:“若那打更之人言亦属实,便是有人在子时一刻潜入馆中前院偷盗,并且此人轻功不错,落地无声,才未让人察觉。”
“敢问馆中是丢了什么物事?”杨坎问道。
“我正要说,你前些日子从唐门来时所带毒方,我们尽倾馆中人手,已对其毒理析明大半,而其解毒之法也近完成。可昨夜忽有盗贼,将毒样与毒理札记一并窃走,以致我等前功尽弃。”说着,任天佐叹道:“唉,我本道大理乃太平之地,久疏防范,以致出此纰漏,惭愧,惭愧。”
杨坎皱眉道:“如此说来,若馆中未有什么值钱物件失窃,便是说明此贼应为唐凌同伙,乃专为盗毒而来。”
“不错。”李捕头说道:“你从唐门送毒之事我已听说,方才我曾在此排查,道是此毒送达之后,馆中知情人氏均未向外透露风声。那唐家托济世堂解毒一事,都有何人知晓,你又同何人说起过?”
杨坎思索片刻,回道:“据我所知,此事仅有唐家宗主和几位宗亲知晓,而唐门肃反平乱之事,他们均有参与,故不可能是他们所为。而我来到大理之后,仅同馆主说过此事,对于他人概未提及。至于消息从何走漏,在下也不清楚。”
杨坎说罢,众人默然沉思,过了片晌,听得任天佑问道:“若你与唐家众人均未说起,那莫非是我馆中出了内鬼?”
“不会。”只听任天佐道:“馆内郎中皆是我一手带出,在此待了少说也有七八年,怎会是什么内奸?这应是其他什么时候出了岔子。”
“其他时候……”李捕头托腮想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问杨坎道:“这小伙,你从唐门来时,路上车夫可是唐家中人?你送毒一事他可知晓?”
“那人倒并非唐家中人,但我只对他说往任家送些珍奇药材,并未谈及毒药一事。”
李捕头抬手将腿一拍,说道:“那便是了,唐门窃毒之时刚被查获,便有人往任家送药,就算那车夫不知你所送何物,若他真是反贼,也当猜得出的。这样,你将那车夫姓甚名谁,何处人氏,有何相貌体征,统统说来。”
杨坎苦笑道:“我自来到大理已有半月,那车夫名字相貌哪还记得清楚,也就记得那人姓廖而已,家住四川,其余全不知晓。”
“这倒也是,那这样好了,你随我去衙门之中,将你心中映像画影图形,或许能有线索。”李捕头说罢,便向馆主等人告辞,带着杨坎往大理城去了。
二人来到府衙之中,李捕头便将杨坎安置幕厅,让他将那车夫相貌细细说与画师。杨坎本就对那车夫无多印象,也只能将其五官说个大概,待那画师成图之后,其人像果乎泯然众人,难以查询。
李捕头捏着画像,拧锁眉头看了一会,摇头叹气,便将画像放回案上,再问杨坎几个问题,均无所获,只好说道:“罢了,看来你这也不知道什么了,那你先回去吧。”
杨坎辞过捕头,便往太和县去了。途中,杨坎仔细回想来时往事,愈发感到蹊跷。按说那盗贼潜入馆中,径直便去取那毒样,若非熟悉医馆地形者,怎能如此驾轻就熟?而若真是当然那车夫所为,他又未能进得医馆,怎能对馆中陈设了如指掌?又或是那车夫传出信来,令其同党去任家踩点,再到夜里翻墙偷盗,可毒样配方据称藏得隐蔽,他又如何知晓其所在何处?
杨坎思来想去,毫无头绪,不知不觉便已走回馆中。进门之后,只见任天佑侧立照壁一旁等候,见得杨坎到来,即将他再行领入正厅之中。
入了正厅,此回仅有馆主一人,只见馆主取出两封书信,并将其中一封交与杨坎道:“慕云贤契,现今门中失窃,毒样药理尽失,我刚才已将此毒毒理与拟推解毒之法写入信中,你且速回唐门,将此信交与唐氏宗主,并告以失贼之事,向他再请一份毒样送来。”
杨坎接过信道:“晚生领命。”
接着,馆主将另一封信交至任天佑手中,道:“天佑吾弟,现今我任家与世无争,如今门中遭窃,恐我等解毒之事已遭歹人盯上。你且尽速赶赴成(防屏蔽)都,将此信送至分馆之中,让他们好生防范,然后留在成(防屏蔽)都看守分馆,直至解药调配完毕,再回来复命。”
任天佑奉信领命,便问兄长道:“那我们何日出发?”
“事不宜迟,今夜就走!”
说罢,任天佐给二人分发了些许盘缠,即令他们前去收拾行李。待到两人整罢行装,已近黄昏,馆主设了薄宴为二人饯行,晚饭过后,杨坎辞别馆中众人,便去驿站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