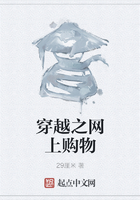“我是你的初恋吗?”方夏眼睛还望着桥下。“是。”苏凉回答。“我不信!”方夏直视苏凉的眼睛说,“你连想都没想就回答!”苏凉说:“就因为没恋过才不用想啊!笨!”“说的也是——”方夏连反应迟钝也可以很诱人,“但是,你怎么可能没恋过别人?”苏凉反将一军:“你肯定恋过别人!”方夏投降似的摆起双手:“没有!绝对没有!”“那你又为什么?”苏凉追问不过是想欣赏方夏的窘态。“我——”方夏认真地想了想,“我可怜你!”苏凉坏笑:“真敢吹牛!嘴大还真把自己当舒淇啦?是没人敢追你吧!”——“烦你!”方夏笑过,眼神突然温存起来,“凉凉,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苏凉愣了一下。
方夏捋着苏凉的长睫毛,说:“你是为我从天而降的,你让我觉得安全。”——安全,这是个让苏凉爱恨交加的字眼。方夏捣蒜似的点头:“当然是真的,你怎么了?”紧接着,她被苏凉揽入怀中,脸紧贴苏凉的胸口,苏凉说:“我永远不会丢下你,我跑得足够快,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马上跑去接你回来。”方夏抱着苏凉,手心轻拍着他的背:“乖啦,答应我,以后有任何不开心都要跟我讲,听到没有?”苏凉的背抖动得更厉害,方夏从他怀里钻出来说:“你等我一下。”转身向天桥另一端跑去。
“苏凉,你能听到吗——”
“能——”
“我们之间隔多远?”
“五十米。”
苏凉仅仅是望一眼,他对距离的敏感度异于常人。
“你会跑过来找我吗?”
“会。”
“五千米呢?”
“会。”
“五万米呢?”
“会。”
“如果我丢了呢?”
“我就跑遍整个世界找你。”
“怎么找?”
“赤道才四万公里长,我跑完一个赤道的距离,就等于绕了世界一周,不信找不到你!”
“苏凉——我喜欢你——”
方夏狂奔过来,一下跃进苏凉怀中,忘了苏凉的断腿,险些撞他一个趔趄。方夏咬了一下苏凉的耳垂,苏凉怕痒,脖子直往回缩:“总算找到我了?我有那么难找吗?”方夏点头,说:“当你从天桥上跳到我面前,我就一千个、一万个确信,苏凉,就是你!”方夏搂在苏凉脖子上的胳膊收得更紧了:“你之前都躲到哪里去啦?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距离高考还有四十六天。
苏凉如愿以偿地睡了个安稳觉,前所未有地踏实,连闹钟都没听到,没想到是被烟味儿呛醒。星期六,苏凉都睡忘了。
苏凉单腿蹦至客厅,被阳台上的苏敬钢发觉。苏敬钢抓紧猛吸了一口,把烟头儿弹出窗外。“少抽点儿吧!没摔死算我命大,别再被你给呛死!”苏敬钢骂:“满嘴放屁!”说罢进了厨房,仍撒气似的说:“睡到这个点儿,吃的叫个啥饭!眼瞅就要高考,跟没事儿人一样!”苏敬钢做饭的手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娴熟的,父子俩谁也记不起了。在苏凉印象中,苏敬钢在他十岁以前从未踏进过厨房一步。苏凉十岁之前,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在。
“凉凉起床啦?”厨房里居然应景地响起女声,周晓燕裹着长身围裙走出来,“听你爸说把腿给摔了,我前几天刚去外地跑了个活儿,才腾出空来看你。”“你燕子姨特地过来给你做饭,不会说声谢啊?”——“就你臭规矩多!凉凉跟我还用客气?”周晓燕说的不假,这个家里的厨房,她进进出出足有五六年了,除了父子俩的胃,连这大小俩孩子的脾气也早给她摸透,“姨给你烀了鸡腿,吃啥补啥嘛,”周晓燕逗得自己“咯咯”地笑,“还闷了一锅排骨,等下炖酸菜。”
门铃响了,苏敬钢去开门。
“我们看苏凉来啦!”徐大疆拎着两大兜子水果,臃肿的身躯快要挤破苏凉家门——我们?苏凉正好奇,一个活蹦乱跳的身影从徐胖子身后蹿出来,是方夏。
“叔叔好!特地来吃你煮的面!”方夏从不吝惜自己讨人喜欢的天赋。苏敬钢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苏凉,说:“进来坐吧,他都快憋疯了。”苏凉盯着方夏问:“你怎么来了?”方夏反问:“闻着你爸做菜的香味儿就来了,不欢迎啊?”她一屁股坐在苏凉旁边,动作娴熟如同自家沙发。“她非逼我带她来!”徐大疆把水果往餐桌上一撂,“我就说你欢实着呢,用不着看,你们俩从周一看到周五还嫌看不够啊!”——“嘘!”苏凉惊恐地朝厨房指了指,徐大疆反应了足有三秒才闭嘴。
周晓燕从厨房出来,解了围裙说:“都是凉凉同学吧?正好,盛出锅就吃!”周晓燕忙不迭走到门口换鞋,苏敬钢闻声从厨房出来:“你咋能走?一块儿吃!”“马上交班儿了,我得取车去,你们爷儿几个吃吧!”周晓燕冲一客厅人笑笑,挥挥手带上了门。
“燕子姨再见!”方夏跟人自来熟的本事在苏凉看来简直像特异功能,他费解地盯着方夏,方夏不解地问:“你看啥呢?”“没啥。”苏凉又是不怀好意地笑,笑得方夏直恼。苏凉说:“叫得还挺亲,知道燕子姨是谁吗?”“燕子姨就是燕子姨呗!”方夏没头没脑地说,“是谁啊?”苏凉笑得狡黠:“我爸的老相好儿!”方夏懒得再听苏凉胡扯,屁股一扭,身下的沙发发出“咯吱——”一长声,低沉、闷涩,像一个老灵魂在悲叹自己的身世。
苏凉尴尬地笑说,这沙发太旧,打我记事儿起就没换过。
“二十多年的老房子,让你笑话了。”苏敬钢抹着手从厨房出来,冲苏凉使了个眼神说,“带人家随便看看。”苏凉指着自己的房间,自嘲说:“可触摸,可拍照,还不要票,就是比博物馆小那么点儿。”
方夏伫立在高过自己许多的书架前仰望着,感叹:“你有好多地图册啊,还有这么多摄影书!”她随手翻开一本摄影集:“你喜欢照相?”苏凉叹气说:“一直没机会学。”方夏见到占据了整面墙的钢琴,惊讶地问:“你会弹钢琴?”苏凉说:“我妈留下的。”方夏掀开琴盖,琴键一尘不染,问:“有爱听的曲子吗?”苏凉摇摇头。方夏坐下,想了想,随手弹起,哑了十年的钢琴瞬间走出悦耳的调子。
一顿饭,一直吃到天黑。苏敬钢借个幌子出门,留下三个孩子边吃边聊。方夏和苏凉整晚斗嘴,徐大疆坐一旁听着取乐。等苏敬钢遛完弯儿回来,他坚持要送方夏和徐大疆下楼。
“我想带苏凉出去走走。”方夏冷不防冒出一句,“叔叔放心,我保证把他完好地送回来,不对,是保证另一条腿还完好地送回来!”
苏敬钢算是默许,眼神里却在对苏凉下着限时令。
即便是卧在苏凉怀中,方夏仍拿捏不准这个男孩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
“知道我为什么跑那么快吗?”
方夏蜷起身子,苏凉怀抱着她,一路暖到胃里。沉积的回忆泛起,将他拉回十岁那年的某个夕阳下:苏凉放学回家,妈妈坐在卧室床边,穿戴整齐,她看苏凉时,表情怅然。苏凉向妈妈怀里跑过去,跟平日一样,结果苏凉摔倒了,是被一个硕大的旅行包给绊倒——苏凉再熟悉不过,自己更小的时候,每次在家跟妈妈玩捉迷藏,瘦小的他最爱钻进旅行包里。妈妈每次都假装找过好半天,最后才打开旅行包的拉链——小淘气原来在这儿呢!然后双手将苏凉拎出来,抱在怀里亲个没完。
“凉凉,笑!”
那是母亲跟儿子之间的暗号,只有等他开心地笑出声来,母亲才会放他下来。
苏凉的双手在空中比划着,仿佛正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动作那么逼真。方夏鼻酸,她感觉越是抱紧苏凉的腰,越在贴近一种不安。
“我有预感,她要走。可我并不难过,我以为那个大包是用来装我的。”苏凉对着夜空说,“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保温桶。”小苏凉紧抱着红色的保温桶,妈妈替他拧开盖子。“妈妈给你煮的面,快吃吧。”苏凉没有吃,尽管那味道早勾得苏凉口水上涌,可他就是忍住没吃。
四月的夜风仍微凉,苏凉咳了一声,被方夏裹得更紧。
他接着说:“她坐在出租车后排,回头望着我,可我就是追不上,我身上还背着沉得要命的书包,那天刚好放暑假,整个学期的书都装在里面。我把书包扔在了路上,腿又开始不争气,酸疼、发软。我感觉自己的肺要炸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快死了,她从后车窗看着我,可我却看不清她的表情。我跟着整街的车跑,停下来时,已经到了火车站。站前全是赶路的人,个个高大过我,我看到那个熟悉的旅行包在人群里来回地穿梭,最后不见了——我该怎么回家?我脑袋里第一个冒出的居然是这个问题!天黑了,我反倒不害怕。我当时不知道离开家有十几站远了,我敲了敲腿,还是没知觉,不如跑回去吧。于是我就开始跑,呼吸再不像来时那么困难了,大概因为肺被我跑没了吧,像书包一样没了。到了家,我又一口气跑上六楼。门没锁,我爸正坐在客厅里抽烟。我扑倒在门口,晕过去了。”
方夏泪流满面,她从未听苏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他啰嗦得像个八岁孩子,此刻,他也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孩子。
“那碗面后来吃了吗?”方夏擦着眼泪问。苏凉说:“醒来的时候,我爸端给我一碗汤面,可究竟是不是我妈留下那碗,我从没问过,不过从那以后每顿饭都是我爸做的。”
假如拥有和失去平均分配着悲伤,似乎悲伤也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
方夏从书包里掏出一支黑色马克笔,在苏凉的石膏腿上写字:40075.7,然后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苏凉会心一笑,这是赤道周长的公里数。
“你这条腿啊,赶快给我好起来!”方夏欣赏着自己的签名,“你还有这么长距离要跑呢!”
“凭什么?”苏凉反问。“不是你说要跑遍全世界找我吗?这么快就想反悔啦?”方夏紧咬着唇,露出兔八哥一样的板牙。“我是说,假如有天你真丢了,我才会跑这么长的距离找你!”苏凉捏起方夏微扬的下巴说,“想跟我玩失踪?”认输吧方夏,你就是这么怕苏凉失望,那么轻易就被苏凉凝望自己的眼神俘获。痴迷,原来就是让人连照镜子时,看见的都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