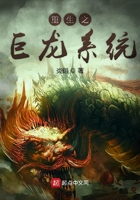冯劲的左手插在雪堆里睡了半宿,食指跟中指被冻成两条黑紫虫子,送到医院,大夫说治不了,只能切。冯劲不甘心,1987年初多次奔赴北京各大医院拜访名医,诊断结果都是一样,只能切。冯劲不忍,继续死扛,直到儿子冯子肖办满月酒。当晚,他散金大摆筵席,醉到不省人事前一刻,古怪兮兮地对苏敬钢和大昆说:“信不信我敢把自己手指头掰断?”——“吹牛!”大昆哈哈大笑,“你要是敢掰,我管你叫爹!”冯劲嘴角露出一丝诡笑,右手攥紧左手两根僵死的指头,使寸劲儿一撅——“你疯了?”苏敬钢阻拦不及,一股鲜血从冯劲虎口中喷涌而出,直蹿上棚顶,三人抬头仰望,扎眼如雪地中盛开出一朵红玫瑰——“叫爹!”冯劲狂笑不止,大昆愿赌服输,应声跪地,磕头叫道:“爹!”冯劲满足地答应着,用滴血的右手逗弄起摇篮中小冯子肖肉肉的脸蛋儿,得意地说:“儿子,这是你大昆兄弟!你抬头往上看,那是爸爸给你放的礼花,庆祝你满月!”襁褓中的冯子肖咿咿呀呀地叫着,一对儿澄净的大眼睛紧盯着头顶那朵红玫瑰,咧嘴笑起来。
三年夜大毕业,左娜如愿进了办公室做工程师。可干了不满一年,左娜便明白了工程师的身份已再不值得她骄傲。一年中,办公室里几名年长的同事纷纷停薪留职,下海做生意:有人去批发市场卖服装,有人开了小饭馆,还有人干起私营五金店,从原来的同事摇身一变成了客户。其中不时有人返厂请老同事吃饭,他们大多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常常在饭桌上把厂长刘决胜撑得三句一夸人家“有良心、重情义、不忘本”。
左娜向来对人情世故迟钝,却也终于觉出,世道真的变了,自己俯首贴案画大半年图纸赚的工资还不够付人家一桌饭钱。
西元1986年的夏天,左娜怀孕了。在此两年前,这座城扩修主干道,大西菜行作为青年大街沿途最煞风景的老、旧、破,拆迁首当其冲。两年后,第一批回迁的居民中,苏母有幸分到一栋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刚好苏敬钢跟单位借的小单间到期归还,他便带着左娜搬回大西菜行和母亲住到一起。苏敬钢本想借此缓和婆媳关系,毕竟自己时常出差,能有个人在家照顾左娜也好。
大西菜行历经岁月摧残的老平房,就在挖土机铁爪的一抓一放间烟消云散。一排排拔地而起的灰土色楼房如整齐划一的火柴盒,将半个世纪的人情冷暖排列得恰如其分。一些彼此做了半辈子邻居的老人们开始彻夜难眠,睡前听惯了隔壁夫妻十几年的对骂,吃饭前闻惯了对门儿蒸的苞米面饽饽香,现在闻不到也听不到,睡觉吃饭都不香了。他们是岁月的遗腹子,一心不二地苦苦侍奉着岁月,却永远搞不明白,岁月从不顾任何人的死活。
苏敬钢拉着左娜出门买菜,穿梭在千篇一律的楼宇间,一瞬间觉得这片生养自己的地方竟陌生得可怕,几次走乱了方向。曾经的胡同儿不复存在,就连供养过此地两代人吃喝的圈儿楼也被贴上了封条,不知何时又将化作另一堆尘土。小夫妻走到大棚正门,驻足猜测,脚下大概就是二人以及冯劲、大昆共同长大的那条胡同儿口吧?却谁也不敢肯定。幸好,尚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如磐石一尊,静立在街角处——那是老王道士、酒鬼老王头儿、王大爷——大西菜行久历风霜的活坐标,过眼云烟的守陵人。
“王大爷!”苏敬钢激动得如见亲爹,“还在这儿呢!”
“三驴子?”王大爷老眼昏花,认了足足半分钟的亲,才笑开一口镶牙说,“就算他们把路牌全拆光,我也不带挪一下屁股的!”王大爷支开一张小叉凳,苏敬钢让给左娜坐,自己立在一旁,四下环视过说:“这就是咱那条胡同儿口吧?”王大爷点点头,颇有些得意地说:“前年拆迁,我在屁股底下埋了俩铜钱儿,回迁第一天,我掐指一算,就搁这位置上一坐,往地底下挖了两尺,你猜咋的?俩铜钱儿连铜锈都没来得及生呢!”王大爷玄乎的口吻如往日一般传神,苏敬钢听得一脸惬意,时光仿佛在眼前倒退回了十八岁。他轻抚着左娜的背,对王大爷说:“我和小娜结婚了。”“喜事儿啊!我得给你俩瞧瞧!”王大爷一双老掌握住左娜两只嫩手,嘴里不停重复道,“大喜事儿……”苏敬钢心喜,说:“结婚时正赶上拆迁,老邻居一个都找不着了,我欠王大爷一顿喜酒,赶明儿我单独请爷们儿去鹿鸣春喝!”王大爷摇着头说:“爷们儿戒酒都八年了,忘啦?——我说的喜事儿不是指结婚,是小娜有喜!”苏敬钢大惊,忙蹲下身说:“你真神了!王大爷,你快帮咱俩好好瞧瞧,这回能保住吗?”王大爷不慌不忙地说:“把你手也给我。”苏敬钢两掌朝上伸出来,王大爷托在双膝上,瞬间瞪大的一双老眼扯平了刀刻似的鱼尾纹,摸着苏敬钢右掌心里那骇人的“人”字疤,慨叹道,“你这命啊……被你自己给破了。”苏敬钢大惑不解:“啥意思?”王大爷望着苏敬钢,故弄玄虚说:“孙悟空改生死簿,阎王爷也罩不住!这辈子的路咋往下走,全仗你自己了。”苏敬钢显然不太在意,却焦急追问:“孩子呢?手相能瞧出来吗?”王大爷淡然地说:“不用瞧,这个小老三啊,跟你这个老三前世有缘,命中注定是要做爷儿俩的。”
此刻,左娜呆坐在一旁,哑然。
她心中慨叹:莫非王大爷当真神人?小半年里,左娜先后两次意外流产,无一不是天灾人祸。左娜激动得两手颤抖,目光晶莹地问:“这孩子真能保住?”王大爷松开夫妻俩的手,神情泰然地说:“或讨债或还债,无债不来;或孽缘或善缘,无缘不聚。这孩子前世跟你们夫妻结的是善缘,不过人家是来讨债的债主,你们想撵还撵不走哩!”“是儿子?”苏敬钢两眼放光。“嗯,是儿子。”老大爷眯着眼点头。苏敬钢起身,掏出一百块钱往王大爷手里塞,王大爷死命推辞:“你俩的爹办白事儿哪个我也没凑上份子,你们孩子就别跟我提钱了!再说,我跟这小老三也算有缘,我们爷儿俩也是善缘。”王大爷笑得悠长,“你们要是乐意,我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
“好!好!”苏敬钢满口答应,“反正我也没文化,你就给起了吧!”
左娜见这爷儿俩完全忽视自己的存在,心中不快,可王大爷先前句句命中,不好直白回绝,便摇着苏敬钢的胳膊,委婉地说:“都还没长成人形儿呢,这么早起名字干啥?”“起了好,起了不就能天天叫了?”苏敬钢丝毫不理会左娜,催促王大爷说,“快给起个好名字!”王大爷闭目掐指,念叨一阵,幽幽地说:“就取个‘凉’字吧。”“善良的‘良’?”左娜再也忍不住,回绝说,“不好。”王大爷笑了笑,不吱声。苏敬钢捏了一下左娜的手说:“别打岔,听王大爷说!”——“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凉’!”王大爷解释道,“我算过,这孩子来年春天出生,命属炉中火,时节主发,有土、木常伴,熊熊不灭,唯欠节制,忌嗔怒。三儿啊——我只怕这孩子秉性随你,故取一个性寒之字相调相较,助他能自行自制、多虑少怒,这孩子五行又缺水,名字里带上两点水,可以逢凶化吉。”左娜听了,撇撇嘴说:“还是不怎么好听。”苏敬钢目不转睛地聆听完,勉强懂了一半,嘱咐左娜坐着等他,自己跑进大棚,一会儿工夫,提着满满两兜子鸡鸭鱼肉出来,撂在王大爷脚底下,匆匆谢过,拉起左娜奔回家去了。
苏敬钢进家门时,见母亲正坐在南屋的床上抽旱烟,他也竟不再恼怒,走进屋说:“别抽了,收拾一下出去吃。”苏母望了一眼左娜,不冷不热地说:“路边儿捡钱啦?结婚以前没见你这么败家啊!”苏敬钢被一盆冷水浇头,兴致锐减,不耐烦地说:“你孙子有名字了,去庆祝一顿。”苏母把烟枪移开嘴:“好家伙!也不问一句我这当奶奶的就敢瞎起名儿,你们可真能耐!”苏敬钢说:“不是我们起的,是胡同儿口的王大爷,名字算过,有讲究。”苏母“咣咣”地敲着烟枪,骂道:“瞧不起我?你妈我念了十几年私塾,还不如一个臭算命的?行!你们爱叫啥就叫啥,叫了就不是我孙子!别指望我给你俩带这孩子!”苏敬钢捶了一拳门框:“到底吃不吃?”“吃你姥姥吃!你爸死了你就敢欺负我了是不是?三瘪犊子你瞧着吧,谁不孝谁不得好报!”“爱他妈吃不吃!”苏敬钢猛地摔上门,拉起傻站在门口的左娜下了楼。
西元1986年初,周国大的花圈店几乎分文不入,再也撑不下去,两个月后被周国大改成一家饭馆,取名四季香,卖抻面、鸡架和简单的炒菜。妹妹周晓燕曾极力劝阻,嫌周国大对开饭馆一窍不通,别连家底也赔了进去。周国大不听劝,第二天直奔劳动市场,雇了三个厨子、两个水案、四个服务员回来,再把门脸儿房粗简地改装一番,砌两个灶台,置办些二手桌椅,一个月不到便开张营业,刚好赶上盛夏,夜里酷热难当,屋里电扇不够用,周国大干脆命服务员把十五张折叠桌子支到了门口马路边上,几十箱啤酒垒成了一堵墙,明目张胆地占道揽客,派出所跟居委会也不敢管。不少人听说周国大开了饭店,纷纷前来捧场,多半是社会上的朋友。
一到晚上七八点钟,四季香门口声势震天,十五张桌子彼此紧凑,三四十人分扎几堆儿,嗑着花生,喝着啤酒,划拳叫骂。周国大则穿梭其中,这桌干两杯,那桌划两拳,也不管来人熟络与否,只要叫他一声“周大哥”就算朋友,动辄就给人家免单。一个月下来,饭店虽不至亏本,却也没赚着几个钱。周晓燕终于看不过眼,只要不跑夜车的晚上就亲自过来收账,硬拉下脸子才多收回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