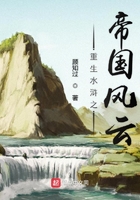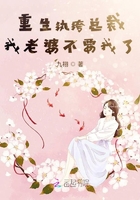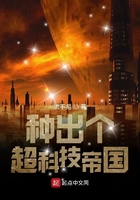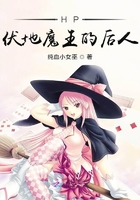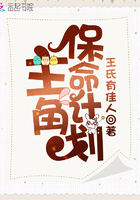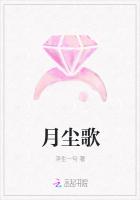老庙——我的初中生活的第一驿站
中国的风景大致都一样:河边有山,山上有庙,庙里住着老和尚。一到这种风景地,就让我想起我住过的一座老庙。这座老庙所在的地名,现在有许多人都知道——西昌。我在那老庙住的时候,西昌还是个无名的边地小城,城边有个美丽的高原湖,名叫邛海。邛海的西南侧,是一座风景山,叫泸山。泸山风水好,从山底到山顶有一脉,树木特别繁密,远处望去,高大的树冠起伏如浪。在这树浪中,错落有致地有大大小小十来座寺庙,从山脚到山顶,隐约可见,让人想起仙山琼阁这个词。
我进庙不是出家。“******”后,破除迷信,把大庙里的老和尚们遣散了,剩下个大庙,挂上一个牌子:西昌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我和两百个初一新生,接了老和尚们的位子。“******”年代一切都那么敢想敢干,除了老和尚念的那本经与我们念的不一样外,庙里其他的变化不大,所以在我前半生里,有了住庙的经历。学的那些课本大都诚心诚意地忘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年多的庙里生活:简槽、菩萨、臭虫、花豹、老僧……
大庙生活最先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引水的简槽。我从成都随下放的母亲到西昌,又从家里进了大庙。说是“******”,我个人的生活却一下子退了八百年,也就生平头一回知道简槽这种东西。山泉在高山顶上,多年以来,人们把碗口粗的棕树一剖为二,然后掏去树心,形成一个长槽,槽与槽相接,水就越沟过坎,跳崖穿涧,流进大庙的灶房。简槽是一槽搭在另一槽上的,如果其中一根被风吹落,被动物撞掉,大庙立刻就会断水。到庙里后我最早的任务就是去查简槽。全校师生饮水就靠简槽引来的那股潺潺细流,一天断流好几回,不去查水是不行的。上山查槽,在槽的两边,因为常有水流滴注,所以树草丰茂,苔厚路幽。那些简槽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物件,长满木菌和青苔,像百年老人的手。这使我感到一种恐惧,想起这原是一座老庙。
老庙里的和尚被遣散了,那些泥胎的菩萨还继续留任。没有了香火,就没了神采。没有人来诵经敲磬,就没有了威严。文菩萨和武菩萨都一个个呆坐着,在我们的身边,当留级生。听不进三角代数、政治经济,现在想起来,觉得真像是有些从第一线“退休”下来的人的神色。在位和不在位的不一样,在位有香火的和没香火的也大不一样。我觉得在大庙里上的那些课算没白上,就因为好好看了那些坐在身边的菩萨面孔,想到了另一种菩萨心肠。
老庙在大山上,于是常和野物相遇。那时国家极其困难,每月定量配给二十一斤粮、三两油、半斤肉,市场上买不到任何东西。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只好上山挖山药充饥。那地方山药叫黏口苕,长在山间石缝里。我们下课就带上小锄去挖。这小锄,把儿只有手臂长,锄口只有一寸宽,是山里人挖药用的,在石缝里掏山药比较顺手。挖山药有时会遇到野物,猫头鹰、狼、麂子。开始怕,但饿起来,也就不觉得猫头鹰的叫声和狼的眼神哪点恐怖了。有一天半夜里,一对金钱豹(当地人称“花豹”)闯到大庙外,在通往厕所的后门叫了一夜。全校的人都被那叫声惊醒了。当时我和三个同学,就住在后门旁的一间小屋里,我们竟没有一个人醒来。第二天早上,听见大家对那种声音的描绘,看见住房外十分清晰而硕大的爪子印,我们再也不敢上山挖山药了。
在老庙虽没有被花豹吃了,却被臭虫们饱餐了许多次,应该说,从生下来到现在为止,老庙的臭虫我认为是最狡猾、最疯狂和最可怕的了。刚进庙,不知庙里有臭虫,在和尚们原先住的楼上,把地板扫干净,打个地铺就睡。半夜浑身火烧一样地痛。点上煤油灯,身上已被咬肿了,掀开枕头,还没有来得及撤退的臭虫就有十多个,用油灯照一下墙板,新开来的臭虫大军排成队地前进着,用油灯一燎,烧得拍拍响……第二天我发高烧,打针吃药一个星期才缓了过来,之后,就逃到后门旁的那间小屋,就在闹豹子后,我也没敢撤回老和尚们住过的楼上去。
这就是老庙留给我的印象:比和尚厉害的是赶不走的菩萨,比庙里菩萨厉害的是庙外的花豹,比花豹厉害的是咬人的臭虫,比臭虫厉害的是不怕咬的老和尚……
大桥——高中生活的最后一课
这是一个区和一个公社的名字,在滇川两省接壤处,金沙江北岸。如果要回忆一下过去的岁月,我是不能省略掉这个点的,虽然它只是短短四个月的一个点。一个点,在我的生活中,不可能有更多的东西留下,连可供回忆的事情也不会很多,在人事档案中甚至连一行字也没有。关于大桥最清晰的表达是:四十年前,我在大凉山的唯一的重点学校西昌高中毕业前夕,在这里的生产队当过四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的工作队员。当然,这一句交代,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不会产生“情感背景”来引导他们进入阅读,但在四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不会在这样一篇短文里诉说这一段历史,我只想告诉你,这四个月的影响,在我此后的人生,打上了一种说不清的底色。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我所在的大桥区,就是艾芜先生《南行记》中的一段。我到大桥去,是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但就是这种运动,这里也特别作了交代,“过去当过土匪”这类情形不当作问题清查。看过《南行记》的小说和电影了吧?好了,你可以进入阅读了。
这个底色是从火塘冒起的青烟,早上的阳光穿过烟雾,让它生动起来。烟雾有一层七彩虹霓,使它呛人的气味柔和许多。这是我房东家,一间干打垒的房子,房子中间是一个火塘,从房梁吊下一根用牛皮编成的绳子,悬在火塘上,火塘里还有一只铁支架,可以放上锅,此时锅里正煮着早饭,弥漫着一屋的洋芋味。我这样细致地说这火塘,不为别的,这就是我房东的全部家产,如果要全面一些,还要加上火塘边上的竹笆,竹笆上一块羊毛毡和一床曾经是被子的东西。我是外人,我不能和这家人一起睡在火塘边,于是我就在木板搭成的半边阁楼上住。我在这户人家只住了半个月,再住下去,我就会变成熏肉了。我已忘了主人的姓名,但那早晨燎醒我的炊烟,却越来越生动了……
这个底色是一盏马灯发出的光,那马灯是我最有用的朋友,在大桥四个月里,我拥有的就是一个背包和一个马灯。这是工作队的装束,只要见到一个背包上挂着一盏马灯的人,老乡们就知道那是“工作同志”。(就如改革开放之初手上提个“大哥大”的,人们就知道这是位响应号召的先富同志。)马灯的灯光让我感到温暖和亲近。在这个没有电灯的大山深处,夜的确太长了。至今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有恋灯情结,在我的生活中,可以说吃的苦不少了,也不太怕吃苦,最怕的是在一个没有灯的环境生活。马灯最好,走到哪儿,哪儿就亮。山上只有小路和田坎路,没有马灯不行。手电筒费电池,也娇气,一进水就坏。我在大桥时正值雨季,每天记不得要摔多少跤,当我每次掉进泥水里的时候,马灯以它全部的光,鼓励我爬起来。记忆中,好像老乡们也喜欢这种灯光,山里来了“工作同志”,生产队就要开会。会议主题总很严肃,不是“以粮为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但开会前半个多小时是快乐的,山里缺少交际的年轻人,在会场能开心一阵子,唱革命歌,打情骂俏,与相好聚一聚,这众多的内容让我感到这里同样渴望生活……
这个底色是秋雨滴进心里的苍凉,远离城市远离亲人,距离把一切变成可以承受的情绪。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秋季,我的双亲都受到了批判斗争。我远离他们,那种急风暴雨,到这儿就成了萧瑟秋雨。同样地,那场运动到了这远山边地,也就成了一个中学生领导的“学习”。秋雨中,许多叶子都落了,让心流泪。我不愿我的父母在这场风雨中离去。每天,我都翻看从公社送来的一个星期前的报纸,然后剪下上面的文章,装进信封里,准备当作信给他们寄去。我很怯懦,我不知人们把父母怎么样了,但又希望父母知道我在想他们。就这样,每天一个信封装一篇剪下的文章,没写一个字,但他们会知道我在说:我想你们,我一切都好……
那些信一个星期去区上寄一次,邮局在河对面,要蹚水过河。我腿上长了个疮,因为总下河蹚水,一直溃烂不愈,至今留有瘢痕。这个瘢痕常让我想,这个地名真怪,大桥,怎么就没个过河的桥呢?
叶延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哈尔滨。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学校期间发表的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度诗歌奖,诗作《早晨与黄昏》获北京文学奖,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到四川成都,在《星星》诗刊社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一九九三年评为正编审并首批获******政府特殊津贴。一九九四年由国家人事部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一九九五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