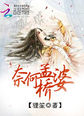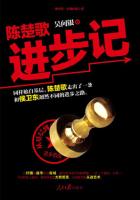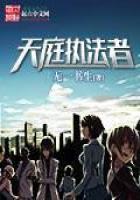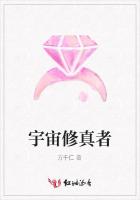在远古的那场战役中,蚩尤部落与华夏部落争斗,日月昏暗,大地飞扬,净是山河悲壮的声腔。这场华夏部落的开元之站,奠定了一个民族几千年以后浑厚凝重的文化底蕴。从孩童时期我就听过那个撼天动地的的战斗,就向往那场天崩地裂的战场,这是莫大的中华文化对于渺小的个体生命,自始之初的呼唤。小小的我难以想象黄河流域这片草丰树茂那个远古的年代,在那场已经没有人歌颂的战斗中,俨然改变了几次模样。
现代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还留下多少关于那场战斗的遗迹;还有多少次远古吹来的烈风传颂那场战斗不为人知的英勇;还有多少典籍在向这个民族的后人延续远祖美丽浪漫激烈彪悍的传言。关于这个民族根迹的寻觅或者说这个民族今后的传袭就成了一个不免悲悯伤感的悖论:
后人的无处探寻与文化的奄奄一息。
一方面,这个民族后人渴望更多的只言片语来了解那场战斗,渴望大地给予更多关于那场战斗的气息。昂首长啸天空,又渴望回响更多那场战斗的金鸣,又渴望彩虹能够重现那个战场的硝烟。无数这个民族的后人怀着崇敬与悲悯去挽起那抔远古留下的黄土,只有这样,才能更近一点触摸这个民族最初的印记。也许人们会惋惜一个痴情的后人对先祖苦苦追寻而不觅;其实,更令人捶胸顿足的是这个民族千年以来的文化精髓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后人的无处探寻与文化的奄奄一息。这是令人心痛的悖论,也是整个民族双重的叹息。好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命运中决然合适的一对,只是少了一份缘分,让两人相遇。
后人与文化,探寻与传递,在本质上是这个民族延续中必须克服的问题。想要解决后人怎样探寻,只需弄清楚“文化”到底在哪里;要解决文化如何传递,就必须弄清楚“文化”在远古时期到底是什么意义。
在远古那场战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那个战场自然就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战场之前,我不敢武断文化精髓是否还在那里。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华文化自身的定义越来越模糊了。一是如今又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侵袭太深了。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伦关怀,处世情操,治学精神,甚至家国信仰都被窃取而去,就像屈夫子的端午节,我真担心若干年之后的后人还知不知道到底是源自哪里。狂妄又无知的人,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爱批评中国人没有信仰。所举的例子不外乎:中国没有教堂,中国人不懂祈祷,中国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很同情也很理解他们的偏论,更多的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懑。华夏民族的后人,现在称作“中国人”,他们没有教堂,可是有灵堂。中国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愿意对那些已经死去的至亲至爱唠叨一点家常,和父母兄弟妻儿比起来,上帝毕竟是个外人。自己掏心窝子的话更喜欢对那些曾经对自己掏心窝子的人讲。稍微回顾一下人权与神权斗争的历程:当西方人还在借助文艺复兴挣扎“人”存在的时候,在遥远的东方,那场战斗之后,中国人在主流文化的发展中,就已经完成了“人”的独立。
活着的人尊敬父母,友爱兄弟,信义朋友。死了,也是对后人殷殷深切的祝愿。于是,活着的后人对于死了的先辈发自内心的崇敬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信仰自己的祖宗就是信仰自己生命的来源。最为可贵的是,这种对于“人”的信仰避免了人受到“神”权极端主义的控制。因而,人才能活的更独立,更自由更有人的尊严与模样。还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只能是信口雌黄。再深深想一下,那些诋毁中华文化的言论背后往往不都是隐藏者处心积虑的政治目的吗——文化演变。
中华文化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不得不想起一种对于历史的分层研究的手段。对于中华文化的演进历程,也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研究:第一层次是以十年为单位。反应一个社会在极端的历史时期内所爆发的各种文化冲突。研究这中极端时期内的历史,只能针对于某个历史事件或者文化现象。对于探寻中华文化这种长远的脚程来说,未免显得短视。第二层研究历史是以千百年为单位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华文化在千百年之内不曾改变的内容可以称得为中华文化的内涵了。对于中华文化在某个历史时期内的研究不然要借助这种千百年的眼光。第三层则以数十万年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对于本次考察来说,只有在还原那场战斗的时候,才可能用的到这种超视距离的眼光。其实,这种超视距离的眼光要解决我的一个困扰,这个困扰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这次考察,我希望我微薄的学术根基与大家才思敏捷的感触力能够实打实地给予这个民族后人一个可信的答案。
”中华文化是本地源起,还是由西东传而来的。”这就是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学术界的争论不止,我的疑虑不休。此次考察,必要还中华文化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哪怕真相让我痛苦心乏。
策马扬鞭大渡河,转身以到彝良山。千关万水等闲度,云蒸霞蔚又一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