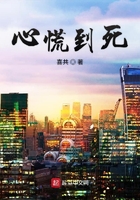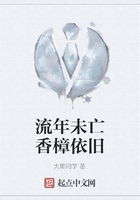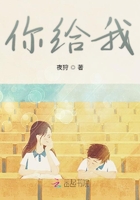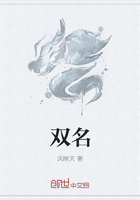说实话,其实,对于年轻时候的父亲我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前不像现在基本上到处都可以照相,手机、相机等随处可见,那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贫瘠的,再说也没有那个条件。父亲兄弟四人都住在村子上,还有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年轻时出嫁到了川口村了,父亲在众兄弟中排行第二。那时候还住在南埝,父亲结婚几年后才到新地方卷盖了现在所住的那三个砖窑,在南埝时住的是一个五六米深两米多高的小土窑,黑咕隆咚的,在旁边一个木椽搭的灶房。我是不怎么记得在那里住过了,但是姐姐住过,不过印象也不深了,现在还好着呢,能够看的出来。
也是记得家里有一辆四轮农用车,听说还是父亲到处筹钱买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来拉人的,在我们这一条梁上好多人都知道183,这是当时的汽车牌照号尾号数字。走的是从涵洞到双碑,再到上点,陈炉这一条路线,当时的从涵洞到双碑票价才一块钱,到陈炉才三块钱,价格也不是很贵依照现在来说。不过现在坐班车从涵洞到我们村三公里路就要两块钱呢,到双碑三块,到陈炉将近十块呢。后来上中学前后,大清早,有是家里门口,聚集着好多同村的学生,都等问着看父亲几点出发,是不是都可以捎上,虽然那么早可能也没有什么人,但父亲也是能早起就早起,捎上,哪怕是在路上多等一会呢。
农用车好像是92年那一年才买来的,那一年妹妹才刚出生,后来父亲还做了一段生意,贩卖了一些扫除和农用品到周围的县镇乡村买卖,那时候我还小,有时候也跟着照看一下东西,到耀县宜君等地方也跑过。只是父亲最先是跟着别人学木匠的,我们家的家具,桌椅基本上都是那时候父亲做的,哪样式做工现在看起来都还不错,包括后来给舅舅家和二姨家做的门窗,只是现在都已经换成了铝合金的了。由于年轻时候的父亲也比较好强,源于一些事情后来也就没有做木匠这一方面了。家里好多人现在还说呢,你看你,那时候做些家具装修些现在多好,事实上也是如此,前几年装修还是不错的,而且也有哪一门好的手艺,不过父亲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在家里的一个柜子里还发现了父亲那个时候学徒和做工时留下的日记本,和一些老式家具的尺寸图册等,上面的字写挺漂亮的。在家里其实包括锯木头用的刨子,和锯子,斧子,搓搓等一些工具到现在都还是挺齐全的。
说到这里,就想起了父亲和母亲年青时候的相识,这还是听老妈说的。两个人也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只是短暂的相识,就结成这一对百年夫妻。当时妈妈的姨妈也是嫁到了我们村子,后来看我爸年轻的时候为人还不错,又吃苦能干,就和我外爷说了。我外爷也是做了一番考察的,后来在家里做了一吨涮汤,叫我父亲去吃,父亲也是放的比较开,就是这一顿饭,让外爷他认可了我老爸。不仅是一米七八左右的身高,又是个有一技之长的年轻小伙,性格开朗,健谈且为人处世等都还不错。他们那时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有车有房条件比较高,只要双方长辈同意了,也就定了下来。也是,到后来弄农用车的时候,外爷和外婆喜欢吃油糕,时常父亲拉人路过的时候在以前的铁桥买上那么几个带给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铁桥了,那里是后来把桥扩宽在中间改建了的一个超市。说起来,铜城这个地方比较小,尤其是老城区,在不宽的两个山之间的川道建设的街道,一共才有两条马路,一马路和二马路,剩下的都不是很宽广。正因为这样,92年省上就开始意识到了,才在耀县划了一块地,开始建立新区,这样离西安也近了。2000年以后新区才慢慢发展的快了起来,市政府也早就搬到新区,以前是在我们老城区,也就是现在的十里堡附近呢,时间还过的真快我现在都25了。
年轻时候的父亲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能折腾的,也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就像开农用车的时候,一般车子有个什么大小抹搭都能自己收拾好,也算一个业余的修理工吧。以前家里种的五六亩麦子,熟了的时候的时候,都是用镰刀割得。后来又从外地来了的“麦客”用哪一种大一点的镰一次性收的比较多,但是不好操作,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哪种镰父亲也能够驾驭。收的麦子还要用拖拉机碾出来,然后在晒干,后来还要扬场去皮,也挺麻烦的。你看现在,只要收割机能到的地方基本上都不用人管,一次性直接到位,只是需要找地方晒干就可以了,懒一点的人甚至都不晒了,看收粮食的来了直接拉走买了就可以了。
记得那时拉麦子的时候,在麦地里我要学着开车,父亲也给我教了,只是操作的不是顺当,有一次差一点开到沟里去,也把他吓坏了,好是没有出什么事,赶紧踩了刹车。父亲的开车还是比较老练的,算算也开了将近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只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跑去外地了,在榆林,内蒙东胜,山西大同一带给人家开大车拉煤去了。一去,连着就是好些年,平常也只是电话联系,一年到头才回来那一两次,直到前两年才不再上去了。说来也是比较辛苦的,毕竟上有老下有小,而且还供养了三个学生,虽然,都不是什么好的学校,姐姐的师范学院,我的技术学院,妹妹的财经学院。但是父亲也是真正的进了自己的一份心,同样的对两边的老人也都不错,给我们姊妹三人做好了相当的表率。
年轻时候的父亲,最先是住在南埝的,后来分家后和大伯,大大他们也在南埝的老地方住了一段时间,像前面说的我没有记得我住过,不过后来听人说那时搞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不准超生,要么罚款,父亲经常带着我到各个亲戚家躲藏,甚至和当时的大半夜来家查岗的负责人,还起了纠纷。那时也好多人都是如此,看看周围大部分家庭也都是三两个孩子的,也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