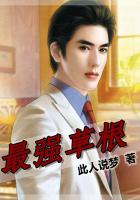生产队长吴大运是水玉莲的丈夫,水保贵的姐夫,水保田的堂妹夫。水保耕比水玉莲大几个月,比吴大运小两岁,过去一直称他表兄。自从吴大运跟水玉莲成亲后,按理说,这位表兄改称水保耕为三哥,可他当了二十多年的表兄,就是改不了这个口,起初水保耕还习惯性的称他表兄,后来两人谁也不称呼谁,见面“哎”一声算是打过招呼了。要是当着外人,吴大运称水保耕为“他三舅”,水保耕称他为“他姑夫”。农村像这样的关系很多,还有比这更难称呼的亲戚哩。
说起吴大运,命运真不好,十七八岁去西藏当了五六年兵。当兵三年后,回家探亲过春节,身穿黄军装,头顶五红星,脚蹬大头鞋,腰系武装带,甭提有多神气。
生产队有四五位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说亲。大冬天农活少,没事的时候,这几位姑娘老是结伴往吴大运家跑,问这问那,问长问短,吴大运也挺耐心,给姑娘们讲些部队的离奇怪事。一来二去,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女孩互相吃起吴大运的醋来,隔三岔五的找机会单独会面。
水三爷家三姑娘,水保贵的亲姐姐,名叫水玉莲,长相俊俏,乖巧聪慧,人见人爱。她是称吴大运表兄长大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兄妹天天见面,谁也说不了什么,一来二往,互生爱恋。两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吴大贵是家里的老大,凡事都得他做主,他托媒人去提亲,只要两个人愿意,提亲只是一种形式。水大爷的大妹子,水三爷的大姐是吴大运的大妈,两家人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亲戚,知根知底,便定下了这门亲事。水三爷、水三奶看着帅气的军人女婿,听说部队表现不错,还给家里寄来过两张立功受奖的喜报,就贴在他家堂屋正墙上,红彤彤的很是显眼。
他为人老实,做事踏实,眼里有活,手脚勤快,不用交待,他会主动做好各项工作,听说部队领导很喜欢他。只要部队表现好,提干是迟早的事,就是转业回地方,起码也是个正式工人,不会回到农村下苦,两家人自然是十分欢喜。
亲戚见了都说,水玉莲找了个好丈夫,同龄的姑娘们羡慕她有福气。吴大运春节探亲,在家呆了一个月,说亲、订亲、成亲,两人幸福甜蜜的度了几天蜜月,嘻滋滋带着牵挂回部队去了。
吴大运回到部队后,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同事信任,领导喜欢,家里年年收到他的受奖喜报,家人很是为他高兴,水玉莲更是天天盼,夜夜想,做着当城里媳妇的美梦。转眼间三年过去,吴大运正在期待提干的时候,领导说他文化程度低,难以适应部队未来建设需要,改转志愿兵,年龄又偏大,他只能卷铺盖走人。
辛辛苦苦奋斗了六年,又回到生他养他的穷山沟,跟日夜思念的媳妇过起了艰难的小日子,后来大伙选他当生产队长,带领穷怕了的社员们跟命运抗争。
同龄人经常笑称,赶快改名吧,都是你这个臭名害的,吴大运,无大运,就是无大用,只能当个生产队长。要是改名了,说不定还能调到公社当几年不拿工资的跑退干部,总比呆在家里务农强,弄不好将来转正,在公社安个家,子孙们还能过几天好日子。
且说吴大运去大队开会,不是传达上级精神,也不是安排什么工作,而是县砖瓦厂招工的事,要求是高中文化程度,政治思想过硬,为人本分老实。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自己文化程度低,没有进城当工人的命。他第一个想到了水保田,他是阳山大队的高中生,是个文化人,给他争取这个名额最合适。他好说歹说,争取了一个招工指标。大队开完会,他跟几位好友在小买部喝了半天酒,看天色已晚,急忙往家赶。
晚饭时分,大门外一阵急促的狗叫声,吴大运走进门来,三蛋站在院台上撒尿,看到他快步走进来,喊叫一声跑进厨房:“妈,姑父来了。”接着吴大运走进屋,望着坐在窗台对面炕台边吃饭的水保田,笑问:“正赶上吃晚饭,下午空肚子喝了半天酒,肚子有点饿,给我舀一碗。”
水保田赶紧放下饭碗,起身站立,指着窗台边的空炕客气的说:“快上炕吃饭,还是昨天宰猪的剩饭菜。”
吴大运不客气的脱鞋上炕,靠在窗台这边盘腿坐下,望着侄子们的饭碗说:“昨天的肉菜,我看着都流口水。”
水保田喝了一口菜汤,咕的一声咽下喉咙:“昨天不是通知你开会吗,咋还有空喝酒?”
水保耕给吴大运端了一碗肉菜,替坐在后炕根的水大爷舀了一碗菜汤,端起放在炕桌边上的饭碗坐到炕头,望着吴大运等待回答。
水大爷吃完饭,靠在后炕墙角,指着饭碗说:“赶紧吃饭,放凉不好吃。”
“好事,好事。”吴大运端起热腾腾的饭菜,夹起一块肥肉嚼了几下,买起了关子。
“是不是修梯田的事?全国人民都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个时候,哪年不是动员生产队修梯田?老百姓修了这么多年梯田,老天不下雨有啥用,庄稼还不如山坡地。”水保耕嚼着饭菜发起了牢骚。
“哎哟,这次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生产队长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快把我饿死了。开完会,几个生产队长非要拉我陪他们喝酒,空肚子喝了几杯,难受死了。”吴大运买关子,就是不讲开会的内容。水保田、水保耕弟兄俩停止嚼咽,望着他等待下文。吴大运不慌不忙,喝了两口汤,扫了一眼水保耕,咬了块谷面馍馍细嚼起来。
吴大运咽下馍,望着水保田说:“我给你说,县砖瓦厂招收工人,红光公社分了三十个名额,公社给大队只给了三个名额,生产队都想要,队长争红了脸,我死磨硬缠要了一个指标,这是我费了半天口舌争来的。”
水保耕着急的问:“招收工人,什么条件,你准备让谁去?”
吴大运说:“招收工人是有条件的,要求家里人口多,家庭生活困难,高中文化程度的才能去,大队就那么几个高中生,胡大海都知道,我详细介绍了你的情况,总算给了一个名额。”
水保耕显得有些激动,他放下饭碗,瞟了一眼大哥,嘿嘿干笑两声,试探性的问:“我小学五年级毕业,跟高中生差不多,大哥认识的字我也认识,要不让我去?”
“水家爸,堵狗来;水家爸”门口的大黄狗拽着铁链大声狂吠,水保耕在大哥的指使下跑出去堵狗。他走出大门,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紧贴墙根站立,手里端个墨水瓶,她是霍飞虎家的二丫头霍夏霞,看到水保耕出来堵狗,大声问:“我家没有煤油了,借一灯盏煤油,有没有?”
“我不知道,进去看看。”水保耕拉住狗铁链,大黄狗挡在后面。
屋里静静没有说话声,水保田、吴大运侧头望着霍夏霞走进门来。霍飞虎家的几个小丫头都害怕水保田,霍夏霞看他盯着她,一脸严肃,吓得有点哆嗦。头也没敢抬,赶紧解释说:“我家煤油用完了,我妈叫我借一灯盏煤油,明早我爸买回来还你。”
霍夏霞说话的声音很低,竖耳勉强听得见,说了句啥话,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有听清楚。水保耕从灶台架取来装过白酒的玻璃瓶摇了摇,对着昏暗的灯光说:“还有半瓶,拿过来。你家吃饭了没有?”
霍夏霞跚跚走过去,递过墨水瓶,说道:“家里没有煤油,看不见做,还没有吃哩。”
吴大运看她衣服褴褛,穿双破布鞋,两个大拇指露在外面。这个丫头小时候得病,不知咋弄的,落下了耳聋的毛病,口齿也不清楚。他望着聋丫头大声问:“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好看不好看?”
霍夏霞好像没有听清,望着他大声问:“你说啥,我没听见。”
水保田笑了笑:“霍飞龙生了两个丫头,霍飞虎生了四个丫头,这弟兄俩同年同月生儿子,算是后继有人了。”
吴大运说:“这弟兄俩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要是再生不出儿子,恐怕要断子绝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龚秀珍坐在灶台边小凳上,望着霍夏霞嘿嘿嘿笑了两声:“保俊今年才两岁多,三爸生儿子,五十多了吧,三爸比三妈大十多岁,三妈生他也快四十了。”
吴大运笑道:“大概再不会生了吧,她十四五岁生孩子,这一生就是八个娃,她的外孙比儿子还大。”
水保耕笑问:“他姑姑还没怀上?”
吴大运说:“结婚这么几年,最近才怀上孩子,这点不像她娘。要是像她娘,我也是三四个孩子的父亲了。”
龚秀珍惊奇的问:“他姑姑有孩子了?哎哟,这几年怀不上孩子,都快急死了,几个月了?”
吴大运说:“说是三个多月,不知道她是咋算的。啥时候怀上孩子还能算出来?”
龚秀珍笑了笑:“我也不会算,我生这几个娃,从来不知道日子,平时少干点重活,肚子疼就该生了。”
水保耕倒满墨水瓶,帮她拧紧盖子,霍夏霞小心的捧在手中,朝水保耕笑了笑:“谢谢水家爸。”说完转身离去,水保耕送出大门。
“刚说到哪儿了?”吴大运摸摸后脑勺:“噢,保耕年龄还小,以后有的是机会。大家都知道你是小学文化,做假谁也去不成,人家巴望着你做假哩。”
“这个名额是你争来的,你看我能去成吗?”水保田忧心忡忡:“这几个孩子要吃要喝,蛋儿上学,二蛋有病,三蛋、四蛋还小,五蛋、六蛋还需要大人照料,我怕她忙不过来。”
吴大运瞥了一眼清洗碗筷的大嫂,安慰道:“这个你放心,我在回来的路上都想好了,翻过这个年头,安排大嫂和金蛋他娘给生产队养猪,猪场离家近,活也不累,能照料好孩子。”
“哎哟,这个你都替我想好了,让我说啥好哩!”水保田着实有些感动,说话诚实得像个孩子:“真是让你费心了,你就放心吧,我不会给大队丢脸。”
水大爷靠在炕后墙角,推开二蛋打瞌睡靠在腿上的小脑袋,捋了捋花白的胡须坐起身:“这是个好机会,他姑父好不容易给你要来一个名额,家里就是再苦也得去。再说,家里不是还有我和保耕吗?有啥不放心的。”
水保田听父亲这么一说,心里稍有些安慰,心想,生产队实行按人分配,家里的口粮一份也不会少,要是以后天旱的话,还能挣几个钱购买供应粮。我走以后,就得辛苦娃他娘了。想到这,他抬头瞅了瞅靠在后炕根的父亲,瞥了一眼坐在炕头边的弟弟,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龚秀珍身上,瞅了半晌问道:“那我就去?”龚秀珍望着丈夫坚定的点了点头。
“谢谢你,兄弟,为我想得这么周全,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表现,为咱水家湾争光。”水保田坚定的说。
“好,就这么说定了,给你报名的事,现不要向外声张,避免节外生枝。”水保田、水保耕、龚秀珍望着吴大运点点头。几个人都明白,凡是好差事,不管条件够不够,大伙都想争着去,哪怕自己不够格,也要找大队和公社领导去闹腾,祸得大伙谁也去不成;闲差事谁都不愿去,即使是举手之劳,油瓶倒了,他也不会动手去扶。这次招工要是被庄上人知道了,说不定背地里有人去大队打小报告使绊子。
水大爷用感激的目光望着这位小外甥,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有你这个好亲戚,还担心啥。唉,好人咋就没好运哩。”
“大舅,我的命运不好,要不是我的文化底子薄,我才不会让他去哩,呵呵呵”他停了停,望着大哥说:“就说我当兵吧,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辛辛苦苦在部队干了五六年,没有提成干,改转志愿兵年龄又偏大,复员回来当个工人也行,结果当了这个出力不讨好的生产队长,庄上人拿我不当干部,你说,是不是命里注定吃不了公家饭?嗨,这么多年,我也想通了,该吃哪碗饭命中注定,该你的推不掉,不该你的挣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