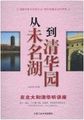北方的风是有几分神秘的。北方的风很像一个看不见的人,他想来你家作客,就不由分说举起拳头擂你家的门,擂完了不行就用脚端用屁股拱。最后办法使完没有达到目的,就索性在楼道里发起脾气来,丁零哐啷乱摔东西。一会儿把一个好端端的啤酒瓶“砰”地一声从窗台轱轳到地上;一会儿又把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乒乓”拿来摔两摔。那块玻璃一开始还算挺得住,但三掉两摔玻璃表面就裂出冰纹来,最后“哗啦”一声掉在地上跌得粉碎。
在北方,刮风天很多人躲在屋里不出门,就是临时到外面买个酱油散个步也得穿上带帽子的厚外套。小时候我们都管这种外套叫“棉猴”。其实,世上哪有这么肥肥胖胖的猴子呢?想起来就觉得挺好笑。今天我下楼去散步就穿着这种“棉猴”。因为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我一走出楼门口就被一只巨大的手推着走。一开始我还想抵制,故意站在原地不动,但是后来我知道我拗不过风的——自然界的一切神力都不可抗拒。我索性顺应潮流被风当成手中的一枚棋子,被它刮得在风中滴溜溜地打着旋,对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脚不沾地如同在冰面滑行。终于碰到近处有一排铁栏杆,急忙伸手抓住以免被风吹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透过那排铁栏杆,我看到一个盖房子的建筑工地。吊着的灯被风吹得变了形,灯影忽明忽灭,人影交互叠错。工头哇啦哇啦在大声喊叫着什么。风更大了,我听到北风在空中咝咝打着唿哨。有一缕特别尖细的声音,像是有厉鬼藏在空中,故意憋细了嗓子好迷惑路人。有砖垛被风吹倒的声音,稀里哗啦宛若一罐子碎银元落地。工头气疯了,喊叫的声音更大了。可生气有什么用,风又没长耳朵。
说到风我倒想起前一阵子读过的小说家莫言的一篇散文《会唱歌的墙》。文章的结尾非常奇异。散文都是说真事儿的,这篇却充满幻想,说他们那儿有个老人收集了几万只空酒瓶砌成一道培,把他们乡和外乡隔开来。那道墙瓶口一律朝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万只瓶子就会一齐发出音色各异的呼啸声。老人砌完墙就坐在墙根儿死了,后来会唱歌的墙倒了,“千万只碎瓶子在雨水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继续歌唱”。这就是北方人对风深刻而又自然的印象。北方的风像刀子刻心,强烈而略带一点残忍的味道。
一夜飓风,满地碎片。第二天一早,我踩着碎玻璃碴子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