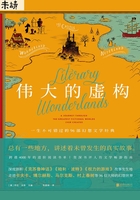我躺在牙科那把好像平放在海滩上的沙滩椅的治疗床上,毫无精神准备地等着医生给我看牙。我爸妈都是医生,我对医院这种味道是熟悉而且亲切的。我小的时候常到医院去玩,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只是觉得那些小瓶子小药盒好玩。我一向身体很好,连牙都不曾补过,这趟补牙是头一遭,在医生拿起器械前我还在心里哼着小调。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恐惧的。医生用一把小榔头在我的牙齿上东敲敲西碰碰,问我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我一律摇头说不疼。牙医说我牙齿上长了个大洞。于是拿出她的全套“兵器”来对我牙齿上的大洞进行轮番攻击,一会儿拿出钩子来钩一钩,一会儿拿出小铲来铲一铲。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显得十分悦耳,我躺在那里还挺抒情,殊不知大的灾难就要来临。我听见医生开动钻头的声音了。
“干什么?”我猛地一惊,跳起来。
“躺好了,别动!”我又被接回到那把“沙滩椅”上。
随后我听到那轰隆隆的钻头离我越来越近的声音。这使我想起装修房子的时候的那种能穿透墙壁的电钻的声音。这种联想让我越发恐惧。医生说;
“疼的时候举左手,不许推我、躲我、或者做其他动作。”
我说:“干吧,没事,我坚强着呢。”
说完我还冲那位医生微笑了一下,以示我是真的坚强。
她看我这么视死如归,就下手了。开始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轰隆隆地震荡着,震得脑袋瓜子微微有些发麻。钻头逐步深入,终于探到了灵魂深处。我“哇”地一声大叫,整个人几乎从治疗床上蹦下来。
“叫你别推人,你倒好,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我被重新推到那床上,医生吓唬我说:“别再乱动了啊,小心你的舌头。”这回我捏紧拳头忍着,一直在想象我听过的最悲惨的故事,想那些战斗英雄,耳边甚至出现了幻听,听见了机关枪的声音。这样挺过了一阵子,终于还是受不了了。那钻头直钻进“我心深处”,我的神经被搅得痛楚万分,不堪忍受。我真的挺不住了。人在疼的时候哪还记得什么该举左手还是右手。我把双手一齐举到半空中,嘴里哇里哇啦叫个不停。
“你的舌头还要不要啦?”
医生虽然戴着口罩,可是我看见她的脸像门帘一样“咔哒”一下放下来。她让我张开嘴说要给我检查检查舌头。她拉出我的舌头来一看,说道:“嗯,舌头破了一点,不过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她继续打开钻头给我钻牙,这一回我吓得抖若筛糠。既得保舌头,还得保牙齿,还得保神经。我躺在那儿孤独无助地望着天花板,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羊。
人到了最后境地也是最平静的境地。钻牙终于告一段落,我像获得新生一般地来了个鲤鱼打挺,迅速逃离现场。这天夜里,我展开病历细心研读。看病历这东西真是深有学问,现一字不落抄写如下:
诉:要求补牙
查:右,深龋
处:右,去龋后有一小穿髓点,氧化锌安抚,两周后复诊。
“安抚”两个字用得实在好,我的牙真的不疼了。但舌头被钻牙的家伙错了一下,说起话来总觉得不如从前那么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