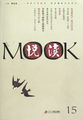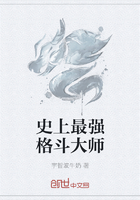西汉中叶以后,帝国已历数百年,基础渐固,在政治方面,不仅郡(国)县隶属关系渐强,郡(国)之长官对于一郡之事也渐有专断之权,形成史家所谓的“长官元首制”的地方行政,中央采信托方式,不仅委郡(国)守相一郡之行政、司法、财政、军事等诸事,于郡国之贡士,亦不加考试,即予录用。至成帝,原任监察之各州刺史已渐侵夺郡国行政权,遂正式改其名为“州牧”,加秩至二千石,使原为监察而设之州,一变而为行政区,郡(国)县二级制至此一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其后州之行政长官虽屡易其名,或称州牧,或称刺史,然其为一州之行政长官的性质却是一贯不变。
原来以郡国守相为元首的地方行政,随着行政区的变化,州的行政长官也渐取得一州司法、军事、行政、选举之权,而州对郡县之支配也随之加强。除了政治方面的变化外,汉中叶以后,统一帝国使人的视野与心胸随之敞开,活动范围不再局促于乡里,空间的扩大,地缘关系也随之扩展,甚至及于州、郡。人的乡里观念不再囿于户籍上的某乡某里,竟至及于州、郡,称乡人者非仅指户籍上同乡之人,乃泛指同郡或同州之人,而所谓州里之词,也渐与乡里同义。
东汉末、魏晋南北朝,为大一统后的分裂时代,中央政府微弱,地方势力高涨,王朝虽维持了表面对地方支配的形势,究其实,地方行政多为地方势力所左右。地方上有名望、有影响力之人,常出任州从事、别驾或郡功曹等职,彼等多为州郡民望所归,州郡长官于地方行政或倚仗其人而行,或为其左右。这些人多少是以地方利益为前提,也多少反映了州郡人民的愿望,他们是扩大的乡里意识中的民意代表,这时代我们所指的乡官便是这类州郡吏。
隋统一天下后,对于这类在地方上分割政府权力的乡官,自然不能容忍,先是于开皇三年(583年),不准他们问事,开皇十五年(595年)便有废乡官之举。此后,不管是州县(郡已于开皇三年废)长官或其下佐吏,除处理杂务的胥吏外,只要是一命以上的官或吏,全由中央派任。这与秦汉时代除州郡县长官,采取回避原则,不以本地人士出任外,其下之工吏全由州郡县长官至治所后辟用当地人的情形大不相同。隋文帝此举不仅剥夺了地方行政长官用人之权,也剥夺了地方人士参与地方政府施政的传统。但是地方人士,特别是地方上有力人士,对于地方政治、地方事务,绝不会因为被剥夺了参与地方行政组织的机会而打消其关心,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也绝不会因为不曾出任的地方政府的官或吏而消失殆尽。
在隋文帝历行集权中央及其以后的各朝代,历经了漫长岁月,地方势力终于找到与统一帝国沟通的道路,在行政组织系统外,获得他们参与地方行政的特殊地位。这就是在明、清时喧嚣一时的乡绅,他们在皇权下仍然伸展了他们在地方上的绅权。乡绅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现任、退任或正在休息等官僚于其乡里时的称呼。这些乡绅因其任官职位之重要、高低与活动范围及影响力大小而有省绅、县绅、邑绅等不同称呼。乡绅与统一帝国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曾是帝国的官僚,或是在乡里外正担任着帝国的官僚。但是在其乡里中,他们并不属于行政系统,他们是地方政府外的另一股势力,对地方政府是种抗衡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又可说是其乡里社会中属于庶民方面的势力,宋以后的乡官即是此类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