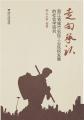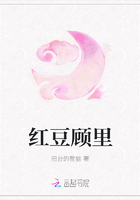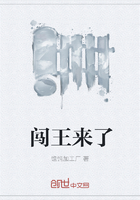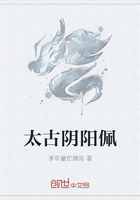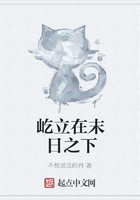北魏分裂而为东西,由高氏、宇文氏专政,进一步地各自篡夺政权,建立了北齐与北周。周灭齐、隋代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南下平陈,分裂了300多年的中国再度统一。不久,唐又代隋而有天下。
政权虽由关中这一支辗转传递,然而在唐代初年,那些统治阶层,包括皇室李氏,以及皇室左右的功臣贵戚,不是关中人士,就是元魏后裔,政治地位虽然很高,却未受到社会的重视,朝野各阶层所看重的,仍是山东士族。世人争与他们通婚,甚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李绩、张说、李敬玄、李怀远等,莫不竞求与山东望族婚姻。直到文宗时,情形犹然如此。文宗曾感慨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以李唐200年天子之尊,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可以窥见时尚之一斑。山东士族到唐朝初年,政治上已无权力和地位,人物虽众,却少杰出俊才;然而由于社会的看重,仍充满强烈的优越感,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就连大臣贵戚也争相攀附。太宗对此深所痛恶。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等奉诏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凭据史传,考其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有膏梁、左寒畯,合293姓,1651家,区为9等,号曰《氏族志》,凡一百卷。太宗看到崔干仍居第一,大怒,加以责备,并降干为第三等,诏颁于天下。唐室在以后还多次刊窜氏族,然而山东旧门并不因此受到影响,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如故。
陈寅恪以为山东士族之所以有些地位,实基于儒学德业,不因官禄高厚而见重于人。他们的家学门风,上循东汉以来能经义、励名行,然后从政的一贯轨辙。换句话说,只有山东士族才是真正的汉时旧家族,重婚姻、讲经学。汉末以后,新兴士族崛起,山东士族稍行见绌。然而经过几百年的物换星移,江东门第丧失原先精神而日渐衰微,关中门第亦因宇文氏政策而转趋胡化,唯有山东世家大族独能保持数百年旧传统,而未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愿得与众不同。他们虽然官卑位低,然而学养深厚,如崔祐甫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柳公绰家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门风之优美,不同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山东士族在唐初社会地位特高,实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