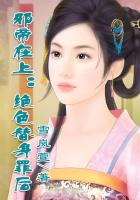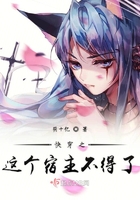要谈世家大族,就不能不谈中古的世家大族。在中古,世家大族成为历史的重心,他们关系到整个时代,风貌独特,性格鲜明。
然而,这些世家大族并不是由国家制定,而是在某些特殊环境中自然形成的。因之,他们不但具备家族的通性,亦各有其独特的个性。
在他们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先有族姓,次有门户,而后有了地望的观念:
族姓——门户——地望
这种发展是非常自然的。由于新族间强大的向心力,使同一祖先的人,不仅在血统上,而且在精神上,也凝聚在一起;家族的,尤其是姓氏的荣誉感,重于一切。而姓,实际上代表了这个家族,家族地位的高低,由姓表露无遗。
其后,由于家族丁口日繁,或由于客观的环境,逐渐分支,自立门户。虽属同姓,然盛衰互异,地位亦自不同。
由于环境的改变,为了与其他同一族姓有所分别起见,族姓、门户,与所著籍之地,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地望之观念因此而产生。
中古之世家大族,莫不具备此三者,缺一不可。
世家大族见诸载籍的,有很多不同的称谓。这都是由于性质、地位、环境、表现的不同,或是论者所持角度的互异产生,莫不有其实质上的意义。由于他们是士人的家族,故被称为士族;与其说是因任官的高下多少,而定世家大族地位之高下,不如说因家族历史的久远光彩为其先决条件,故有世族、世家、世门、世胄之名,而特为世所重。有些家族,人口众多,或声望极隆,故被称为大族;有些家族,人才辈出,历据高位,故被称为高族、鼎族、盛族、冠族、华族、右族、甲族、权族、贵族、贵势、贵游、门第、门地;或因其声华著闻,贵重无比,故被称为华腴、华齐、膏梁;有些家族,有名于时,故被称为名族、望族;而姓即所以名族,故有大姓、著姓、甲姓、右姓之称。这些称谓的使用,并非漫无限制,大抵是强调某一特质的偏学。至于泛称世家大族的,似乎只有氏族一词,在历史上使用得最为频繁。
世家大族不是一种制度,因为它既没有固定的组织形态,也没有经过人为的制定与规范;从称谓的纷乱,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存在。
前面提到过,中古暑期的世家大族必具备族姓、门户、地望三者,《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柳沖传”中,载录唐朝谱系学者柳芳“氏族论”的大要,论中将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依此三要素,区分为五个系统,同时举出其中最特殊的世家大族:过江则为侨姓,(琅邪临沂)王、(陈郡阳夏)谢、(陈郡阳夏)袁、(东海兰陵)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吴郡吴县)朱、(吴郡吴县)张、(吴郡吴县)顾、(吴郡吴县)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太原晋阳)王、(博陵安平、清河武城)崔、(范阳涿郡)卢、(赵郡平棘、陇西狄道)李、(荥阳开封)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京兆杜陵)韦、(河东闻喜)裴、(河东解县)柳、(河东汾阴)薛、(恒农华阴)杨、(京兆杜陵)杜为首;代北则为虜姓,(代郡)元、(代郡)长孙、(代郡)宇文、(代郡)于、(代郡)陆、(代郡)源、(代郡)窦居首。这种分别全然是柳芳所创,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的、这样分的。不过,这些名称虽属后起,但确能表现出各自的地域分布及精神特质,故广为后代所普遍采用。但在柳芳以前,世人心目中的世家大族,则与此大不相同。
晋初贾弼,笃好簿状,广集诸家,大搜群族,所撰18州士族谱,括116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梁时王僧孺集18州谱七百一十卷外,更有《东南谱集抄》十卷,不在百家之数,别为一郡。可见南方贾、王等谱学名家,所重但在18州116郡。隋志称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36族,则诸国之从魏者;92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阀阅,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按中国,即中州、中原的异名。亦即前述之18州116郡,东南、代北自当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