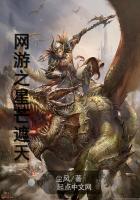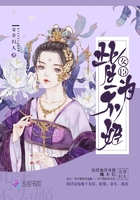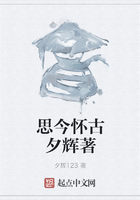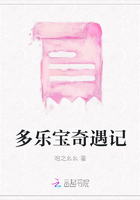东晋之所以能立国,可说是全靠门第,这自然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只是这时虽为门第社会,却非封建社会,故东晋立国与东周无殊,而结果稍异,既君权下移于门第,而非诸侯。
东晋门第享有的特权,比之渡江以前的西晋更多,他们可以自由地占山封水,不编户籍;不但随附他们而来的部曲宗党,蒙其庇护,逃避课役,甚至流民、逋逃人犯,亦多寄居大姓为客。他们不必缴纳正常之赋税,服正常之徭役,只需随意损纳。由于这些不编户籍的侨人数目庞大,自然影响到朝廷的收入。东晋朝廷历次下令土断,想把他们纳入编户,自不为侨人所欢迎;而从朝廷的三令五申,也可以考见土断的成效如何了。土断既不能顺利地推行,朝廷既无钱又无兵,一旦有事,还得求这些门第出钱出兵。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九品中正制更保障了他们出仕的优势。实际上,政权本来就操纵在他们手里。在东晋的100年历史中,门第中人相继执政,把持朝廷,不仅出将入相而已。天子名义上奄有天下,实则这些门第才是真正的主宰。主客易位,君臣易势,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元、明二帝时,王导、王敦相继当权,王氏强盛,有夺天下之心,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及成、康继统,又有庚亮、瘐冰专擅朝政,甚至操废立之柄。穆帝以后,直到简文帝时代,桓温且被修《晋书》之唐史臣讽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孝武帝时代,则有谢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至安帝初年,桓玄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端。
东晋享国百年,政权不出琅邪临沂王氏、颍川鄢陵庚氏、让国龙亢桓氏、陈郡阳夏谢氏四家,政出私门,权去公家。京兆韦华对姚兴说:“晋王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沈约亦称:“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门第固然取得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然而朝权、国命岂是容易把持?在动乱不安的时代、危疑飘摇的局面下,随着特权来的,是艰巨无比的责任:维系国家和民族于不堕,真是谈何容易。诚如所谓“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权力和义务是不可分的;当我们条举门第所享有的特权时,也该想想他们肩任之重,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的。





![[欧洲]中世纪教育思潮与教育论著选读(中)](https://i.dudushu.com/images/book/2019/09/28/0555160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