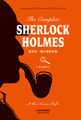她只觉得,做儿女的见到父母有难不能不管。
其实夏霏在很久以前,就有接父母去塘沽自己家里住的想法,但当时父母只有六十几岁,在儿子儿媳妇那里每天给做饭接孩子,也没有如现在这般凶险。所以,横竖他们说要照顾儿子脸面不能去。他们说既然有儿子,老的哪有平白无故跟着女儿住的?这不止坏了农村的礼数,而且也把儿子给寒碜透了!到头来在这三里村五里地儿的、他还怎么做人?怎么在这乡里乡亲当地混?岂不是让人家笑话吗?也不知他们那年代人的观念怎么会如此。
表面看是这样,或许二老还有别的原因吧。
毕竟夏霏知道,人越上年纪,越是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感。
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过去的环境,哪怕是委屈着过活,最起码大环境下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所以再委屈,内心深处似乎也是安生的。
他们风烛残年大概已经别无所求,只求身心能够安稳就谢天谢地了。
夏霏的母亲是个农民,没有退休金。父亲,曾是一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军人,民政局为了照顾他战争中曾经立过功,于是这套房子是以优惠五折的价钱得到的,但要求房契必须写成父亲的名字。而且政府还规定,如果年轻人来居住必须要带着老人。在小区里如果看不到老人,光年轻人来居住的,会以不孝顺为由,将年轻人一律驱逐。
面对此规定,儿媳妇也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这么多年,她总想千方百计想法设法,可以说使用了浑身解数,以各种方式将房本名字改掉,改成自己的。但是在政府那里无论怎么托人搭关系,也还是行不通。最后,她便只能每天盼望着这二老去死,尽快去死。
面对这么大的财产,而不是在自己名下?
此疙瘩,是她进门多年耿耿于怀忧心忡忡的。也经常趁着女儿们在大年初二齐聚之际,没少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当主题,兴风作浪大打出手闹矛盾纠纷。
夏霏居然还听家姐说,自父母来他家居住的那一天起,户口本和身份证便被儿媳妇没收了,父母活着都拿不到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打搬到儿子这里,也从来没见过自己的证件,他们俨然在儿子这里就成了黑人黑户。而且为了嘀咕这套房产,她用尽了心机。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后来,居然不知她在哪里托关系成功了,真的公证出来了一份白纸黑字的声明。那公正的内容就是——“如果父亲先过世的话,房子的继承权和拥有权,不能是配偶,是儿媳妇。”
而且还端端正正,稳稳扣上了权威机关政府部门的专用大章。
大姐嚷嚷到最后,似乎也只是落个说说。
叹息的同时,谁又能怎么样呢?谁能一个人说了算而能改变现实呢?夏霏只能是不停地劝着让大姐少想这些个家务闲事儿。让这些垃圾,在大脑中全然推走到一个角落,千万不要让此兴奋作怪起来……如若不然会影响睡眠健康的。
忽然,大姐家的电话骤然响起。
不单把大姐吓了一跳,这深更半夜的,也把一直沉浸于思索回味的夏霏吃惊。正在发愣间,大姐也放下了所有,赶紧去接了电话。
敢情这电话是老家村里姑姑的儿子阿喜打过来的。
电话里传来阿喜那热情高涨的声音:“啊,还没休息吧?”
“啊。没有休息,怎么?这么晚,是不是有事?”
大姐也在寻思着,姑姑不是早已经去世了吗?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可以驱使他那么一个不擅长交际,每天活在真空里的人能够午夜惊魂。
“哦。我是有事。我是有事。”
在他说着重复的话语时,举着听筒的大姐还偶尔能够听到他的旁边,似乎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小声嘁嘁喳喳,向他说着什么干扰。大姐一下子就明白了。莫非此刻就是他目前第二任又老又丑、拉家带口的东北媳妇在一旁操控着,正在教给他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正猜测间,只听到阿喜又说:
“是这样,我媳妇的二女儿要结婚。邀请你们全家和三舅,还有三舅妈都来参加婚礼,还有也邀请塘沽的亲戚全家都来我这里。下周六,便是正日子。”
接下来,夏霏便听到大姐在电话里,句句说的都是委婉拒绝的话语。
屋里这电话,也来不及再去多说什么,总之,夏霏只知道自从姑姑去世后,还有过去他的原配媳妇被他和母亲合力赶跑了之后,作为三舅这边所有的亲戚,便与依然还居住在小村里的他们疏于联络。
等大姐撂下电话后,转眼已经到了真正午夜了。
虽然姐妹一见面,还没有说够,没有来得及交流这家子目前的新状况,但的确已经很晚了。大姐和夏霏匆匆去了一趟洗手间……快速简单做着最后的睡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