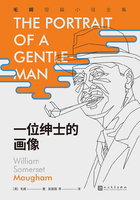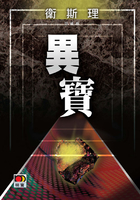一步步下了台阶,走过了百米外的冰层,眼前矗立的又是另一座雪山。
她不禁向上望去,这一座雪山高矮似乎与上一个类似,但是滑道却是更加陡直并且弯度更大。需要在征服大的弯曲后,才能够迅速,更直上直下地俯冲——这无疑更具挑战!
但他们刚跑到山顶,就见一对二十几岁的情侣共坐在双座皮圈内,竟然在俯冲下去时,由于冲力太大,进入雪道了后,皮圈又出其不意地冲出索道,将那条拦截的钢索围栏撞断,撞断后还不算完,接着又猛力飘移,被横贯出几十米远开外。
啊!好惊险啊!站在远处看的夏霏顿时惊愕了!
远处有几个身着红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迅速跑过来营救!
看到这些,她用手罩住了嘴巴,也学着雨冲从雪山顶上和俯冲下去的小华对话时的样子,围成了一个小喇叭,向上面连着喊话:
“喂…… 下来吧!”
但这偌大的空间,反光的白底色,衬着移动的黑点花点。上面究竟哪个才是他们两个?夏霏眯着眼睛调节着近视,再加上白色反光,依然无法看清楚。不过她敢断定,刚才喊也是白喊,他们肯定听不到。在这白雪苍穹里,这声音瞬间便被悄没声儿吞没了,于是最后无奈她只能用手向上比画。幸亏他们也瞧见了这个危险过程,为了不让夏霏担心,雨冲乖乖领着小华,顺着冰雪台阶走下来了。
噢!谢天谢地。她终于看到了十几米之外的雨冲和孩子。
“嗨!五点半了,够晚了!小华,不是说还要去别处玩吗?”她近前一步,提醒着玩兴不减的孩子。小华听了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退掉了皮圈。
夏霏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了所有家私,物归原主后,朝着出口的方向走去。雨冲不安地看着执意要走的夏霏,又笑着看噘着嘴执意就是不肯走的孩子,摸了摸头感到束手无策。小华站在冰层地面上,执拗了好一阵儿,才慢腾腾朝出口方向走去。
雨冲紧紧跟着孩子,走在夏霏的前面。
此刻,她不知怎么了,忽然莫名产生了一股冲动——此时她竟然很渴望去牵他的手,于是她便果然将右手伸了过去,这么大胆主动生平还是第一次。此刻她的头部嗡嗡的,紧张空灵得几乎不会了思索。但是这种冲动,却压迫着自己必须斗胆去做这件事,似乎在催促着自己立刻去追逐着完成一个美好的梦境或夙愿。
但当刻意碰触到时,只有一点点,可,他却躲闪了。
这究竟是有意拒绝,还是无意中碰巧的下意识动作?一股难言的絮状物,便于夏霏的心中不断掠起并升腾。
但置身于现实的她,便也很快又转移了心神。
他们曾经在网聊时,探讨过空中接吻,就是要在下一个去处——摩天轮中进行。这也是夏霏需要严格控制时间,不顾孩子意愿,执意去摩天轮的原因。虽然几小时前,在玫瑰花园那五平方米的厨房里,她并未在接吻中体会出任何乐趣,但现在她却毫无理由地渴望着。
难道是为了体味好玩?是为了追求新鲜感?是为了寻找一种方式来刻骨铭心?到底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总之在情感的诸多方面,自己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想来想去最后头都大了也没有个所以然。但她清楚自己的思想经常会在现实与想象中遨游穿梭,经常会在分裂与挤压中茫然,经常会在顺然与矛盾犹豫不知所措中撞击……所以她时常也不是很了解真正的自己。
在路边拦住了的士,往摩天轮的方向奔去。
但现在是五点半,到那里估计已经六点多了,空中依然是雾气霭霭,根本望不出去。一整天了,夏霏就从没见到过太阳,回味起来,只觉得那个滑雪场内的冰雪苍穹,反倒是清澈明亮通透的。此时车子向外环线以外不停地飞进,终于在没有摩天高楼的干扰之处停了下来。
夏霏拿出钱包,争抢付了50元车钱,因为她不好意思总要雨冲来破费。
她们终于见到了传说已久的摩天轮!但浓重的雾气,依然还是遮挡住了它真正璀璨的光辉。
他们三个人兴冲冲地走进等候厅,结果等待了半个多小时,才允许进入摩天轮。他们缓缓钻进了空中悬挂着的小笼子里。这次乘坐摩天轮,对于这里的特殊规定,无疑令夏霏和雨冲失望了:包厢必须是多人乘坐,至少五个人,并且没有三两个人的单间。
于是在孩子于空中不知疲倦胡乱走动时,雨冲还不停地斜眼,躲着旁边呆坐着的那一对情侣,偷偷向着夏霏调皮眨着眼睛,并吐着舌头做着鬼脸怪样,似乎是在对夏霏提前未见面时,电脑聊天时出的馊主意、无限讥讽嘲笑。
夏霏只有用眼睛瞪他,其实此时她的内心是失望的,而且迫切希望尽快离开这里。尽管在这冰冷的笼子里只在空中晃悠了半个小时,但也好比是经历了半个世纪般煎熬难过,这让她第一次有了虚度光阴糟蹋时间的感觉。无聊之余,她想为孩子拍张照片,可因为空间狭小,只能拍个大脑袋,而且也没有背景,毕竟笼子外的空中是昏昏暗暗的雾霾,索性便不拍了。这么大的摩天轮,竟然连个音乐都没有播放,她静静呆坐在那冰凉的铁椅子上,顿感了然无趣并且无限抱怨着。
好容易从这里走出,看了一下手机,已经晚上八点了。
哦!已经很晚了。他们迅速来到了公交车站,在这里足足又等了半个小时,才坐上了起始点的公交车,缓缓向着玫瑰花园方向前行。
可是夏霏怎么办呢?不是今天暗暗计划着走吗?估计晚上10点钟也会有通往塘沽的轻轨,她只能如此侥幸地想。但这公交车通向玫瑰花园的路,怎么会如此没完没了?雨冲与自己隔着一条半米宽的通道,孩子与自己并排紧挨着挤在双人座上,公交车像个老爷车般晃晃悠悠。此时又累又困的孩子,好几次险些要睡着了,依着公交车的惯性,头部差点儿撞到围拢到前面的粗栏杆。
“快到了吗?……”她向着只隔一个通道的雨冲,焦急地询问。
“快啦……”他回答得总是蛮有把握。
车窗上凝结着很多的雾气,看不清外面太多景物,只感觉窗外有许多亮光点点在灵动闪烁。但这闪烁的光芒被雾气影绰着有些拖泥带水,显得并不十分犀利,不可以穿越得很远。这样的璀璨朦胧景致,倒是让她感觉到别有一番韵味儿。
这些,也让她自然想起了在六里台天津师范大学北院读书时,深夜里在八里台和六里台之间骑自行车回学校的情景。那时她们乘着夜色,骑着自行车,惬意领略夏日的凉风。那时她们是那么无忧无虑,那么自由自在,那么能够主宰把握自己生命空间里的任何琐碎,而且总是那么游刃有余。哪怕是风吹草动,是微不足道的一分一毫。
初到大都市里来的夏霏,面对着黑夜里的闪闪烁烁便会吟诵几句:
“蜃楼海市落星雨,火树银花不夜天……”
似乎只有拉长了音拖长了拍才够足了味儿,最后,才可以将翻滚着的热情,迅速拍打到周身末端上去。
高个子美女刘娟永远是第一个支持她的。
只要话音一落,宿舍长刘娟便总是第一个拍手:“嗨!绝了!”
然后单手扶车把,朝着夏霏竖起了大拇指。
转眼大学毕业了,在同学们依依惜别之时,她还没有忘记在刘娟留念册的第一页上,舞弄了两行——“蜃楼海市落星雨,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诗句!
相信无论时隔多年,当她们拿起这本毕业册时,仅此两句,便足以敲开这“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时记忆的闸门。任凭眼泪潸然的同学,无论历经多少校园以外的无数过往的烟云,记忆中也会如潮水般奔腾不息,闪烁着——那时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