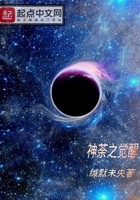潘道延在第一时间从惊恐中突然回过神来。
就在吴元厚倒下去,吴家所有的人扑向老爷的时候,只有潘道延一个人不顾老爷死活,转身把那幅画摊开来放到地上。
潘道延俯身看了一眼那幅画;第一眼,他脑子“轰”的一下,顿时浑身痉挛发抖。刹那间他第一感觉是这幅画好像有点不对,不是原来他从吴家拿出去给朱红看的那幅原作。这一瞬间他脑子里一闪而过:朱红暗地里调了个包?他随即趴到地上看;这一看,他脑子再次“轰”的一下,好像五雷轰顶把他吓得半死!他的感觉像闪电一样倏然又回到先头的第一眼感觉上。
这时候潘道延已经断定:眼前这幅画不是自己先头临摹出来的那张。他曾经在自己的仿作上做了一个非常暗的记号;他没有跟朱红说,没有跟任何人说。其他人凭肉眼寻找那个记号,好比大海捞针。唐寅的《落霞孤鹜图》原作他忒熟悉了。眼前这幅画是假的。他感觉这幅画有那么一种感觉有点不对;究竟是什么不对?他一时说不出来。
其实,在吴元厚当时看这幅画的时候,潘道延已经瞟了一眼。不过,他当时跟阿仲一人一头拿着画轴,他站的位置是反方向,人立在画面的顶头,第一眼直觉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再说,他那个时候好像有点走神,有点漫不经心心不在焉,心里想是吴先生看,听吴先生说说怎么看而已。吴元厚说:“假的。怎么会假的?”这个话,潘道延听见的,当时他一怔,没有反应过来;吴太太、吴天玉、阿仲、明香也听见的。随后情况突变,他们注意力集中在老爷身上,这时候没人注意潘道延,只有明香无意中一个转身,看了他一眼。
灵堂布置好,吴太太从悲痛中回过神来;明香、阿仲扶她到外头一间坐下来喘口气。这时候吴太太首先想到的是,吩咐阿仲打电报给少爷;接下来想到的是老爷临终前说的那句话:“假的。怎么会假的?”
吴太太不懂字画什么真的假的,问女儿,吴天玉也不大懂;阿仲明香是更加不懂了。吴太太说:“待会儿问问阿延,是怎么回事儿?”这时候潘道延已经魂不附体,像个精神失常的病人坐在灵堂里,木呆呆地盯着吴元厚脚跟前的长明灯看,任你怎么问他,他面无表情没有任何反应。
明香把阿仲拉到外头,小声说道:“不去理他,让他去。”
阿仲跟着明香走,一边轻声说道:“老爷有一句话我记得清爽,说他这次到南京去,看到金陵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唐寅的《落霞孤鹜图》,老爷说‘那件东西假的。真的,在我家里。’”明香一怔,说道:“我也想起来了。老爷当时问‘阿延,《落霞孤鹜图》还在你画室里是不是?’——哎,会不会是阿延暗地里鬼虚鬼虚的出了一个什么花头?”阿仲这会儿也起了一点疑心,说道:“记得老爷到南京去出差那天,我在园子里看见阿延拎了一个布袋匆匆忙忙出去,里边装的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我当时随口问了一句:‘阿延,你到哪边去?’他说‘到城里去一趟’。当天阿延他回来,是我开的门,他好像是空着手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到乡下去了。这次阿延回来,他又把那个布袋装了东西带回来了。”明香听了,回头把阿仲说的这些话传给吴太太听。吴太太一听,眉头皱起来说道:“阿仲也是的,没话寻话说。把阿仲叫过来,我来问问他。”
吴太太回头一想,有点纳闷,跟阿仲说:“老爷先头说那幅画真的;后来他一看,又说假的。这个弄不懂了。会不会是老爷自己弄错了?”阿仲回道:“别的我不敢讲,老爷看唐伯虎字画,真的假的怎么会错?不可能的。”
“老爷看东西就这么准?比南京的顾大仙还要仙,还要厉害?”
“顾大仙本事大我晓得,反正老爷不会错——”
“是人,总归会有错的。阿仲,你就这么肯定?”
“太太,我还是有点怀疑阿延,……家里,除了他,没有人碰字画。”
“这……”
“这个事情,要么少爷回来,问问少爷看?”
“天泽又不在家里,他怎么会碰那幅画?”
“不是这个意思,太太。——我说的意思是,少爷懂字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儿,兴许少爷搞得清爽……”
“等他回来我来问,你们不要问。”
“是,太太。”
“这些嘀嘀咕咕的闲话现在不能跟小姐说。”吴太太关照道,“家里有些事情是不好瞎讲的。再说了,现在也不能瞎猜疑。这个事情等天泽回来再说。”
“嗯,”阿仲点头道,“太太放心好了。我是绝对不会在小姐面前瞎讲的。倒是明香你,嘴巴要紧一点。”说着,看了明香一眼。
“这个不用你阿仲关照。”明香一嗔,说道,“有些话我是跟太太说的,跟小姐是不会说的——你放心好了。我这会儿就把嘴巴闭上,一句话也不讲。”
“千万不要在小姐面前说阿延,听见了没有?”
“晓得了,太太。”
“现在你们也不好把阿延想得那么鬼……”吴太太说。“嗯,”阿仲身子向前一躬,头一点回道,“不去乱想……也不敢想。”
如果吴天玉听到背后这些闲话,这会儿她是不能接受的。
吴天玉觉着她父亲是猝死,是一个意外,跟潘道延没有关系;眼下要自责的首先是她自己。在她看来,父亲的死她是有责任的。如果她不让父亲吃酒,父亲肯定会听她的,只要她撒点小姐脾气。一想到这一点,吴天玉不能原谅自己。她心里想,她最多这么想:“如果阿延这次回来,不买两瓶老酒就好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不能怪阿延,要怪,只能怪我……”
内疚、悔恨挥之不去,加上极度悲伤,这时候吴天玉已经哭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昏昏沉沉地待在她父亲遗体边上。她要陪陪父亲,她心里想;这会儿她心里边空落落的,像一张空白宣纸。
吴家在惟亭不是一般人家,外头人好奇,觉着吴家一天到晚关着门,有点神秘兮兮,弄不大清爽这老宅子门里头,这高墙后面的人和事情。有人看见这几天曹中医从吴家进进出出,这会儿外头闲话随之而来:
“听说吴先生坏掉了。有人讲他血压高,不好吃老酒的。吃得多,闯祸。他是吃老酒吃死掉的——”
“瞎讲!吃老酒不会的……这个,跟吃老酒没有关系。我也吃老酒,天天要吃的。我已经奔七十岁了,身体不是蛮好么。”
“可能是别的原因,生什么疾病?”
“曹中医讲,有可能是脑溢血引起的,头上充血,血管一下子爆掉。也有可能是心脏不灵,血管不通,心肌梗塞,骨碌一记去掉。”
“我问过曹中医,还是曹中医的讲法比较可信一点。”
“吴先生年纪也不大,今年大概五十岁模样;这么大的名气,没想到寿命短哦,蛮可惜的,可惜哦。”
“家里人肯定难过得不得了。家里一棵大树倒了。想想人没有意思,真的没有意思,说走就走。”
“前一阵子看他身体不是蛮好,怎么回事啊?听说吴先生平常一直有点不大开心,闷闷不乐……”
“也有可能是被儿子气的。他儿子,我听隔壁邻居讲,老早有点不学好。吴先生吴太太弄不过那个儿子,心里不开心。”
“儿子女儿好,蛮要紧的。要不然,做爷娘的被他们气煞掉!”
“吴先生有个学生子一直在吴家,一天到晚看不见他人影子,不声不响躲在屋里跟吴先生学写字画图。吴先生的女儿也一直躲在家里,不大看见出来。难得看见她到街上来走走,人长得漂亮哦。”
“哦,吴家小姐,讨人欢喜,人蛮好的。吴先生吴太太欢喜那个女儿,当宝贝。听他们家里丫头讲,他们家少爷不在家里,在上海……”
第二天上午,吴天泽正在屋里画画。
他一边画,一边跟约翰王聊天。这天是礼拜天,约翰王休息,一个人跑过来看看吴天泽。说话时,突然听见房东阿姨在外头喊道:“吴天泽电报!”
吴天泽到门口收了电报,回进来,也不马上拆开来看,随手把电报往画桌上一扔,对约翰王说:“前天我父亲写信来,叫我回苏州去……”说着,他拿起毛笔继续作画,“我这两天帮人家画一幅山水,没有空,还没有给家里回信。这会儿好了,家里打电报了,肯定是催我回去。我现在不想回去,一个人待在上海蛮好,写写字画画图;有空跟朋友吃吃茶,吹吹牛。家里有什么要紧事情?还要给我打电报,弄得像真的一样——”
“哎,吴天泽,”约翰王瞟了一眼桌上的电报,说,“你还是先看一下电报再讲。如果没有什么急的事情,一般来说是不大会打电报的。”吴天泽一听,这才放下毛笔,把电报拆开来,一看:
父去世,速回!
吴天泽手一抖,嘴巴张了张:“啊?啊,啊!”随即猛地“哈”一声道:“怎么可能?!”约翰王吓了一跳,从凳子上弹起来,一步跨到吴天泽面前,问道:“出了什么事情?”头凑上去一看,“喔唷”一声。
吴天泽头一晃,眼睛眨巴了一下,盯着手上的电文看。约翰王急着说道:“就五个字,有啥看头?快点回去!”
“我父亲,他怎么会突然去世呢,啊?”说罢,吴天泽手忙脚乱拿东西准备走。约翰王要了吴天泽苏州家里的地址,说:“你先回去,我到时候看,抽得出空,我就到苏州去一趟。实在抽不出空,我写信给你……”
两人一道出门,约翰王执意要把吴天泽送到上海火车站。
“太太,少爷回来了!”明香的一声哭泣叫唤从门外头传到里边。这一声揪心得很,吴天泽顿时觉着天塌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意识到:对这个家他是有责任的。现在他回来了,而他父亲却离他而去。
“如果我提前几天回来……”吴天泽心里想,“如果一接到父亲的信,马上回来,能见到父亲,什么事情都好商量,都可以商量……”这会儿吴天泽脑子里忽然闪过先头在路上自己的胡思乱想,其中有一条,他觉着他父亲是被他气坏掉的。他突然想到自己曾经差一点把母亲气坏掉。
“老爷,天泽回来了。”母亲一声怆然泪下,教他无地自容,欲哭无泪!
“啊,啊,啊……”吴天泽“扑通”一声跪在他父亲遗体边上;他伤心,难过到极致,嘴巴张了张,连续发出短促、粗重、高低起伏的声音;他母亲、他妹妹,用人阿仲、明香在边上看了,一齐失声痛哭……
“阿延呢?”待到阿仲明香止住哭泣,分别劝住了太太、小姐,吴天泽从地上爬起来问道:“哎,阿延呢?”
“阿延,——他不在。”阿仲看了吴太太一眼,回道。
“怎么不在?”吴天泽一怔,坐下来接过明香端上来的茶碗,一转眼接着问道:“他人呢?我回来到现在还没看见他——”
“阿延他——”明香嗫嚅道:“他今天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到哪边去了?”
“我不晓得。”明香看吴太太脸一沉,吓得不敢说话;憋了半天才说:“这个你要问小姐。他跟小姐说过一句,他要出去一趟。”
“不要问我。”这时候吴天玉憔悴得很,脸色煞白,回道,“阿延他今天到哪边去我也不晓得。他什么也没说,就说了一句:‘我出去一趟,要的!”
“嗯。”吴天泽吃一口茶,略一沉吟,头一抬,说,“妈,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下……”吴太太觉着儿子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嘴巴上说是跟自己“商量办事情”,实际上他在安排,在关照家里人——
“上海的傅家佑先生要通知的,”吴天泽看了妹妹一眼,说道,“这个电话天玉去打,我有傅先生家里的电话号码——待会儿就去打。傅先生是爹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他一定要来的。第二个要通知的,是南京的顾大献先生。打电报,金陵博物院顾院长收。这个,阿仲去办。阿仲,你现在知道怎么拟电文?”
“知道,少爷。”阿仲头一点,回道,“写六个字‘老爷去世快来’!”
“不这样写,”吴天泽手一摆,说道,“你现在照我说的写‘吴元厚先生不幸去世’九个字——这是讣告。讣告的‘讣’字,知道啵?”
“知道,少爷。”
“我们本地,”吴天泽轻咳了一声,似乎已经想好了,说道,“唐楼的唐先生要通知。这个电话天玉你来打,打给唐小姐。还有一些亲戚……最后就是叫阿延写封信跟他家里说一声。他家里别的人,来不来随便。但是阿延他爹潘新侬,照我的意思一定要来的。……好了,就通知这些人。明香,你待在家里陪太太,有人来,张罗照应一下。吃饭,家里不要忙了。待会儿阿仲跟镇上馆子说一声,订好了,叫他们把饭菜送过来……”
“那么你呢,吴天泽?”这会儿吴天玉脸上稍微有了点血色,问道,“你关照这个,关照那个,你做什么?”
“我,”吴天泽端起茶碗吃一口茶,慢慢地把茶碗往桌上一放,看了一眼墙上日历,淡定说道,“我坐镇家里,有什么事情你们来跟我讲,我来处理。”
略一停顿,吴天泽接着说道:“哦,还有,我们家向来不欢喜外头人随便进来。这个,阿仲你要盯着点,有其他人来,要跟我讲一声。”说罢,吴天泽一转脸,对他母亲说:“就这样。妈,你看呢?”
听到儿子这会儿在问自己了,吴太太舒了一口气,稍微怔一下,点头道:“就这样。”随即一转眼,说道:“阿仲、明香,你们就照少爷说的做。眼下也难为少爷了,长到这么大,头一回经历这种事情,现在这样把事情安排好,已经是不容易了。”吴太太看了女儿一眼,一想,接着说道:“天玉,打电话跟唐小姐说,就说吴天泽回来了。叫她有空过来,一来是陪陪你;二来是我们家里现在也需要帮忙,请她过来帮帮忙,不知道唐小姐肯不肯?”说罢,吴太太眼圈一红,看了儿子一眼,随即手捂住嘴巴,声泪俱下:“老爷,天泽回来了,他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吴天玉、阿仲出去办事,吴太太单独跟儿子说话。吴太太说:“天泽,你没有回来之前,家里边就阿仲一个用人,一个男人里里外外忙出忙进。我,你妹妹,还有一个丫头明香,全是女人,哭得昏头六冲,六神无主。本来还指望着阿延担当一点,没想到这当口,他昏头昏脑木知木觉的,一点用场也派不上。这会儿,不知道他一个人跑到哪边去了。你说他没良心吧,不见得;你说他不懂吧,我看他也蛮懂事的,就是不知道他这次从外头回来,人神经兮兮的,真的弄不懂他。哦,对了,有一个事还没来得及跟你讲,阿延他娘两个多月前去世了。……还有,你爹上个月到南京去了一趟,待了一个多月。回来那天,人好好的……过了几天……就是那天,阿延从外头回来的那天,吃饭的时候出事情的……”
吴天泽听母亲这么前后一说,沉吟半天,说道:“阿延的事情现在先不去管他,那幅画回头再说。眼下要紧的是阿延人在哪里?把他找回来——”
“到哪边去找?”
“哎,妈,你刚才不是说阿延现在在城里谋生,住在人家家里么?——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很简单,叫阿仲去找一下。”
“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只知道他住在城里边。”
“你们不知道,天玉应该知道。阿延总归要跟天玉说的——待会儿天玉回来我来问她——说不定她知道了,不告诉你们。”
“哎呀,问题是天玉也不知道。她要是知道,这个事还来跟你说什么,我早就叫阿仲把他找回来了,还用得着你讲?”
“这个事情先放在一边,回头再说。”吴天泽立起来走了几步,转身又坐下来说道,“妈,我看你乏得很,这会儿我在,没事,你到房间里去歇一会儿。”一转眼,见明香过来,吩咐道:“明香,待会儿帮我拿一件干净衣服,我身上这件衣服要换一换。”
“是,少爷。”
“给我重新泡杯茶——我要吃茶。”
“嗯,少爷,我马上给你泡。”明香说罢就去做了。
唐小姐接到吴天玉电话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赶到惟亭。
这是唐小姐第一次去吴家。去之前,她在家里也是颇费思量的。有一点她没想到,人生安排她第一次到吴家去,是去吊唁——她本来期待的是“应邀前往做客”——她想她应该去,一个人先去,而不是改天跟她父母一道去。唐太太跟女儿说:“你还是跟我们一道去。你一个人先去,好像有点不大妥,算什么呢?”
“怎么了?有什么说法吗?”唐小姐问道。
“说穿了是个身份问题。”唐六梓想了半天,对女儿说,“照老法规矩,没过门的媳妇是不好上门的。你还没有跟吴天泽定下来;这回是他们家办丧事,这个说起来总归有点不大好,我觉着。”
“哦,原来还有这个说法。”唐小姐一想,不以为然道,“我不懂。但是这有什么关系?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还讲这一套,没有道理。”说罢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