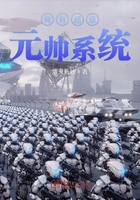因米芾另著有《书史》,所以在诗中对书法理论的阐述与书法作品的品评并不系统。米芾在书法方面推崇晋人,由兴波:《米芾的书法艺术观》,《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第191—193页。心慕魏晋风流,如《寄薛绍彭》一诗中对欧、褚、柳、张、怀素、智永等大加贬斥,对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书大加推崇,认为应以晋书为学习典范。究其深层,米芾乃是喜爱晋人及晋书那种自由挥洒的气度,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米芾还经常用诗的形式来品评书法作品,如《寄题薛绍彭新收钱氏子敬帖》、《刘泾收得子鸾字帖云是右军余恐是陈子鸾薛绍彭亦云六朝书又得像余时在涟漪答以诗云》诸诗,对书法作品予以品评、鉴定,起到了题跋的作用,扩大了诗歌的功用。可惜这类诗多是应请或题跋之作,艺术性不高,缺乏其山水诗中的清新之气。
唐诗重“情”,宋诗重“理”,宋诗中处处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形成了同唐诗迥异的审美情趣。在宋诗中的才学、议论等等,都是宋代文人苦心经营、多方求索才形成的独特面貌。在“晋尚韵、唐尚法”之后,宋书想要有所成就,一定要突破前人成法,要同诗歌一样,创造出有自己时代特色的书学风貌。有趣的是,宋诗在唐诗的重“情”之后开始了理性的思考,而宋书则在唐书尚“法”之后开始了任性抒情。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部类形成宋代文人在精神世界的互补:他们在用诗歌进行理性思考的同时,用书法来感性地抒发情绪,这样便在心理层面形成了互补与平衡。苏、黄、米三人的书学思想及论书诗构成了北宋书学理论的主体,并开创了宋代书学的新风貌。
二、南宋论书诗的发展——个性衰微与理论变迁南宋书学理论研究与论书诗创作远逊北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号称诗歌领域“中兴四大家”,其中陆、范在书法方面成就颇高。书法方面的“中兴四大家”指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同样有一定的成绩,这一时期的诗、书相结合问题值得关注。陆游为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书法和诗歌一样,寄托着饱受精神压抑而欲一吐为快的强烈感情,在诗歌史上和书法史上都以能提升精神为特征,殊为可贵,否则宋诗和宋书的精神早已衰落。陆游现存二十余首论书诗中,近半数是有关草书的。他将难以排遣的忧愁与苦闷通过酒、草书与诗歌抒发出来,不同的文艺部类都成为他宣泄情感的有力载体。陆游一腔爱国热情贯于诗歌之中,论书诗也不例外,如《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醉中作行草数纸》等,都是“醉”后作草,使情绪得到了充分释放,但与书学理论相去较远。
南宋书家有成就者多集中在爱国诗人身上,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等人,都属于诗不能尽达情,溢而为书,是以在书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朱熹对诗歌和书法的影响都不可忽视,理学思想对二者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追求一种中庸的创作,诗歌和书法的个性都显不足,但由于后期皇帝对理学的支持,对时代风气形成了一种指导性的影响。
南宋后期有成就的诗人和书法家则罕见,仅岳珂在唐、宋论书诗创作上占有特殊地位,其现存论书诗近二百首,从数量上看为唐、宋两朝最多者,但在书学理论上建树颇微。岳珂在书法品鉴及收藏、文献整理等方面成就卓然,他还创作了六十余篇赞,其中孕有较系统书学思想。南宋书法创作走向了低谷,在书论方面却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姜夔《续书谱》等著作,也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了。
文艺思想嬗变溯源
梳理唐、宋论书诗可见两朝文艺思想嬗变有一明晰线索:由感性体悟至理性思考。究其原因如下:
1.唐型、宋型文化的特质不同,进而影响本时代文艺思想之走向。台湾学者傅乐成教授曾于1972年发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指出唐、宋型文化的区别所在:“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据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见《国立编译馆馆刊》第一卷第四期,又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一个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的新的质变点。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服胡麻赋〉注》中认为本朝文明“前世莫及”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00页。,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则云:“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书店,1983年,第70页。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亦认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当今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更断言“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第137—144页。对于“空前绝后”这样不免带有绝对化色彩的赞语,我们后辈学人或许可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和补充,但也很难达到他们的直觉表达所蕴含的对表述对象的深层把握,“然则宋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成熟型的范式,应是没有疑义的”。王水照:《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在唐、宋这样伟大的文化时代,产生了诸多“文化人”。所谓“文化人”是指在学术、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多个领域都有突出成绩、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复合型人才。唐代如贺知章、张旭、李白、王维等,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均为代表人物。诸多文学、艺术领域天才般人物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对于这些“罕见的全才”王水照:《“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的研究不应只是单一性的,而应对其文艺思想做以综合性的研究,从而发现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未完全显现的观念与思想,并借此透视出时代的文艺思想脉络。蒋士铨《辩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十三,清咸丰蒋氏四种本。这两句评价宋诗之语亦可用于宋代文化。盛唐之音的代表艺术家李白、张旭等,多以不可遏止的激情来抒发对盛世的体悟,放旷豪迈构成这一时代文艺的主旋律。而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之身份有一与唐不同之特点,即多为集官员、学者、文士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比唐人更格局宏大、渊博精深。这一时代的文艺家具有浓重的知性反省的思辨色彩,对文艺思想之探求也更趋深入与理性。
2.文艺形态的差异使唐、宋两代文艺思想也呈现出不同风貌。首先探求唐、宋诗学思想的变迁。唐人重情,宋人重理;唐人重感悟,宋人重思辨;唐诗更多展现诗人对生命的体悟,宋诗更多表达对生命的思考。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认为:“唐诗充满了激情。我觉得,经过唐以前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可谓抓住了唐、宋诗歌中主导特征,激情的被抑制使唐诗的感性体悟至宋诗转为理性思考。其次,唐、宋书风的变化对文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晋韵”是唐人歆慕并孜孜以求的,在两晋书风影响下,唐人更多的突破在篆、楷上,重“法”是唐代书法的典型特色,而唐代论书诗则基本上歌颂草书与擅草书的书家,这是在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上产生了偏离现象。唐代论书诗更多地体现书家、书法作品的神韵,追求这种艺术活动带来的精神愉悦感,与大唐风度的自由精神相吻合。宋代书法更多追求对书法内在精神意蕴的理解,而非局限于点画之间,尚“意”是宋代书法的典型特色。宋代论书诗更具有理性特征,对书法作品的技法探讨明显增多,体现出宋代书家的复古与创新取向,既有书法方面尚“意”特征,又兼宋诗尚“理”风格。
在唐代论书诗中更多的是诗人对书家、书法作品的主观感悟。唐代诗人与书家交往频繁,促进了诗歌、书法两大文艺部类的繁荣,一人兼而为诗人与书家的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如张旭、李白、贺知章等,但更多的是进行书法创作而非书法艺术的深度思考与理论探索。宋代书法在“唐法”之后提出了“宋意”,力求开创属于自己的一代书风。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书家更多地对书法内在的意蕴进行思考,对“晋韵”的追求与对晋、唐书法的批判共存。北宋以来,诗人、书家集于一身者明显增多,他们不但进行诗歌、书法创作,而且进行诗歌思想、书法理论的深度探索,力求诗、书都在唐人之后开辟新路。唐代论书诗多为描写草书之作,宋代论书诗在题材方面草、楷、篆皆有,且从外在点画、风格乃至内在神韵等均有探讨,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使宋诗学理化,论书诗中融入对书法艺术的理论思考使诗歌更具艺术气息,形成颇具宋代风格的文艺思想,而唐人的艺术思想在理论阐释上则不及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