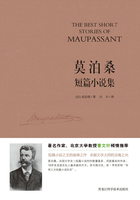她神色冷淡通透,判若两人。两道淡漠的眼神宛如一束红外线,穿透过这个物质世界。倏忽间又活象是一对玻璃球体,眨闪着木然的亮光。
“你心情不好?”他问。
她莞尔笑了,“你看得出来?”
“我感觉到的。”
她垂下头,“我相信。”
他们很少见面,要不是选接班人的事她也不轻易找上门来。天造地设,他俩竟又有机会相聚在一块儿。每次见面,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多看她几眼,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依然那样光采动人的漂亮的脸,还有那文雅的落落大方的风度。他还察觉到她身上表现出来的成熟感,显得她更美丽庄重。然而在他面前这美丽的庄重好象一下子淡薄了许多。这种淡薄却又使他感到一种潜意识的舒畅。
他很想见她,那怕是只呆一会儿。见面时的舒畅心情里却又隐隐地飘着一缕儿绵绵的悔恨,悔恨他自己,也悔恨这个世界。自从听闻她被抛弃之后,这种悔恨就象吸水的棉团越来越沉重了。她年纪轻轻的就独自一个人带着儿子度过了十几个冬春。她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泻在儿子身上去了。她孤独地生活着,这孤独是一种忍受,也是一种忍受着的爱。他暗地里为她祈祷,祝愿她找到一个合意的人。然而,她好象看透了他心灵一样,依然孤独地过着。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对不起你。”他负疚得声音也颤沉沉的。
“一切都已忘却了!”
“那你……”
“孤独吗?习惯了。”
他惊愕地望她一眼。
“失去的东西多了也就习惯了,连灵魂、人格,自尊都失落过了。”
他苦痛得抬不起头来,紧闭着眼睛说:“他不是来过么,也许他明白了过去……。”
她冷笑了笑:“他吗?占有也是一种习惯吧!”稍停一会儿,她摸了摸那只带着朵白云的母指甲盖儿说:“他没想到我这里没有一点儿蜜糖。”
他感到一阵心灵的痛楚,顿时觉得自己变得矮小老朽了。他责备过自己,也埋怨过命运,可从没想过这责备也是个习惯啊!他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责备过自己吗?
当他察觉自己悄悄地在心里爱上了她的时候,已是考过高中结业试了。接着他照着她的志愿填报报考清华大学,出人意外的两入都上了录取线。他高兴极了,心里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世界上处处洒照着阳光。接到录取通知的当天晚上他给妈说,她没做声,拿着通知高兴得流下了泪水。三十多岁的年青寡妇伏在床上泣咽了整整一个晚上,烟黄了的蚊帐在黑暗里簌簌地抖动,她应该高兴儿子有了出人头地的黄金际遇,对得起他死去的爹,在祖祠灵牌面前也抬得起头了。
他兴奋极了,但却睡得很甜。他给母亲带来了最深厚的安慰。
翌晨,他惊愕住了。一夜天光,妈竟变得消瘦憔悴了,头发也一片灰白。
“北京有多远路?”她问。
“坐火车要两日一夜。”
“人走呢?”
“差不多两个月。”
“哦……”她哗的一声哭了,就象失去了儿子似的痛哭了起来。
他慌忙地扶着她。
“路太远了。”她睁着泪眼,“那边冷吗?”
“下雪。”
“听说冻得耳朵也掉了下来。”
“戴上帽子就不会了。”
“要是忘记了哩……”她又呜咽地哭了。
他顿时也心慌意乱了,“妈……”
“离家这么远,你有个病痛差错的话,要我怎个活呀!”
“妈,不会的。”
“妈舍不得……”她抱着儿子大声地痛哭。
“……”
他忍不住地掉泪了。
妈妈也有自己的难处。他家五代贫农,四代单传,轮到了她身上,虽然早早死去了丈夫,但终算保护下李家的一根独苗子,在祖宗灵位面前可以交代得过去了。到黄泉下同他爹见面时也问心无愧。她最大的希望是保护好儿子,让李家的香炉一直香烟缭绕。她也想过计划生育的条条,心里非常害怕,担心这香炉有熄火的一天。可是细心想想那是儿孙们的担子了,自己最要紧的是把儿子紧紧留在身边,看着他长大,看着他成才,看着他拜堂,也看着他养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儿……。
“孩子,你不要去北京了!”她说。
“我是去念大学哩!”
“不要念了。”她恳求道。
“妈,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他焦急了。
她又饮泣起来,“我怕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
他心情复杂,急得手足无措。他找过薇芷,她默默地听着他说,漂亮的眼睛不明地流露出惊讶的目光。
“你妈很疼你呢!”她在思索着这伟大的母爱。
“你说呀!”他焦急地问。
“还不简单,没妈妈疼我!”
“你……”
“你有个弟弟就好了。”
“倘若你换了我,怎么办?”他说。
“每天从北京寄回一封信给妈妈。”
“那有这么些邮票钱!”
“到了北京再想办法。”她突然斩钉截铁地说。
他下决心说服妈妈,把几件钉补过的衣服也收拾好了。
妈焦虑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她终于病例在床上。
“你先走吧!”他对薇芷说。
“你很孝顺。”
“我不愿伤了她的心。”
“明年来吧,我等着你。”她深情地望着他说。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们就这样分开了手。
日子长了,他开始感到生活的无聊,每次读着她的来信,大学里沸腾的生活,科技升腾的信息,知识结构的更替都使他感到兴奋,刺激起求知欲望。他后悔了,对失去了的岁月感到无限惋惜。于是他又决心读大学去。
妈妈知道了非常焦虑,她不明白儿子为啥老是想离开这个家。书读了足足九年长还不够么?一个人肚子撑饱了再多的白米饭也塞不进去。够得上写信念报纸就行了呀!那天她吃过早饭便匆匆上路。正午赶到圩上在黄大婶家里占了个卦,算出她儿子命水好,有榕树这样多的叶,有竹树那样多的根,只是眼前碰上了风浪,要给他挂上个秤砣,好生稳住。这个秤砣她想也不用想便明白了。回到家里她当晚就托媒上成叔家里说亲去。她满以为有了这个秤砣儿子就留得住了。高兴了整整一夜。待一切都有了眉目准备就绪之后,她从区上把儿子叫了回。
有如晴天霹雳,他一下子惊呆住了。他失神地仰摊在在床上,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地响,一颗心早已跳出了胸膛,手脚冷冰冰的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他想不通妈妈这样逼紧为的什么?他心上只有一个薇芷,从没有思念过任何一个姑娘。他曾暗自发誓,要是薇芷愿意嫁给自己,他—定做到始终如一,绝无二心。他看见薇芷站在面前,倚着床沿睁着一双泪眼默默地凝望着他,她多么伤心啊!她知道了吗?他隔着一条清澈的小河,看见她站在对岸河边的青石块上,浑身纯净透明,晶莹地闪发着绿色的光。他惊讶住了,他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看见过她啊!看见她沾满着故土的赤脚,看见她那执着的追求,看见粗糙的刻苦拼搏的双手,看见她那一颗透红的搏动着的心……他那冷冰冰的手脚渐渐地变得温热了,感到全身的血在沸腾了起来。他看到自己的事业、理想和希望,世界上的一切都好象变得纯净清晰而又明白。对了,他不能答应妈妈,绝不能答应。
他霍地站了起来冲出门外去了。
“阿华!”妈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站了出来。
他浑身震动,双腿着魔般地站住下来。宛如反馈信息在大脑皮层上闪现,他望见母亲憔悴的眼睛,发白的消瘦的脸颊上沾着斑斑泪痕,还有那微微颤抖着的嘴唇,顿时他双腿软软地拖不起来,浑身无力。他竟本能似地停住了。
“你不喜欢?”她忧郁地问。
他点了点头。
“是妈给你定的,有什么不好!”她那白纸般的脸盘变得一片灰暗暗的,没一丁点儿血色。
“我不喜欢她。”
“傻仔,拜了天地,成了你的人,你就会喜欢了。”她想起了自己走过来的路。
“妈……,我真的不喜欢……”他想给妈说自己同芷薇的事,话到唇边又吞住了。他知道在妈妈慈和善良的心坎里却又令人费解地留有嫌弃薇芷的宗底身世的阴影,门当户对,他家不可以接进门来一个成份高的媳妇。他的心顿时冷却了,只觉得一阵阵刺痛。
妈抽泣了,眼泪涌泉般地流下来,冰凉了的身体木然地立在地上,一动不动,好象一根朽木只消微微地捎碰一下,便会啪的一声倒在地上,永远也再站立不起来了。
“我那有脸去见你死去的爹呀!”
他心慌了,手足无措。他担心妈妈会倒落在地上。他了解妈妈的心,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的悲哀,了解她心灵的痛楚,也了解她的祝福和希望。她的心是慈祥的,她对薇芷很好,每次上门都端出最红的桔子,柔软的糯米粑粑给姑娘吃,问寒问暖,并没有因为心里嫌弃她的家底而慢待了人家。然而,他明白阶级门第的森严就象萨菩一样地在妈的心里扎下了根,没有任何的办量可以把这根儿拨出来的。他一时之间觉得头昏脑胀,心慌意乱,焦急得悄然地滴下了泪珠儿。
“妈,我不去上大学了。”他让步了。他害怕伤害了母亲的心。
她术然站着,脸上依然是那样的悲怆冰凉。她明白儿子的孝心,也体察他求学心切争取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光宗耀祖。正因为这样,她才不能让他远走他乡,无论如何得留他在身边,看着他,管着他,不能由他有半步差池。顿然,她眼前一亮,觉得圩上的黄大神卜卦很灵,儿子不就答应不走了吗!她那干巴巴的嘴唇边露出了一丝儿笑容,随即又消失了。她察觉自己还没有把秤砣挂在儿子的颈脖上,便说:
“明日是吉日,正好拜天地呀!”
“妈,我不……。”他急忙说。
“你不是答应了吗?”
“不答应,我不……”他急得说不下去。然后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吱吱哑哑地驶走了。
“你不听话!”妈沮丧地坐在地上,昏厥了过去……
她变得冷漠了,看见他苦痛内疚的样儿,心里觉得好笑。他在为自己的灵魂而悔过,还是在埋怨这不幸的命运。她不愿意回忆过去了的岁月,也没有兴趣翻腾起那青梅竹马的嬉戏的激情。只要生活熙熙攘攘,混混沌沌地过去了,但愿能原原本本,实实在在的到来也就感到满足了。她觉得他很可怜,昨天她还上门向他求教,冀求得到他的同情,枯竭了的心灵好象得到了一阵甘淋小雨,唤起了生命的绿色。可是,当她今晚同言威见面之后,看见他急于咀嚼蜜糖的饥渴模样,她顿然地感觉到自己的重量,恍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她没想到自己身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啊!呸,这是什么品种的魅力?因而她反而讥笑起自己的怯懦。
她终于明白了,她同情他但又恨他。
她站起来束缚好被南风吹散开了的纱窗幔,才又坐在他面前的白藤椅上,说:“你吃亏在缺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
“这是历史的惩罚!”他很感激她向上面极力推荐自己,可是一切好象早已注定了的一样。
“不,应该惩罚历史。”她觉得他太可怜了。
他惊讶地抬起眼睛望了望她。他理解不了她的话,感觉她变了,变得捉摸不定,变得不容易理解,好象她倏然成了足球场上的飘忽的中锋。
为了推荐他上去,她做了一些调查,这才发觉他确实是个开拓型的经济人才。他的集团公司开业才一年多,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去年获得了厚利。接着公司朝多元化开拓,活象一张蜘蛛网向世界市场呈现出放射性的伸延,同十几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协约,成为世界性的准集团公司。他有经验,具备了专业知识,可以说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因缺少一纸文凭,他上不去,仍旧当个副经理。他的智能远远地超过现任的职位。她现在才明白内里的一个秘密,领导班子的调整还得有个文化水平提高,年西降低的平均数值,而这一切都得具有证明。她知道有的人好几年前是五十七岁,可今天却填上五十五岁。人们说未嫁姑娘年年十八,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有人说了个笑话,某副市长全身都是假的,只有两样东西货真价实:汉族、男性。这虽然有点儿危言耸听,但那个假确实是存在的。我,非我嘛!这二元论兄弟是学到家了。她越了解得多便越生气,生气之后才又觉得好笑。什么时候这官场也能象科学技术研究那样付诸实验,实事求是,那天下定然会早日大同。还是那一句话:大有大难,小有小难。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各怀心事的世界。
“这不公平,但该说的我都说了!”她有点感慨了起来。
“我还是这个宗旨,既来之则安之。”他何尝不感慨万千呢!工作是自己做了,可落到实处却是空的。有人做了预测他是当然的副市长,这无疑说得太武断。但他当选市劳模之后,这“当然”的呼声却又高涨了起来。传说纷纭。有好心的还做了可行性分析,认为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个文凭,一个后台。方大姐早离休了,人走茶凉,说话人家可以左耳入右耳出。结论只能是两个字:命运。他对此脑子里都有过反应,也都有个种种预测,只是没有料到上面竟然不顾真才实学,才明白这劳模毕竟还是个虚的东西。归根到底,使他心情复杂,思想混乱的原因应该归究于这些预测和可行性!?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薇芷了解他,从心里感谢她为自己奔波。
“我不理解。”她简直是惊异,这开拓意气和逆来顺受两者竟然如此和谐地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象混和了的沙糖水一样。
“不理解也得接受啊!”
“……”她笑了,笑自己忘却了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不理解的却是理解了的,理解的恰恰是没有理解。昨天有位好心的领导劝她别给李华讲话了,注意影响,好象她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外面的话难听死了,尤其是出自言威的嘴。要是过去她准伏在枕头上咬着被角哭了,今天她只一笑了之,有什么值得挂在心上!
“我不明白你担心些什么,究竟有啥可害怕的呢上行下效,当官还不是这样的过去。”他又感觉她变得捉摸不定了。
“嘻嘻,”她又笑了,“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但我不当你说的那个品种的官儿。你我不一样,我随时准备掼下乌纱帽落荒而逃。做不了便当我的技术工去,绘图测量都行。”
“你……”他惊喜交杂,猜不透她的心,人说每个女人都是个谜,她却是个很难猜得着的谜。几年不见面,她变了,他辨认不清楚是她脱颖而出,还是焕发出本来的容光色彩!
“我担心会出洋相,你得给我说说,批阅文件的程序格式,平日交代秘书做些什么工作,还有出席宴会我该站在哪个序列……”她一口气地说了许多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问题。他心里觉得好笑,这个主任工程师十足是从大森林里跑出来的。
“车到山前自有路!”他笑了笑,好象刹那间什么都可以理解了。
四
炎夏,太阳很猛。这里的阳光比省城的毒,烤得皮肤火灼灼的疼痛。马路两旁新栽下的白玉兰、梧桐和盘架子树。才长得人般高,叶子稀稀疏疏。行人道上光溜明净,没设有遮挡太阳的骑楼。
幸好遇上荔枝大年,西瓜又烂市,这样上好的消景生果吃得大伙儿肚皮胀了。虽然天气炎热,可心上还是清凉的。讨厌的是还带有点儿甜蜜的果皮最惹苍蝇,垃圾池里红头绿眼的大苍蝇嗡嗡地叫鸣。徐大妈讲究清洁,用塑胶袋子包紧住果皮,桌子用洗洁精抹过,一尘不染,家里休想昕得见嗡嗡的鸣叫声。楼下院子里的水泥曲道上不知谁家在晒荔枝干,一摊摊的,幸好太阳猛毒苍蝇不愿意陪着一起晒干,全都躲到别处去了。
小王妈搬走了,但有事没事爱回来街坊叙旧。她儿子上了去,见多识广,家属里数她消息灵通。左邻右里见她来了,自然而然地聚集在她周围。话匣子打开便滔滔不绝的没有个完。
她说:“近日来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副市长,跟咱们一样是个长头发的。”接着用手指住远处天空那一座七十层高,嵌着茶晶玻璃的圆形的旋宫顶层又说:“这铁塔是她擎起来,牛头庄天桥也是她双手垒起的,人家的脑瓜有电子,对了,是电脑子……”
“这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记性不好,啊,陈什么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