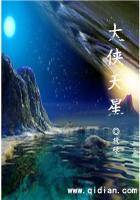第六章
整个学校里面,最得意的人群当属考完高考的高三党们-带着浴火重生的凤凰气质。长安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体会过“涅槃”这两个字的美感——枉为他喜欢“涅槃”乐队这么多年了。
考得不算太好,但是长安也算是发挥出了他应有的水平。到了最后一个月,长安才发现爸妈基本上对于他考试的结果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期待,反正是把这场逼死人的考试考完了,全家人都轻松起来,默契的是谁都不过问成绩的事情,只等着出了成绩以后安排后面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班里、年级里的同学们都在疯狂地组织各种聚会和派对,还有一个更为盛大的活动,就是年级的毕业典礼。长安认识的朋友里面,认真听摇滚乐的,只有殷亦可一个人,但是会乐器的却不止于此。他的梦想,就是站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表演一首喜欢的歌。其他几个班里面找来了一个会打鼓的哥们儿,一个会弹键盘的。实在找不到贝斯手,于是找了一个傻乎乎爱凑热闹的哥们儿,大家伙打算一起逼他“速成”,虽然成就一个熟练的贝斯手是不可能的,而短期内练下来一首简单的曲子总还是可以实现的。会唱歌飙高音儿的人选是早在年级里面出了名的校园歌手,人家不但在学校有名,在网络上都是小红人一枚。就这样,一个校园摇滚乐队就成型了。
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也突然掀起一股乐队小说流行的风潮,组乐队几乎是每个学校里都有的时髦,而究其动机,四分是热爱音乐,六分是耍酷。几个小伙子凑在一起,达成一致的目标是分外容易。主唱早都是名草有主的人了,每次排练都带着漂亮的外校女友过来,坐在一旁又养颜又暖心。大概是这样的陪着乐队的姑娘格外令女生羡慕,没多久,竟然速成的贝斯手和鼓手也都各自能带关系暧昧的姑娘来看排练了。而高三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考试前,老师们恨不得在学校里搞性别隔离,而这一考完试,对于这样亲密的男女生同学关系,班主任老师也只是笑眯眯地含笑不语,她偶尔过来看看排练的情况,还鼓励同学们好好排练,争取在毕业典礼上“一举成名”呢。长安觉得老师也真有意思,这态度变化反差也太大了。
于是也不知道怎么着,组建乐队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几乎是自从头一天当鼓手敲打出的巨响从学校的音乐教室传出去以后,每天的排练都成了学校里可供围观的非正式表演了。每天其他年级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的围观群众还相对少一些,基本上也就是高三回校溜达的同学,而一到课间,其他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也都过来了,围在教室外面,向他们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长安的自我感觉好极了,他觉得爱音乐的人就应该这样被羡慕着,而真正演奏出自己心中的旋律,是更胜一筹的喜悦。那是一种比语言更美妙的表达,更贴近内心的感觉,更有力量。
在长安心里,纵然挤在门外的学妹里面,也有几个长得不错的,可他只期待一个人有一天能过来看看。可惜那个人在高考前不怎么搭理自己,考完了,更加没了消息。殷亦可怎么样了,她还好吗,慢慢地,长安都没有了自信再去关心这个问题。
长安这段时间特别不想回家,因为每天很晚回到家的时候,一个人安静下来,想念的疼痛就无法克制。他最近喜欢
Blink-182的一首歌,那首歌里有一句话,“Inthenightwe‘llwishthisneverend.”
那个毫无心情想念长安的殷亦可仍旧把自己彻底埋在旋律里,从早到晚,大大的耳机挂在头上,人就像是穿了一层盔甲可以整个脱离于现实的世界。晚上熬到两三点钟才能睡着,早上破晓时候就又醒了,醒来就戴上耳机又开始每日每夜地听歌,这样的状态已经连续两周了。
她的音乐喜好从之前单纯美好的英伦摇滚快速进阶到了暴虐的重金属,狂灌了一周嘶吼之音以后,她开始无限循环着一种极度压抑、绝望的唱腔,黑暗如沼泽般的气氛在殷亦可昼夜颠倒的日子里肆意蔓延着。曲子一首接一首地放,不停地滋生又疯狂滴消耗着所有那些强烈、躁动、细腻、蔓延开来的情绪。
和爸妈,她每天只说几句话:“好的,马上来吃饭”、“吃好了,不吃了”“我没事,就听听歌”、“真没事,不出去了,你们出去吧”,以及“嗯,知道了,你们睡吧,我一会儿就睡。”
慢慢地,殷亦可进入了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在这里,她放弃了语言。这个思维犹如疾风狂奔的女孩儿在用静止的状态给心灵飞速地作茧,在这个自己封闭起来的狭小世界里,她可以停止不明所以的努力,可以不向任何人作任何解释,可以以为别人的态度、评价都不存在,这个世界对自己那些无法商量的要求也可以不予理会。在这里,只有她和音乐,她和她心里的旋律,她和另外一个或生或死、千里之外、语言不通的人的共鸣,而这种理解,足以让所有其他的所谓“理解”无足轻重。
慢慢地,殷亦可的妈妈开始有些担心了,向来有敏锐直觉的她看着女儿这样一日日发展下去,不好的预感与日俱增,但她又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她向来是个理性、内心宽厚的母亲,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她知道理解是很重要的,然而这样封闭着自己的状态发展下去,怕是会对心理产生伤害。
殷亦可爸爸说,“实在不行,要不要给她老师打个电话?”
是个不错的主意,殷亦可妈妈考虑了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联系。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一个礼貌的时间,殷亦可妈妈拨通了班主任老师的电话。重点学校高三年级的班主任,不仅仅是教学上的好手,也几乎都是学生心理成长和家庭关系的专家,很受家长们的信任。
“喂,周老师,您好,我是殷亦可的妈妈,不好意思一早打扰您。”
“亦可妈妈啊,您好您好,别客气,您说,什么事?”
“哦,周老师,是这样,孩子们这都高考完了,我们亦可的情况,您大概也了解……”
“嗯,是的,那天考完,出了考场我看见她了,我知道,她没发挥好,不过现在,毕竟还没有出最终结果,还是先放松心情,不要太担心了,好好休息几天!”
“确实是这样,周老师,孩子回来跟我们说,考砸了,我们一开始也是安慰她,让她先耐心等等成绩,别多想了。结果这孩子对自己不依不饶的,从考试完了到现在都两个星期了,天天就闷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哪里也不去,也不跟人说话。周老师,我真是担心,这样下去,孩子要憋出病来了。”
“啊,是这样啊,这情况确实家长要干预一下了,亦可妈妈你考虑得确实对,这么长时间自己一个人憋着,确实对孩子成长不利啊。最近班里面同学之间活动挺多的,我安排班长赶紧联系亦可,叫她出来和同学们聚聚吧。”
“周老师,我也希望她能出去和同学们玩玩啊。他们班长好像前几天打了几次电话找她来着,她都不想接啊。还有几个可能她玩得好的好朋友,也过来找她,不见面也都不接电话,不联系了。周老师,你看这怎么办才好呢?”
“嗯,这样啊。那您跟我说说,她这段时间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
“这孩子就自己在房间里面听她的那些音乐CD,没完没了地听,有的时候我看都半夜两三点了,灯还亮着。我真是很担心啊。”
“亦可妈妈,你身边,有没有很懂音乐的朋友,成年人,性格成熟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建议你不妨请这样的朋友尝试跟亦可联系联系,让他们从音乐的角度谈谈,跟孩子聊聊她喜欢的东西。我们首先是要马上让她开始与人沟通,不能让她再这么一个人闷着了。”
“啊,这样啊,周老师,您这个办法我可以试试,是个好主意。嗯,我找找我的朋友看。太谢谢您了周老师!我应该早点向您请教。”
“别客气,亦可妈妈,您先试试看,最近有什么情况您随时和我联系,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您也放松心情,高考的事情,我们后面再商量。”
挂了电话,殷亦可的妈妈心里亮起了一盏灯,这位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老师不愧是教育的好手。想到她提的建议,殷亦可妈妈着实开始在脑海里面搜索起来。这位在企业里做高管多年的商海精英在人际方面确实广阔,很快,她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老乔。
老乔其实并不老,比殷亦可的妈妈还年轻好几岁,只不过是因为他一直蓄着的刚刚盖着下巴的胡子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沧桑。他是当地电台的音乐主播,一直在节目里用着他自己本来的名字,一个可以很土气但细细想来又很文艺的名字——乔木生。三十有五的他曾经是个狂徒,入过帮派,打过架,为了心爱的女孩儿差点丢过命。年轻气盛的他无奈岁月蹉跎,慢慢俊秀的面庞也弃他而去之后,他开始主动地褪去身心铅华,唯独留下了天生有一副会听旋律的好耳朵和他那不入凡俗自然洒脱的心。老乔的电台工作基本上是由他独当一面,在这种城市的综合电台里工作,音乐节目都占不到一个全天的频道,穿插在正午太阳晒得人酥软朦胧和深夜人们情意微醺的时候,老乔低沉的声音像大提琴般稳稳地托住这个城市里偶尔在喧嚣中独处的心情,他们的万家灯火,和老乔独白的淡漠,彼此需要。
老乔是在一次政府公益活动上和殷亦可妈妈认识的,殷亦可妈妈虽然是个商界精英,却速来赏识风雅之士,老乔在音乐方面颇广的见识令人印象深刻。
挂了周老师的电话,殷亦可妈妈拨通了老乔的电话,三两句精炼地总结了孩子的情况,老乔热心地同意帮她试试和孩子开始沟通。两人相互客气了几句,老乔留了殷亦可家里的电话,说这两天就联系。
对老乔来说,光是听了殷亦可妈妈那几句描述,他脑海里就马上浮现出了曾经那个摔了家门然后独自在公路边上漫无目地流浪的自己。对这个尚未谋面的孩子,老乔似乎已经信心俱足,自己走过的路,还不比一个未上路的孩子熟悉么?
自此,殷亦可的妈妈为孩子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殷亦可的妈妈没有看错人,经历了世间冷暖、叛逆成熟的老乔如今的思想闪着睿智的光。而她不知道的是,老乔听摇滚乐的年份,要比殷亦可的年纪还长。
晚上十点半,老乔的声音准时从广播里传出,殷亦可的妈妈刚刚把车停好,坐在驾驶座上,她静静地听了几分钟节目。常规的节目赞助商冠名问候,老乔的声音不温不火,轻描淡地挖苦了几句这不怡人的燥热天气,然后开始播起了舒缓的流行歌曲。殷亦可的妈妈默默在心里想,不知道这个老乔什么时候会联系女儿,但是因为自己急躁就连连催促确实不是礼貌的做法。十点半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已经算晚了,可能老乔昨晚节目都要将近十二点了。今天就算了吧,实在不行,明天再联系一下他吧。
殷亦可的妈妈熄了火,锁好车门。站在楼下的她,望着女儿窗口隔着窗帘透出来的微光。对于这个鲜嫩又敏感的灵魂,做妈妈的,真想冲进她的房间将她一把拉出那个越发悲伤的房间,她有时候真希望自己的小亦可还是那个小小的孩子,天真烂漫,完全地相信着大人给她的一切安排,她多么希望一切还会像女儿小时候那样,自己每次假装兴奋逗女儿开心的时候,都会看到她的小手掌兴奋地拍在一起,听她高兴地喊着“好棒啊!好棒啊!”而这个小女孩终究是长成了少女,一个需要为自己的想法挣扎出空间的少女,而作为她的妈妈,是不是保持优雅的旁观就真的可以呢?
回到家,殷亦可果然还是自己闷在房间,殷亦可爸爸在客厅心不在焉地看电视,一是怕女儿在房间里出什么事,二是怕女儿突然出去跑到外面出什么事。
殷亦可妈妈走到女儿房间门口敲了敲门,无人应。她小心翼翼地尝试打开房门,看见戴着大耳机听歌的女儿猛地抬起头,她愣愣地看着站在门口的妈妈,一边头还点着音乐的拍子,没有打招呼的意思。
殷亦可的妈妈跟女儿做了个手势,示意她想进来说几句话。殷亦可这才取下耳机,揉了揉耳朵周围压红的皮肤,理了理自己那一头凌乱的短发。
殷亦可妈妈整了整女儿床上随意摊开的被子,坐在了床脚。
“妈,你回来了。”一边这么说着,殷亦可觉得有些生硬,不由挠挠脑袋。
“嗯,是啊,忙了一天。你吃晚饭了吗?”
“嗯,跟爸吃了两口面条。”
“亦可,这几天还不想出去玩吗?”
殷亦可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看看窗户,外面天空不知道什么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深蓝色。她回答了一声“嗯”,也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妈妈今天给你们周老师打了个电话,就问了问学校最近有没有什么安排,没多说别的。你们周老师说,欢迎你参加班里面毕业典礼的排练,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没什么兴趣,我出了学习,什么特长也没有。哦,对了,学习也不是我的特长。”
“这……”殷亦可妈妈听了这样的话,三分是尴尬,七分是心疼,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了打破这种生硬的局面,殷亦可妈妈拾起对在枕头边上的一个CD盒,看了看封面上的图案,一个模模糊糊的画面,好像是一个注满了红色液体的泳池。
“这是什么乐队的?好听吗?”
“哦,还可以。还挺好听的吧。”殷亦可显然没有跟妈妈分享的意思。
“对了,亦可,妈妈认识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在电台做音乐节目的叔叔。妈妈想,你这么喜欢听音乐,肯定你们俩有很多共同语言,妈妈介绍和这个叔叔认识认识吧?你们可以一起聊聊音乐。”
“电台的吗?电台的音乐可能不是我喜欢的。”
“嗯……没关系,你可以先认识认识他,说不定他也喜欢你喜欢的这些呢?”
“不知道。再说吧。”殷亦可眼睛往地板上看,刚才那几句已经是这几天来说的最多的话了。
等了几秒钟,殷亦可没再说什么,妈妈也觉得再继续有些勉强,只好叮嘱了女儿早点休息,就转身走出女儿房间了。
殷亦可又套上了自己的大耳机,不想思考,只想听歌。
她自己不想承认,但连续长时间窝着听歌的她,摘下耳机听人说话,觉得那声音犹如从海底传来一般。这几日,她的脑门阵阵发涨,有的时候脊背也已经很不舒服了,但却没有力气站起来。有时候到了深夜,会觉得呼吸有点困难,需要很用力才能一口气吸到底。而真的困得不行的时候,想逼自己闭上眼睛睡一会儿时,心脏又跳得格外强烈,震得整个胸腔、整个人都不舒服。于是就这么醒着听歌听到困,刚睡着又被身体的不适感烦扰醒,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