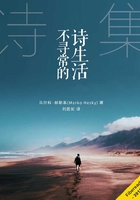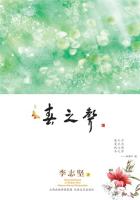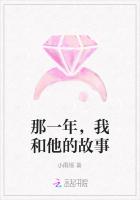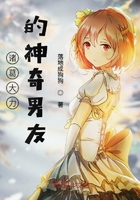——访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蔡东士
听说咱们《电视艺术家》杂志本期的封面人物是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蔡东士,熟悉他的电视人纷纷“报料”——
一位了解他的业界领导总结了蔡书记的“四气”:正气、骨气、才气、义气。而这“四气”,又几乎无所不在地体现在工作、生活的细节中和笑容里;
一位电视界卓有成绩的老领导有感而发:离开领导岗位前,蔡书记多次过问、落实我今后的安排和待遇,我夫人总在念叨,有机会一定要当面向蔡书记说声“谢谢”;
一位资深电视人感慨地说:蔡书记是省委领导,但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温和、可靠、笑容可掬的大哥,这缘于他的深厚学养和人格魅力;
一位年轻的电视编导由衷地表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蔡书记颇具亲和力的微笑。有一次他到电视台演播厅参加一场重要的晚会,从头至尾他都在微笑,我们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天,我们刚走进蔡书记的办公室,只见他已经快步迎上前来,一脸灿烂的笑容,我原先想好的几句客套话都没有说。
一坐下,我就递上了最新一期的《电视艺术家》杂志,蔡书记边翻阅边笑着说:前几期我都看了,不错,办得精彩、有深度,也比较人性化。他又关切地询问了杂志的发放情况,这才开始接受采访。我没想到,他那么坦率地谈起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包括8年难忘的知青岁月——
难忘的知青岁月
蔡东士属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1947年出生在粤东地区潮阳县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
那是一个崇尚理想、激情燃烧的年代。蔡东士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作家、医生、工程师。他总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对文学尤其感兴趣,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楼梦》、《说岳全传》等大量文学作品,好些字和词他还不会读,却连想带猜知道了大概的意思,会写会用了。
有一天语文老师带着蔡东士的一篇作文来家访,问他的母亲:这篇作文写得很好,是不是他哥哥帮着写的?怎么用了那么多没学过的词呢?
母亲看都不用看就回答道:不是的,他哥写作文不如他。
正当蔡东士为实现理想而发奋读书的时候,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蔡东士读大学的梦破碎了,为革命贡献青春的热情却不减,原本可以留在家乡的他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去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第十三团,也就是现在的阳春岗美华侨农场。
蔡东士的知青生涯开始于1969年6月。
艰苦和困难蔡东士都不怕,他的执著认真和聪明能干很得干部职工的赞许。可他心里有个阴影,那就是父亲的右派问题。当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它足以让一个要求上进的热血青年窒息般地害怕。因为如果要想入团入党参军提干招工,这类家庭问题绝对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那时候,除了拼命地干活,蔡东士几乎不作其他的考虑。他的才干很快让他脱颖而出,他被抽调到师部报道组,文章在屡遭退稿的半年后频频见报,但他内心深处的阴影却一直没有消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敢正视姑娘们热辣辣的目光,也不敢写渴盼已久的入党申请书,甚至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都没动考大学的心思。
那正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春天,“唯成份论”的年代要结束了。蔡东士的二哥和二嫂认定弟弟是读书做事的材料,力劝他参加高考,蔡东士这才在煤油灯下(当时晚上十点后不供电)苦熬了十个夜晚后,瘦骨嶙峋地匆匆赴考,他的强项是写作,作文分在湛江地区一举夺冠。而在收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时,而立之年的蔡东士“苗条”得只剩下90多斤。
许多年过去了。
一次,农场的农友聚会,已经是省委副书记的蔡东士和大家在一起,好象又回到了当年。一位早已定居香港的女农友笑着和他重提往事:“你那时多骄傲啊,眼睛长到头顶上了,我们好些女知青喜欢你,你可是一概不理睬。”
蔡东士同样笑着举起酒杯,说:今天我总算有机会解释一下了,当时我不是骄傲,也不是不解风情,是自卑啊。那么多好姑娘,我不敢找,怕讲了我的家庭情况吓跑你们,所以干脆沉默……
一番肺腑言,四座皆静默。短暂的静默之后是一片掌声,掌声中包含了农友们的心里话:东士,你还是我们印象中的小蔡!坦诚而且率真……
许多年过去了。
2006年,蔡东士带着女儿回到了他曾经战天斗地的农场,满山新绿显示出勃勃生机。而凄凄荒草中他当年居住过的连队茅草房却已是风烛残年,面对老主人默默无语。长大了的女儿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爸爸,原来你们那时候这么艰苦啊!”
蔡东士欣慰地搭着女儿的肩膀,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听革命老前辈讲过去的故事时那份敬佩和理解。历史的车轮总要滚滚向前,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是和知青岁月连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教给了我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乐观向上,虽然也有痛苦和遗憾,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后,已经成为我们珍藏的记忆,人生的财富。如今,女儿读懂了。但愿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读懂他们的父辈。
奋力打拼的记者生涯
知青、党员蔡东士在阔别校园十年后,成为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入学不久,学校组织看一个纪录影片,当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蔡东士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些比他小十来岁的同学不理解,他也不做解释,心想:经历过寒冷的冬天,对春天的来临该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积聚在蔡东士心头有关家庭出身的阴影彻底消散。他的学习成绩依旧领先,社会活动也积极参与,显示出过人的精力和组织才干,被大家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省学联主席。在班里,他还是品学兼优、善解人意的大哥。
毕业那年,蔡东士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在这之前,因为在农垦工作时常常给报社、电台等单位发稿,他在新闻界已经有了不少老师和朋友。加上蔡东士对记者这一行热爱已久,所以,他的工作如鱼得水,顺利开展。
正式到单位上班之前,组织上派蔡东士到重庆培训半年。回广州的时候他途经湛江,以记者的良心和敏锐的新闻触觉发现了一个医疗方面的问题,当即奋笔疾书成文,发在了内参上。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胡耀邦总书记和其他有关领导的重视,专门为此作了批示。
初战告捷,蔡东士大受鼓舞,更感到手中这枝笔沉甸甸的。他经常带着问题下基层,下农村,动笔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写文章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又十分讲究结构、条理和文采。那时候熬夜写作成了家常便饭,也成了他很享受的乐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累也认了。他向来喜爱古典诗词,每回出差,都铁定带上一本《宋词选》,早晚得闲时就拿出来翻阅、欣赏,其中不少名篇他都可以背下来。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住那些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从中体会意境,吸取精华,融会贯通在他的文章中,就是真情、激情和深情。蔡东士的通讯、散文和报告文学结集《寸草心》出版时,一向爱才惜才、提携后辈的著名作家岑桑高兴地为其作序。
在中大读书时,蔡东士就加入了广东作家协会,现在已经是中国作协会员。调离新华社之前,一位老师叹道:东士,你去政府部门工作,此后恐怕就只会写那些例行公事的文稿了!
蔡东士笑着,在心里回答了他敬重的老师:您放心,不会的。20年了,他写新闻稿、发言稿,起草文件,都做到了简洁、实在、有激情、有特色。他为纪念谢非同志逝世一周年填的《满江红》词情深意切;他为抗非英雄、白衣战士们自己动笔写的书所作的序好评如潮;梅州的叶剑英元帅故居纪念馆开馆时,他起草的领导致辞,言简意赅,文采飞扬,回顾了叶帅一生的丰功伟绩,表达了故乡人民对他的景仰和思念,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素未谋面的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和为蔡东士进入新华社讲过课的郭超人看过蔡东士的文章,很是赞赏,为他的第一次破格提拔投了赞成票。助理记者蔡东士当上了分社采编室副主任,几年间写了大量有见地、有分量的内参文章。
正当蔡东士在记者的岗位上越干越欢,同时管理水平和协调能力也得到一致好评的时候,省委的一纸调令结束了他六年的记者生涯。
调令来得很突然,蔡东士事先一点也不知道。领导找他谈话时,他明确表示不去,还是继续当记者。但领导说:省委和总社领导很重视,这事已经定了。你快去报到吧!
没有选择了,蔡东士走马上任,当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职务两年跳四级,他自己都完全没有料到,满脑子想的唯有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现在,人们总说蔡书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他粲然笑道:我走到哪里,见到的都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我根本不敢摆架子,也摆不起架子。
回想起来,蔡东士始终认为:8年知青岁月,练就了他克服困难、不懈追求的意志;六年记者生涯,养成了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习惯。这让他一生受用不尽。
与电视结下不解之缘
蔡东士与电视结缘,是在他告别记者生涯的前夕——
要调走了,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天经地义的事。蔡东士马不停蹄赴佛山地区调查有关鱼骨天线的问题。他走村过巷,以一贯的认真细致投入了采访,发现群众架鱼骨天线看境外电视属事出有因。要解决问题,宜疏不宜堵,办好老百姓欢迎的电视节目才是万全之策,但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在文章中分析了我们的电视报道总比境外慢半拍的情况后,提出能否在广东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网开一面,允许广东电视台用境外电视的新闻图像,文字则以新华社的为准。
这样既有客观事实又有理论分析,还能提供决策参考的内参,无疑会引起重视。结果,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同意试行蔡东士文中所提的办法。这种有效的疏导,给广东电视打开了一扇开放的窗口,在1987年可是一件新鲜事。观众们虽然不知内情,却为电视新闻的这一改革而欢欣。